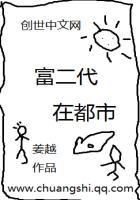杰伦营帐。
出于避免受到敌人偷袭的考虑,杰伦每一次命令大军停下来休息的时候,都会先派探子到四周打探,这样一来,如果有什么风吹草动的话,杰伦便可以马上知道,早做准备。
这不,军队刚刚扎好营,杰伦自己也才洗了一把脸,马尼罗就走进来报告说:
“兵团长,探子回报,从哥本尔根出来了一支军队正朝我们的方向逼近过来,看旗号好像是沃尔根亲自出动,大概还有三四里远的距离。”
“来得正好,省得我们再跑那么远去找他。命令全部士兵上马,准备跟沃尔根军队决战。”杰伦笑着说道,同时心里想:终于可以报仇了。
马尼罗出去一会之后,‘前进军’的士兵们就已经全部准备就绪了。
“兄弟们,出发!”杰伦挥舞着手中的刀,说道。
实际上,他们几乎不用再走了,沃尔根的军队离他们的队伍不超过七百米的距离。
两军正式交战之前的对峙,自古以来只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山崩地裂,喊声震天;另外一种则是像现在这样,安静,绝对的安静,静得几乎听得见双方士兵的心跳,静得连一颗纽扣掉在地上都听得见声音。
一种为自己一方而血战到底的神圣感觉、一种用对方的鲜血来染红自己的战袍的感觉不约而同地在双方的心里升起。
“杀!”当两股强大的杀气互相交缠着、各自膨胀到极点的时候,这个战场上用得最多的字就不可避免地要从双方主帅的嘴中蹦出,并且接着便要借助士兵们手中的枪和刀得到实行。
杰伦身先士卒地冲了过去,在他以前参加过的所有战役中,他从来不曾如此冲动。尽管他心里早就深深地明白身为主帅,最忌讳的就是过于冒进,主帅是一个军队的总枢纽,总枢纽一旦出了事,后果将会不堪设想。只不过,当他看到沃尔根阴沉的笑脸的时候,长久以来压积在心里的莫大仇恨一下子不受控制地全部爆发出来。在这个时候,他脑子里浮现出惨死的亲人们临死前在大火中挣扎、哀鸣的情景。他像是一头被激怒的野兽一样冲了过去,他要砍下那可恶的头,狠狠地撕下那张恶毒的笑脸。
“兵团长,不要冲动。”本来骑着马跟他并排的马尼罗想要阻止他,可惜已经太迟了,马尼罗只好跟在后面冲了出去。
军中两位最高领导人都冲了过去,自然而然,周围的士兵们也都边大声呐喊边跟着压过去。
“后退者杀。”对方也没有闲着,沃尔根大手一挥,催促自己的士兵们前进。然后又在前去交战的士兵后面排起了一队弓箭手,吩咐他们谁要是敢临阵脱逃不用等命令直接就一箭射死。这招果然够毒,怪不得他敢于在他老师面前夸下海口,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他的士兵们本来大都有点害怕“前进军”,但在他的这种举动之下,每个人都争先恐后地向杰伦的军队涌了过去,惟恐落后一步,被人射死。
两队人马正式交战了!就像狂风纠缠着暴雨,双方士兵纠缠在一起。大刀举起来又砍下去,举起来又砍下去;长枪凶狠而又不失灵活地左挑一挑,右刺一刺。地上的鲜血越来越多,尸体也慢慢地堆积起来,可是没有一个“前进军”的士兵会后退。投身于战斗之中的士兵们仿佛都听到有某种韵律,某种正好切合内心律动的韵律在流动。他们眼中都流露出贪婪的色彩,一种对血液的渴望,想看到对方的鲜血奔涌而出的热切心情甚至使人的求生欲望一时之间趋于消亡的状态。
凭着一股狠劲,再加上作战经验也比对方的士兵丰富,在开始不久的一段时间内,虽然人数上比对方要少,“前进军”竟然暂时取得了一定的优势。不过这种优势随着时间的推进,越来越微小了,毕竟到了真正贴身搏斗的时候,人数少一点无论怎样都是要吃亏的。而且,“前进军”以往之所以总是能够无往不利,不仅仅是靠临场的勇猛,还有另一个原因是对方总对“前进军”感到恐惧,因而放不开手脚。然而,现在,对方已经“不敢”害怕“前进军”了,因为,退却一定会被乱箭射死,只有打败“前进军”,才可能有一线生机。
失去了理智,杰伦红着眼睛,只顾一个劲地朝沃尔根的方向杀过去,甚至忘记了自己也可能受伤,忘记自己可能被人一枪捅死、一刀砍死。他现在只知道自己每杀一个士兵就会多接近沃尔根一点,就可以离报仇雪恨近一点,再近一点。是的,报仇,他心中除了报仇再没别的念头。他在不知不觉地陷入一个一旦进入就无法脱身的旋涡,他感觉自己周身乏力,但是他手里的刀却没有停下。一刀,又是一刀,他依稀看到周围的士兵在不停地倒下去,但又不停地涌上来,像海浪一样一个接着一个,后浪推着后浪,仿佛永远也不会休止。他感到自己像大海中的一叶扁舟,就快被这些海浪打翻、打沉,就快要被淹没了。
他抬刀砍中了一个士兵的喉咙,鲜血喷涌而出,激射到他的脸上,热乎乎的,有一种小时侯妈妈在冬天时用热水浸过的毛巾给他洗脸般的感觉,他伸出舌头舔了舔自己脸上的血迹。
“妈妈!”杰伦忍不住低低地呻吟了一声。
而那士兵的瞳孔慢慢扩大、发散,一脸惊讶的神色,仿佛不敢更不甘心相信自己即将要死去的事实,慢慢地倒了下去。
“妈妈!”杰伦又大叫一声,他感觉自己的身体在空中漂浮着,像浮着,像一片秋风中盘旋的叶子,毫无着落,他拼命想抓住点什么,可是却发现他什么都抓不住。
“兵团长!”朦胧之中,杰伦好像听到马尼罗这样喊道。
“前进军”总部阿尔斯山的营帐内,依维斯、西龙、坎亚正在商量军事。
“依维斯,前方传来消息,杰伦战败;星狂则在和敌军耗着,双方暂时都没有什么大动作。”西龙说道。
“什么时候的消息?”依维斯急忙问道。
“刚刚,白木跟我说的。我认为当务之急是派兵去救杰伦,至于星狂他虽然为人浮躁,但现在他还没遇到真正的对手,应该不用我们担心。”西龙说道。
“嗯,坎亚,我们有什么兵马可以立刻派过去救援杰伦的?”依维斯问道。
“依维斯,我们的军队分居四方,一时之间也难以召集,而总部的兵马则要镇守住这个山头。所以我想我们目前派不了兵去救援。”
“那你的意思是让杰伦自生自灭?”西龙诘问道。
“也只好如此了,况且我们鞭长莫及,就算派过去也不一定来得及帮杰伦解围。”坎亚答道。
“不行,我们不能眼看着杰伦孤立无援。依维斯,无论如何我们都应该派兵过去。”
“是的,坎亚,你说怎么办?”
“我们最多只能派五万兵马过去。”坎亚见状只好说道。
“那就派十万兵马火速前往救援。”依维斯说道。
“可是,依维斯……”
“坎亚,不用多说了,总部少点人也不会有事,西龙,派兵的事情你去筹办吧!”
“好的。”西龙说着瞪了坎亚一眼。
星狂帐内。
“星狂兵团长,这大半个月来,我们尽待在这个鬼地方,几乎动也不动,我实在受不了,而且我的粮草即将全部用光了,到时我们就不得不撤军了。”菲雅克对星狂说道。
“你着什么急啊?你要是那么厉害自己冲过去,粮草的事情你不用担心,用光了自然会有,我们‘前进军’家底还是很厚的,哪像你啊?就那么点积蓄,还想学人家打仗?还想统治整个普兰斯?四王子,心急是吃不了热豆腐的。”星狂一副优哉游哉的样子,实际上他也颇感郁闷,连日呆在这个地方,对方不进攻,自己暂时也不敢贸然挥兵前进。虽然心里已经有了一个计划,但是毕竟还没有实行,不过一看到菲雅克那副样子,他便禁不住要装装样子,逗菲雅克更加着急,取笑取笑他。
“可是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我们来就是为了打仗,不是为了在这里欣赏风景。况且这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闷都闷死了。”菲雅克红着脸说道。
“我知道了,看来四王子是嫌这里闷,嘿嘿,哥撒亚的‘美人儿’这么快你就厌烦了?”说着星狂走上去拍了拍菲雅克的肩膀。
“星狂兵团长,你……”菲雅克听到星狂这样说话,一时不知道答什么好,“算了,我还是告退了,星狂兵团长,有什么消息再告诉我。”
“恕不远送,四王子走好。”星狂捋着胡须望着他的背影道。
“维拉,最近士兵们操练得如何?”星狂转过头问道。
“士兵们操练状况还可以,不过……”维拉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
“不过什么,快说。”
“士兵们离家千里,以往有战争或者行军的时候,因为繁忙所以没有多少时间去想事情,现在一停下来,整天无所事事的,思念家乡的情绪便越来越浓了。”
“停了这么久,也该动一动了,妈的,我这副骨头十几天没有活动,也快‘生锈’了。”星狂说道。
“不知道团长有什么妙计?”维拉最近觉得想东西的事情该留给星狂,反正自己也想不出什么好的法子,不如乐得清闲。而且随着他跟星狂相处的时间越久,他便越对星狂佩服得不得了。现在维拉打心眼里觉得这个家伙虽然时不时便要爆几句粗口,有不太文明的嫌疑,但实在是一个自己怎样也无法望其项背的军事天才。
“呵呵,如果我说等待也是妙计的一部分,你相信吗?”星狂笑着说道。
“相信,当然相信。”维拉说道。
“这样都相信?你不是吧?那要是我叫你脱下盔甲冲过去跟可约拼命,并跟你说这就是我的‘妙计’的一部分,你还相信吗?你会这样做吗?嘿嘿。”星狂不怀好意的阴笑道。
“只要团长需要,叫我做什么都行。”维拉拍拍胸膛,大声说道,内心想星狂一定是在开玩笑逗乐子。
“好,我就等着你这句话。”星狂大笑道。
“不是真的吧?团长,是在跟我开玩笑的吧,呵呵。”
维拉尴尬地笑了笑,又再次感到自己的智商严重不够用,而且隐隐觉得有点不大对头。自己刚才那样说好像是在把头慢慢放上了绞架台,然后前来执刑的刽子手问自己想不想死,自己竟然回答说:有需要的话,我就去死。这不是傻到彻底吗?
“军中无戏言,你当了这么多年将军不会连这个都不懂吧?”星狂很开心看到维拉进入了自己的圈套之后一副又是无奈又是无辜的表情。
“是,不过团长,我可以问问理由吗?”维拉口中说道,心里却叫苦连天:你这么无厘头,我怎么知道你哪句是真哪句是假啊!
“维拉,你知道军人的天职是什么吗?”星狂突然语重心长地说道。
“保家卫国。”维拉这次学聪明点了,又拍拍胸膛说道。
“不是说这个。”星狂正准备听到自己最想听的那四个字,不料维拉竟然不上当。
“英勇杀敌。”维拉又说道。
“维拉,那你知道在这样的大冷天,有一个夜晚,突然要你赤条条站在外面吹风会是什么感觉吗?”星狂脸色一沉说道,既然诱骗不成,只好实行大官对付小一点的官经常用的方法———威逼了。
“报告团长,军人的天职是服从命令。”维拉垂头丧气地说道,心想:真是官大一级压死人。
“聪明,这就对了,那你还想问我理由吗?”星狂得意地捋着胡须说道。
“想。啊,不,不想,不想。”维拉说道,同时内心想:叫我去死都不让我知道理由,这是什么世界啊?
“嗯,今晚,我们就要出动全军去把可约杀个片甲不留,你现在就去跟士兵们宣布这个消息,同时,你还要告诉他们,今晚所有的人除了带刀、枪、弓箭之外,其他的什么都不能带。”
“其他的什么都不能带?”
“就是说不能戴头盔,穿衣甲。”
“不是吧?”维拉刚才还以为星狂是捉弄自己,让自己不穿盔甲就上阵杀敌,没想到原来是所有的士兵都要这样。
“就是如此,别废话,快给我出去吩咐士兵们做好准备。”
“是。”维拉不禁暗暗叫苦,出风头的事情星狂自己一个人都做完了,吃力不讨好的便让他来扛,现在出去跟士兵们说不能戴头盔、穿衣甲,然后还要他们去冲锋陷阵,不是给人骂都骂死了?
维拉慢腾腾地来到操练场,召集全体士兵之后,站在阅兵台上,清了清嗓子,张了张嘴巴。正准备宣布消息的时候,突然发现自己有个问题还没有弄明白,那就是该叫台下的人为士兵们还是战士们,还是用别的什么称谓。假如称为士兵们的话,显得很疏远,而且太普通了,几乎每个将领都是这样称呼士兵的,显示不出自己的风格;但如果用战士们的话,现在又不是在战场,虽然是即将要上战场,但毕竟不是在战场,这是有本质上的区别的。
“喂,快说啊!”
“待在那里干什么?”
台下的士兵见到维拉静静地张开了嘴巴好久都没有合上,纷纷发表意见表示自己的不满。而且大概是维拉平时的形象过于大众化,过于平易近人,士兵们大都对他没有丝毫的敬畏之情。所以以上两句已经算是最文雅的讲法,还有的士兵是这样说的:
“有话快说,有屁快放,妈的,老子刚操练完,还没来得及上个茅房,又急急忙忙召集我们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