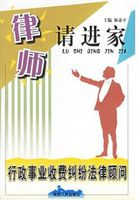可以说现在国际社会对于生殖性克隆都持一致反对的态度,但是对于是否禁止以预防和治疗疾病为目的的治疗性克隆问题上,各方观点有着明显分歧。2001年12月,联大根据法国、德国的动议,决定成立特别委员会,负责讨论和拟定《禁止生殖性克隆人国际公约》。美国、西班牙等国家,要求公约中除了禁止生殖性克隆人以外,还应该禁止一切包含人类胚胎的克隆研究。美国代表说,如果不禁止治疗性克隆,那么以科研实验为借口而制造和毁坏人类胚胎的做法将被合法化,新生命将变成一种可以采掘和利用的自然资源,而一旦克隆胚胎大规模出现,将不可能得到控制,从而使生殖性克隆的禁令名存实亡。而中国、日本、世界卫生组织等方面则主张区别对待治疗性克隆人。利用克隆的人类胚胎干细胞培养出用于移植或替换的组织和器官,可以为治疗糖尿病、老年痴呆等病症带来福音。中国代表说,国际社会不能容许科学研究损害人类尊严的某些作法,但同时也不能因噎废食,禁止可能造福于人类的医学研究和实践。各国的国内立法对治疗性克隆有不同规定,国际社会应尊重他们在不同的历史、文化、哲学和宗教背景下做出的选择。日本方面认为,关闭可能拯救人类生命的科技大门是个“错误”。
我国一直旗帜鲜明地反对生殖性克隆人。1997年3月,在英国宣布成功克隆绵羊“多莉”之后不久,我国卫生部负责人就宣布:“我们不同意、不支持、不允许、也不接受克隆人。2001年11月25日,当美国一个公司宣布他们已经成功地由成人细胞克隆了人类的胚胎时,中国卫生部再次重申了这一政策,并在2002年2月26日的联合国大会上表示中国政府支持联合国的建议,积极支持尽早制定《禁止生殖性克隆人国际公约》来反对生殖性克隆人。
遗憾的是,尽管我国政府多次重申不允许克隆人,但至今还没有出台一个专门的法规以规范克隆人的研究。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我国反对生殖性克隆,但支持治疗性克隆,赞成以治疗和预防为目的的人类胚胎干细胞研究。
3.关于人体克隆的立法构想。克隆技术本身是生物医学领域的高科技,有着美好的前景。让这项技术为人类造福,抑制其负面作用,趋利避害是我们立法的一项重要指导原则。我们一方面要借鉴其他国家的一些立法经验,另一方面也要立足我国的国情,建立一套可操作的制度和规则,为我国治疗性克隆技术的发展,和防止生殖性克隆可能引起的技术、伦理、社会等问题提供法律依据。
(1)禁止生殖性克隆人。由于生殖性克隆人从技术上无法保证其安全性,人体克隆胚胎可能会导致流产、早产、死胎、畸形等不良后果;从伦理上克隆人违背了人类社会成员最基本的社会伦理关系,是对人类尊严的否定;从现实上克隆人会造成人口数量猛增、破坏生物多样性、诱发新型疾病等诸多不利。所以,为了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有必要禁止克隆人的一切实验。这是人体克隆立法的最主要内容。
对于生殖性克隆应该严格禁止,防止引起社会伦理道德、法律制度、人权等方面的危机,对于这一点世界上已经形成了共识,不会有太大的阻碍。但是我国在立法的时候应该注意以下几个问题:首先,对于什么是生殖性克隆,特别是如何区分生殖性克隆和治疗性克隆应该做出准确的规定。否则会造成混乱,使生殖性克隆难以有效禁止或者治疗性克隆的发展被阻碍。我们主张对生殖性克隆应该作较为狭义的解释,只要不以克隆出完整的人体为目的的克隆都不应该被禁止。其次,对于违反禁止生殖性克隆人的规定进行生殖性克隆人实验的应该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一方面应该承担行政责任,对相关机构和个人进行处罚。另一方面,情节严重的还要承担刑事责任。当然,对于刑事责任的承担还有许多待研究的问题,比如适用什么样的罪名的问题,有些国家提出适用”反人类罪“,但这个罪名过于抽象,不容易被公众接受;有些国家认为适用”故意杀人罪“,但这种罪名也显得过于牵强;也有人提出适用”非法克隆人罪“,我们认为这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单独对违反禁止生殖性克隆人的行为制订罪名,比较适合这类犯罪行为的特点。另一个问题是如何界定违法的主体,具体实施者无疑是主要的责任人,而生殖性克隆中还有可能涉及委托进行克隆的人、体细胞和卵子的提供者、代孕者等,这些人如果明知的话也应该承担一定的责任。
第三,在禁止生殖性克隆的过程中也应该加强管理,而不能一禁了之。我们建议对于克隆技术的研究无论是生殖性克隆还是治疗性克隆,都应该建立一定的监督检查制度。在禁止生殖性克隆的法律中,规定进行克隆研究必须符合的条件和监督机制,从体制上杜绝生殖性克隆的违法行为。
(2)允许治疗性克隆。治疗性克隆不同于生殖性克隆,它不以生育人为目的,仅仅停留在克隆细胞和器官的水平。相对而言引起的伦理问题较少,现在大多数国家都没有禁止治疗性克隆。特别是我国受西方”上帝造人“的观念影响较小,长期以来不像西方有些国家那样反对堕胎,视胚胎为”生命“,所以在治疗性克隆上我国遇到的阻力比其他国家要小得多。所以我国应该利用这个很好的条件,发挥我国治疗性克隆在国际上较为领先的优势,鼓励从事治疗性克隆活动。治疗性克隆的有着重大的应用价值,我国有必要对其加以促进和保障。但对于治疗性克隆也要严格规范,毕竟治疗性克隆与生殖性克隆都属于克隆技术,从本质上并没有区别,如果不严格管理会导致在治疗性克隆的伪装下进行生殖性克隆,以及不规范的治疗性克隆所导致的技术和伦理上的问题。
对于治疗性克隆应该注意以下问题:首先,对于接受克隆的当事人必须出于自愿。因为,毕竟克隆技术是一项尚在试验阶段的新技术,在研究开发、实施应用的过程中存在着极大的风险,特别是涉及人身安全方面的问题,当事人很有可能对此会作出一定的牺牲。如果对其隐瞒真相,通过强迫、利诱等手段进行克隆实验,则会侵害当事人的利益。
其次,对于可以进行克隆技术研究开发、实施应用的主体资格,应该在法律上做出明确、严格的规定,以保证治疗性克隆安全、高效的进行和持续有序的发展。研究机构必须拥有一定的资金和相当的技术,同时应对研究人员进行严格的资格限定,加强对其科研道德的教育和管理。也可以像美国那样在科研机构内设立”生物安全委员会“,专门负责生物安全方面的事务。
第三,加强对克隆技术的监督、管理。克隆技术是有可能产生很大危害的技术,即使是治疗性克隆也是如此。为了使克隆技术的研究开发、实施应用有序的进行,防止克隆技术的滥用、最大限度地降低其负面效应,以及在突发意外事件时能快速地采取积极的应变措施,有必要对其进行严格的监督管理。可以由医疗、卫生等行政部门具体对治疗性克隆进行管理。采用批准制度,对符合条件的机构所进行的科研活动进行立项管理,也就是每一个机构所进行的克隆实验都要置于国家的监督之下,以保证克隆实验万无一失。
(3)克隆人的法律地位和权利义务。在上文中我们已经阐述了,克隆人必然会来到人间,只是早晚的问题。在当今复杂的社会环境下,克隆人试验不可能完全禁止。所以,我们在努力禁止克隆人实验的同时,也要做好克隆人诞生的各种准备,防止其对社会生活、亲属关系、伦理、权利义务关系等方面造成严重的冲击。对于克隆人而言,首先是生命权的问题。也就是克隆人有没有像其他自然人一样的生命尊严。对于这个问题应该没有什么争议,克隆人虽然不是通过两性繁殖的方式诞生的,但其也具备人的生理特征,完全可以成为一个具有生命权的人。任何人非法剥夺克隆人生命的行为,无论是在实验室还是其他场合,都将是犯罪行为。但这里有一个棘手的问题,如何对待”人畜嵌合体“。”人畜嵌合体“就是将人的细胞核移植到动物的去核卵细胞中,再移入子宫生育出来的”生命“。这种行为是极端不负责,损害人类伦理道德的行为,被许多国家所禁止。但同样禁止不等于不会诞生,如果这样的”人兽怪物“诞生,我们如何确定其是否有生命权变得异常复杂。从技术的角度说,这种”人畜嵌合体“基本上是由人类的基因所制造出来的,虽然多少也会受到动物卵细胞的影响,但其作用微乎其微,所以他的生命权也应得到尊重。
对于克隆人的亲属关系也是应该解决的重要问题。我们认为,可以像试管婴儿一样采用拟制的方式确定克隆人的父母。由于克隆人不存在普通人意义上的父母,所以为其设定父母,使其体会到正常人的家庭与社会关系,拥有一个很好的生理和心理状态。
在克隆人诞生的过程中还存在一个隐私权的问题。隐私权是自然人支配自己私人信息的权利。”克隆人“产生之后,对于遗传物质细胞的提供者,卵细胞的提供者以及克隆人自己的身份是否可以提供隐私权保护。我们认为,这些都可以成为人类新的隐私范围,当事人可以选择公开或者保守这些内容,他人无权干涉。侵害他人涉及克隆人的隐私权,像侵害其他隐私权一样都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总之,我们认为,人类科技的发展总是伴随着欢呼、兴奋、担忧、恐惧和无奈。人类的每一次科技进步都带来一阵阵赞扬和反对的尖叫,但每一次科技都会不为所动地向前继续发展。阻止科技的进步不是一个明智之举,趋利避害是几乎每一项技术产生后的任务。就像核技术带给人类极大的灾难,但又是人类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能源宝藏。我们为了保持人类社会特有的秩序,就应该防止有害因素的侵袭。生殖性克隆人会毁灭伦理规范、精神和道德,相信人类的智慧能够使克隆人的技术为人类带来幸福而不是灾难。但这需要各国科学家、法学家、哲学家、伦理学家、社会学家们的共同努力。
生物遗传资源的保护
一、提供基因资源引发的纠纷
(一)基因所有权问题的提出
人以及所有生物体内都有无数的基因,基因的研究将为我们揭示一个又一个未解之谜。但是基因技术是以基因为研究对象的,找到理想的带有特定基因的物种是基因研究的前提和基础。比如,找到一个野生的抗病虫植物,并进而找到其抗病虫基因;在众多患有同一疾病的人中对比找到致病基因,都是基因技术研究的重要条件。如果没有这些条件,基因研究也就很难展开。我们的问题也就由此产生了,对于人体基因而言,提供基因者能否拥有某种权利,以及获得相应的利益,对于除人以外的动植物而言,拥有该动植物资源的地区能否享有一定的权利。如何保护由生物遗传资源所引发的利益纠纷,已经是随着生物基因技术发展所不得不面临和解决的问题。
众所周知,人类的很多疾病都是由基因引起的,如果能够找到这些致病基因,那么就可以进行早期诊断,并进而找到战胜这种疾病的基因疗法。但是,在采集基因进行研究的时候就会产生冲突。1987年,一位叫狄比·格连勃的人找到了美国迈阿密儿童医院的医生兼分子生物学家鲁宾·马达龙,希望这位医生能够利用研制的分子探针检查和诊断他两个孩子的疾病,同时恳求能找到一种治疗这种罕见疾病的方法。狄比·格连勃的两个孩子患的都是一种名为”嘉拿芬“的疾病,这种疾病具有种族遗传性,主要出现在犹太人中。”嘉拿芬“病可以说是一种典型的基因病,患者的第17号染色体上的部分基因产生突变,造成天门冬氨酸酰基酶的缺乏,导致中枢神经系统缓慢受到破坏,最终患者会因此而死亡。
马达龙医生同意了格连勃的请求,从他的两个孩子身上提取了血样和组织样本,此后许多患”嘉拿芬“病的患儿家长听到了这个消息,纷纷表示支持。马达龙医生从而顺利地从大量患儿身上采到了血样和组织样本。1993年,马达龙医生发现了”嘉拿芬“病的基因,并发明了诊断该病的遗传学检测试验。马达龙所在的迈阿密儿童医院随后将此项技术申请了专利,并在1997年取得了该基因的专利权。
迈阿密儿童医院的行为引起了众多为”嘉拿芬“病的发现提供血样和组织样本的患者家长的不满,认为基因是从患者身上取下来的,只有他们可以处置这种基因,医院无权对基因享有权利。2000年10月,4位家长和3个非营利组织共同起诉马达龙和迈阿密儿童医院,请求法院禁止迈阿密儿童医院商业性使用”嘉拿芬“基因,并赔偿原告75000美元。迈阿密儿童医院只同意支付少量的经营许可证费作为赔偿,但遭到了原告的反对。原告认为迈阿密儿童医院试图靠经营许可证来阻止原告使用自己的基因。而且由于有许可证的限制,嘉拿芬基金会不得不中止免费为他人诊断”嘉拿芬“病的服务。
“嘉拿芬”一案提出了一个基因所有权的问题,这个所有权不同于基因专利权,而是指病人对于他体内的基因是否拥有权利。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提供基因帮助科学家获得研究成果的病人,可不可以对基因研究成果享有一定的权利,他们之间的利益怎么分配的问题。
类似“嘉拿芬”案的纠纷不断出现,史蒂夫·克朗和艾里·福斯与亚伦钻石研究中心的纠纷也是其中之一。史蒂夫·克朗和艾里·福斯的身体里都有一种抵御艾滋病毒的基因,他们长期接触艾滋病毒,但却安然无恙。当他们向纽约的亚伦钻石研究中心捐献了自己的血样进行试验后发现,他们的血液竟然可以抵抗艾滋病毒的侵袭。随后像“嘉拿芬”案中一样,亚伦钻石研究中心对发现的基因申请了专利。史蒂夫·克朗和艾里·福斯对未将其列为专利共有人非常不满,他们认为对艾滋病的免疫力是因为他们自身的原因,而非研究中心给予的,所以他们应该分享这项专利。而亚伦钻石研究中心则认为,史蒂夫·克朗和艾里·福斯没有在智力上对该基因的发现作出贡献,而且该基因专利权并没有给这个非营利性机构带来任何收益,所以他们两人不能成为专利共有人。
(二)基因提供者所享有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