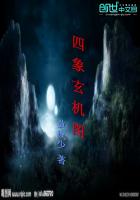如果说,“新世界”和“大世界”这种来自西方的大众休闲娱乐形式在上海的定型,被濡染上了中国乡村大型庙会的文化色彩,那么,一种与近代大工业、大商业紧密结合的复合型大众消费空间——“销品茂”(Shoppingmall),及其他一些经济、文化底蕴相似的休闲娱乐设施的出现,则把人们的文化经验引向了一种全新的,关于“现代性”的体验。在中国的现代商业中枢——南京路上,先施、永安、新新、大新四大公司,率先把西方资本主义的大型百货零售业与休闲娱乐业组合,开创了一种集现代购物和休闲娱乐于一体的大众消费空间。同传统的剥离式的休闲娱乐方式不同的是,“销品茂”通过不同功能空间之间的组接或交叉,把对现代物性的体验,与社交功利、休养愉悦、文化审美熔于一炉。先施公司屋顶花园里的饭店、酒吧、咖啡馆、旅馆,永安公司附设的大东旅社、天韵楼游乐场,大新公司5楼的交谊舞厅,与商场内的BVD内衣、HOUBIGANT香水、FLORSHEIM鞋、PilsnerArtExport啤酒、Fab洗衣粉、康克令水笔,及相机、留声机、录音机、自动汽炉这些现代产品,以及象征着现代科技进步的自动电梯、冷暖空调等基础设施,共同构成了一个庞大、丰裕、精致、新潮的消费环境和自足性的生活社区,使消费者恍若置身于一个与屋外普通生活截然不同的世界,确信踏上了商场内的自动电梯,也就踏上了通向现代的高速通道。现代资本主义经营的空间策略,在生产实体空间的同时,也在生产与此相应的文化心理空间。
事实上,至30年代,这种强调现代物性体验的空间策略已被广泛地应用于其他新兴的文化休闲娱乐场所。1932年开办的百乐门舞厅,以当时国际最流行的美国artdeco(阿黛可)建筑风格、考究的巴洛克式内部装潢和以现代科技为支撑的“弹簧地板”、“玻璃舞池”,成为当时男女“社交公开化”的重要载体。1933年,耗资百万金,配有美国RCA最新实音式有声电影放映机和最先进的冷气设施,2000个沙发座的大光明电影院落成。由著名捷克建筑师邬达克设计的室内环境有“宽敞的艺饰风格的大堂,三座喷泉,霓虹闪烁的巨幅遮帘以及淡绿色的盥洗室”。大光明以及奥登、卡尔登、恩派亚、夏令配克、中央、维多利亚、巴黎、上海、美琪、兰心等这些设施先进、风格各异的电影院或影戏院,成了当时上海“每日百万人消纳之所!”。
大型购物中心、大型游艺场、现代影戏院、回力球场、跑马厅、跑狗场、舞厅,以及散落在南京路、霞飞路、四川北路、静安寺等各个主要街区的咖啡馆、酒吧,与霓虹灯闪烁的橱窗、街景,奔驰在大街上的新款劳司莱斯汽车,构成了一种与四马路文化迥异的新型都市文化景观。在当时的新感觉派文艺刊物《新文艺》上,曾登载过一篇署名迷云,题为《现代人底娱乐姿态》的文章,以饱胀着热情的辞色,对这种文化形态进行了礼赞:
娱乐,这个写在过去的历史中不知道受过几许世间的白眼和凌辱——好一个有决断力的,壮胆的,幽秘着魔术似的,并且包满着肉底表现呀!
半世纪以前连影子都未曾出现过的新时代的产物——银幕,汽车,飞机,单纯而雅致的圆形与直线所构成的机械,把文艺复兴时代底古梦完全打破了的分离派底建筑物,asphalt的道路,加之以彻底的人工所建造的街道,甚至昼夜无别的延长!我们的兴味癫狂似的向那个目标奔驰着。
SPORTS,侦探小说,短篇和小品上的嗜爱——这也是求着极点之刺激的我们心境的一断片。
生命是短促的。我们所追求着的无非是流向快乐之途上的汹涌奔腾之潮和活现现地呼吸着的现代,今日,和瞬间。富于生气的,原色而壮丽的大协调!(迷云:《现代人底娱乐姿态》,载《新文艺》一卷第六号)如果我们再比较一下四马路的休闲娱乐文化中的“京式盆汤澡罢身,杏花楼畔又逡巡。贪看一出髦儿戏,也算风流队里人”的澡后看戏;“洞庭春色佐春茶,饮罢徐徐上小车。听说客从何处去,西金街内访桃花”的茶罢嫖妓;“万里云烟远近夸,冷笼陈土小壶茶。横陈短榻纲组里,更有何人肯忆家”的烟馆寻乐。就可以发觉,产生在20世纪初至30年代上海的休闲娱乐方式,无论在“形、筋、骨”或“精、气、神”诸方面,已与传统有了质的差别。现代休闲娱乐方式虽“不脱奢靡、麻醉的负面作用,却饱胀了热情,有种生命欢欣、跃动的气息”。
至此,一种以现代大工业和发达的商品经济为其结构底蕴,以资本运作和市场消费为其发动引擎的大众文化公共空间,在现代都市上海正式形成。
二、城市、时间与人:大众文化公共空间形成的原因
(一)城市:贸易中心的崛起与公共空间的形成
人们在谋生劳作之余,还需要休闲娱乐。在自然经济状态中,人与土地的关系非常密切,人很少有机会离开自己的土地,地域之间的社会交往和人员流动的程度也比较低。因此,中国传统的乡村生活及其休闲娱乐活动,是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包括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人文环境)中进行的。日常的休闲活动,就其范围而言,一般多以家庭、族亲、邻里为轴心进行,只是在农闲或年节时,才会有村社之间的公共性娱乐活动。就其形式而言,是建基于普遍匮乏的小农生活及其习俗之上的喝茶、聊天、宴客,或迎神、观戏等。就其功能而言,是以休憩和延续传统为主要价值取向。因此,在中国乡村,很少有常设性的、规模化的公共休闲娱乐场所,只是在一些商业较为发达的城镇才会有一些比较大的、固定性的茶馆、酒楼等,以满足本地居民及往来客商的休憩、享乐之需。
上海在开埠前,只是个偏远的小县城,其繁华程度远不及苏、杭等地,休闲娱乐场所自不足观。但自开埠通商后,中外商旅往来大幅度增加,据有关资料统计:上海的洋行1844年11家,1854年120家,1867年300家,1903年600余家。上海的商号1865年88家(租界),1906年3677家(租界),1908年7381家(包括华界),1909年10528家(包括华界)。1870年-1910年间,上海口岸的对外贸易额在全国总额中所占的比重在43.6%-63.6%之间浮动,远远超过了中国其他三个主要口岸城市广州、天津、汉口同期贸易额的总和(11.6%-18.9%)。自19世纪60年代起,上海已成为全国最大的通商城市和“远东第一大码头”,其经济功能远远超过了它的政治功能。这在通常以政治要素建市的中国古代城市发展史中是极为罕见的。因此,“近代上海的崛起改变了中国大城市的功能意义”。
不同于农民附着于土地,中外贸易活动的大增,导致了大范围的社会交往和人员流动,也导致了休闲娱乐活动范围、功能的变异。首先,就范围而言,人们的日常休闲活动已不再局限于家庭、家族、邻里、村社,而是更加社会化、市场化,更多地在商业化的公共空间里进行,由此,大量常设性的公共休闲娱乐场所应运而生。其次,就功能而言,这些公共场所已不再仅仅局限于满足休憩、享乐之需,而是将休闲娱乐功能与社交功能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了。中国近代史研究专家李长莉指出:在晚清上海,中高档的酒楼、餐馆里,大多是些请客聚餐的饭局:“肴分满汉尽珍羞,室静情堪畅叙幽。请客谁家最冠冕,同兴楼与庆兴楼”。茶馆不再只是单纯解渴消乏的地方:“夫别处茶室之设,不过涤烦解渴,聚语消闲。而沪上为宾主酬应之区、士女游观之所”。戏馆也成了士商社交应酬、请客聚会的场所:“沪上为众商聚会之所,凡举会请客者咸邀入戏馆,利其便也”。烟馆也不再只是吸烟过瘾的地方:“烟铺之设,原以便行人之瘾,何处无之”,而上海的一些高档烟馆,“华其居,丽其设,精其器,工其烟,是以海内文人商贾,无不闻其名,仰其景,偶一至沪,甫停骖即往一爽素志。故是设不但便行人之瘾,实乃备文人巨贾之清玩。是以文人巨贾或论诗文,或谈交易,是借烟以畅叙幽情也”。由是,这些公共空间在供人消遣娱乐的同时,也在促进市场交换、加速信息流通、聚纳八方来客和结构新的社会关系。
(二)时间:劳动与闲暇的分离及休闲时间的延长
在以往小农生产方式下,经济增长的方式主要依赖于劳动时间和劳动量的投入,休闲娱乐在这种粗放型的生产方式中,往往被认为是奢靡,是被正统伦理排斥在中心之外的。有限的休闲娱乐活动则严格地受制于节气、昼夜等自然条件影响,如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农忙时劳作、农闲时娱乐。但大工业生产和商品经济带来的一个直接结果是劳动时间和闲暇时间的明确分离。这对人们的休闲生活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一是商业活动及市场谋生方式,不再像农业生产那样把人整日拴在土地上,具有更多的灵活性和自由度,遂产生了较多的可支配时间,可用来进行休闲娱乐。二是大商业或大工业的组织方式,改变了人们在自然经济状态中,作息时间的分配受制于自然节气、生态条件等不定因素的混沌状态,使劳动时间和闲暇时间之间的区分明晰化、固定化,如定时工作制的出现和礼拜天休息等。人们的收入,也大多不再与劳动时间的投入直接挂钩,这使得休闲娱乐活动有可能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此外,城市化过程中的市政建设、能源利用,也直接影响了人们休闲娱乐活动的时间分配和便利程度,如街灯的设置、煤气灯及后来电灯的普及,使人们的社会生活不再受昼夜的约束,由此延长了人们的休闲时间。而马路的开辟、交通工具的增多,使人们的休闲活动不再受距离的限制。这种时间分配和空间安排上的“合理化”过程,对开埠后的上海社会生活产生了深刻而广泛的的影响。
先是租界里的洋行,把这种近代化的时间节奏带进了上海,并渐次扩散到整个市民社会。如西人工作定时、礼拜天休息,那些在洋行里工作的中国雇员首先随顺其俗,而那些与洋行有关的商务活动也依时而行。渐渐地,这种作息制度不仅影响了租界内与西人共事的中国人和与洋行有商务关系的中国商贾,也影响到了一般市民。至19世纪70年代初,这种作息习惯已成为租界内社会生活的主要节奏。人们白天从事各行各业,傍晚或周末便涌向各种休闲娱乐场所,由此造成了夜生活的繁荣和礼拜天休闲的习俗。当时有许多诗文记载了此种情景,如有记公司礼拜放假时景况的:“巨贾千般未足夸,洋商交易羡丝茶。每逢礼拜公司放,百万朱提散客家”;有记一般市民逢礼拜时喜悦心情的:“第一开心逢礼拜,家家车马候临门。娘姨寻客司空惯,不向书场向戏园”、“恰逢礼拜闲无事,好把京班仔细看”;有记人们在周末纵情逍遥的:“酒兴方阑戏馆招,才听弦索又笙箫。无端忙煞闲身汉,礼拜刚逢第六霄”、“礼拜日任人游玩焉,前一日曰礼拜六,是夜尤为热闹”;有记夜生活繁荣景象的:“洋场随处足逍遥,漫把情形笔墨描。大小戏园开满路,笙歌夜夜似元宵”。由此可见,夜生活和周末休闲,已成为上海社会生活的一个突出特征。
(三)人:市民社会的形成及其文化选择
上海开埠以后,传统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开始发生质的变化,原先建筑在小农经济上的宗法社会被留在了城外,“士农工商”的社会排序也发生了根本性的颠倒,一个以市场交换为生存法则的市民社会迅速地崛起,并深深地影响了城市文化生活的选择。
可以看出,贸易、商业、航运及其附属职业(服务业)占了绝大多数比列,这说明此时的上海已成为一个沟通海内外的贸易、商业中心城市。与以往附属于农业的传统城镇经济及其社会结构不同,这些依据新的社会分工而形成的职业人群,在上海构成了一个中西混居,以市场交换为生的近代市民社会。在日常文化选择上,他们更多的是依据市民社会的生活逻辑和世俗的欲求(如视日常休闲享乐为正当,具有道德合法性),通过市场消费的方式,选择适合自己的精神生活方式。正是由于这一消费群体及其精神需求的存在,上海大众文化公共空间的形成和发展,有了深厚的社会基础。至19世纪70年代,日常性的休闲娱乐活动在上海已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不仅仅是富商豪绅在各种休闲娱乐场所一掷千金,一般收入不多的普通市民也在工余寻找休闲娱乐。当时有人在记述上海的文化消费市场时谈到:在上海,像茶楼对饮、盆汤沐浴、书场听书、戏院观戏、飞车游观等,都已是无需太多花费的大众化休闲娱乐活动,那些受雇于人的店伙、账房、塾师等普通人,也可以在劳作之余,到这些场所去休闲娱乐一番,以解身心疲乏:“身非富人,依人作嫁,或为商伙,或为馆师,则碌碌终朝,当夕阳西匿,暝色末昏,亦将行此数者,以适一时之意,以解一日之烦”。这说明日常休闲娱乐已不再只是少数中上阶层的特权,而已是一般市民普遍拥有的一种大众化行为。休闲娱乐的大众化、世俗化,这正是社会生活方式近代化的一种趋向。
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上海大众文化生活及其公共空间的形成,是商品经济、城市社会的伴生物,是建筑在近代生产与消费之上的文化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它们构成了上海这座城市的文化底色。
三、空间的再生产:大众文化公共空间的当代重构
(一)聚纳、满足、缓冲:大众文化公共空间的三种功能指向
自改革开放以来,上海大众文化公共空间伴随着城市功能的恢复,获得了历史性的重构。据可获得的资料统计:截至2002年底,上海已有各类休闲娱乐场所48737个,其中舞厅717家,剧场336家,影院68家,卡拉OK厅1322家、音乐茶座(包括咖啡厅、酒吧)394家,音乐餐厅(其中兼有酒吧功能)508家,游乐场16家,文化馆45家,文化站234家。此外,各种以文化资源作为建构要素,体现着现代休闲理念的新型公共消费场所,如步行街、文化街、酒吧街、多功能购物中心、主题公园、大型健身房等也被渐次建造起来(上述这些统计资料,仅说明着常设性、实体性、亲历性的大众文化公共空间,并不包括网络、报刊、电视等虚拟性或间接性的大众传媒,以及文化节庆等非常设性载体在内)。随着这些大众文化公共空间的出现,城市的灯光再度亮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