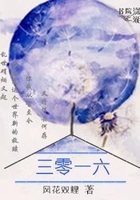大三的那个春节,轻歌过得并不开心,她与至善之间的联系时有时断,她不知道至善究竟在做什么,经常发短信给他没有回复,打电话给他也没人接听。偶尔至善接听轻歌的电话,他的语气总是很疏离很冷淡。轻歌不知道他到底发了什么事,好不容易等到他接听她的电话,问他究竟是怎么了,他总说没什么,然后以各种各样的理由挂了电话,再打过去,就是没人接听了。
整个寒假,她都过得心神不宁的,似乎有什么不详的事情发生的。他们之间相隔千里,一在成都,一在南京,彼此之间只能通过电话联系,至善这样不接她的电话,她也只能干着急。好不容易盼到了开学,她直接买张机票就飞回了南京。
轻歌上飞机前给至善发了短信,他没回,又给他打了电话,他也没接。她心里有点生气了,他这一个寒假都不回短信不接电话究竟是什么意思,难道是要跟她分手吗?轻歌为自己的这个想法吓了一跳,这绝对不可能的,至善说过会跟她永远在一起永远不分离,他绝对不是个言而无信的人。
她揣着一肚子疑问回到了学校,425宿舍的其他人也已经陆续回校了。一回到宿舍,直接扔下行李到教师宿舍区去找至善。
至善家的铁门是紧闭的,她站在门外敲了半天的门,一直都没人开门。正当她转身准备离开时,忽然发现至善就站在楼梯上,手上提着新鲜蔬菜,显然是刚刚从外面买菜回来。
这段时间被他冷落的委屈一下就涌上来了,她像个小媳妇一样别扭的站在至善家门外,红了两个眼睛说:“你到哪儿去了?我给你发短信说我回南京了,你也不回短信,打电话也不接,你怎么了嘛?”她原本是想冲他发脾气的,可这一点点火焰在一个多月没见他一个多月累积的思念的打压下消失殆尽了,剩下的只有满满的想念。
至善看她的目光没有一点点感情,那黑框眼镜下的双眸依旧清澈剔透,可就是冰冷得像是从深渊里掘出的万年寒冰,没有一丝温度。他那两片薄薄的嘴唇里吐出来的话同样令人冷彻骨髓:“你来这里做什么?”
初春的季节,轻歌只觉得寒意一点一点通过衣服渗透进来。一瞬间,她有点晕眩,这一切都不是真的吧?这一切都只是在做梦吗?为什么那么不真实?她的小纯子从来不会这样对她的,对,这一定是在梦里,一定是一个讨厌的噩梦,她必须用梦里醒过来。她撸起袖子,用牙齿狠狠的在自己的手腕上咬了一下。手腕传来尖锐的痛感,口里竟然尝到了血腥的味道。所有的感觉都在告诉她,这不是一个梦。
至善冲上来,拿起被她咬过的右手看了一下,上面有一排深刻的牙印,甚至有微小的红色渗了出来,可想而知,她刚才那一下咬得非常用力。他重重的甩开她的右手,用冰冷得极尽残酷的语气说着:“你有病吗?喜欢自残也请到别处去。”他越过轻歌,掏出钥匙打开了自家铁门。
就在他即将踏入房间的一瞬间,轻歌猛然抱住他的腰,哭喊着说:“小纯子,你到底是怎了?你为什么不理我?我哪里做得不好惹你生气了,你告诉我啊!你告诉我,我可以改,你别再生气了好不好?你别用这种冷漠的态度对待我,我受不了,我真的受不了。”
至善浑身都在发抖,镜框下的眼睛依然通红,像是马上就要流出血来了。他脸上的表情无比悲切,似乎正压抑着巨大的痛苦。他用力掰开轻歌的手,将她重重一推,在轻歌跌出屋外的同时毫不留情的关上了房门。
轻歌就这样怔怔的坐在地上看着至善家的铁门,眼里的泪水像决堤的瀑布般往下淌。她的小纯子,她的至善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不,她不能接受,他对她甚至连一个解释一个说法都没有,难道就这样毫无理由的将她绝之门外吗?
她绝不接受,就算他已经厌恶她,已经不喜欢她了,就算是要分手,要一刀两断,她也要他一个说法。她从地上爬起来,拼命地敲打着至善家的门,厚实的铁门发出沉闷的声音。她一边敲一边哭喊:“贺至善,你给我出来!你这样不声不响躲在里面算什么?你出来啊!”
至善就坐上客厅的地板上,刚买的西红柿散落了一地。他仰面对着墙壁上父亲的遗照,泪水从眼角滚落。他抱紧自己的双腿,将面埋在腿间不可抑制的呜咽起来,身体剧烈颤抖着。
轻歌还在敲打着铁门,手掌已经拍得发麻,她仍不愿意离开。轻歌的脸上满是泪痕,她不走,不甘心,无论如何也要贺至善给她一个说话。她不知在门外站了多久,似乎泪水已经流干了,喉咙里再也发不出一丝一毫的声音,冷风袭过,只感觉脸上冰凉凉的一片。她只是机械麻木地重复着拍门这个动作,表情呆滞得就像一尊将要破碎的木偶。
铁门哐当一声向里打开了,轻歌的右手僵在半空中,掌心的皮肤已经被不太平整且锈迹斑斑的铁门磨破,鲜血渗出来又很快凝固干涸了,只在手掌里留下一块块乌红的血印。
至善站在门里,轻歌站在门外。他依旧冷漠的目光从轻歌的右手掌心转到她的脸上,一句薄情的话从他的嘴里说了出来:“我们分手吧!”
轻歌的脸上露出愤恨的表情,一把拽住至善的衣服,双目瞠到最大死死地瞪着他:“为什么?到底是为什么?我要一个理由。”
“我要去美国了,去那边读博士,我妈妈在那边已经帮我联系好了一切。”
“去美国?”轻歌不解地看着他,就像在看一个陌生人,“你不是舍不得这边的一切吗?你不是说不去美国读书吗?为什么现在又突然告诉我你要去?你真的是贺至善吗,还是另外一个人?”
至善突然暴怒似的冲轻歌大吼道:“我为什么不去美国?那边的环境和条件哪样不比这里好?你看看国内的现状,搞研究的不好好搞研究,喜欢三天两头到记者面前现身说法。专家不是专家,教授不是教授。搞论文搞学术的抄,写文章写小说的抄,抄抄抄,抄了还能走红赚钱,在这种大环境下,谁还愿意潜心研究创作?有本事有能耐都想移民国外,那些个干部官员一个个都成了裸官,我凭什么还要留在这里?凭什么!?”
轻歌猛然向后退了一步,整个人好像傻了一样,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半晌,她才艰难地开口说:“就算你要去国外读书,也不需要放弃我们之间的感情啊!你又怎么知道我不愿意等你?又怎么知道我不愿意跟你一起去呢?”
至善最后看了她一眼,说了三个令她彻底绝望的字眼:“不需要!”
那扇铁门再次在她面前轰隆一声关上了,犹如彻底关闭了她心底最后一丝希望。她大学生涯中这段刻骨铭心的恋情在维系了一年后竟然就这样走到了终点,小纯子还是她爱的那个小纯子,至善却已经不是她的至善了。
轻歌抹着眼泪,一步一趑趄的离开了这个令她伤心的地方,她却不知道,四楼的某扇窗户里,一双流泪的双眸也在依依不舍的目送她离开。
从那天起,轻歌再也没见到至善。至善之于轻歌,就像严利之于小乖一样,只是人生命中的一个过客,匆匆出现,又匆匆消失了。
在轻歌的心里,她知道至善不是一个过客,哪怕他放弃了她,哪怕他伤害了她,哪怕他背弃了他们之间的诺言,他仍然不是一个过客,他是她生命中最最重要的人,是她深深爱过的人。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轻歌能够彻底从这段恋情里走出来,她能够重新爱上别人,并且组成幸福美满的家庭,有一个听话乖巧的孩子。但是,在轻歌的心底,她仍然无法忘记大学生涯里这一个给予了她爱与痛的男生,她仍然无法忘记他们之间曾经有过的快乐,以及分手时那种深入骨髓的痛。
大概只有这样的爱情,才能让一个女孩铭记一辈子;大概只有这样的爱情,才能让她多年后再想起这段感情时,仍能尝到一种涩涩的滋味。
轻歌的手机响了,依旧是那首熟悉的旋律,依旧是那段在字里行间透着淡淡忧伤的歌词:
我们都曾经明白。
也都曾经遗憾。
错过了爱就难以重来……
到哪里找回真爱。
找回所有遗憾。
爱的真相就能够解开。
多给我一些片段。
拼凑未知的意外。
失去记忆最初的爱。
听着这首歌,轻歌的泪水又来了……
他们分手后,轻歌消沉了很长一段时间,她患上了失眠症,夜里睡不着,早上又醒不了,吃东西吃不下,好不容易吃进去一点又反胃全都吐了出来。如此折磨了一个多星期,她的身体终于支持不住,晕倒在宿舍楼外。
宋白在得知这个消息后,抛下全剧组的人,从横店影视城赶到南京。躺在病床上的轻歌瘦极了,深陷的眼窝和突出的颧骨使得她原本精致漂亮的脸蛋此时看上去异常的苍白憔悴。宋白站在病房里,不由自主地握紧了拳头,额头上的青筋甚至因愤怒而凸显出来。站在他身边的罗小乖她们几个全都往后退了一步,似乎很怕他下一秒就爆发出来。
或许、或许她们不该将轻歌和至善的事情告诉宋白,可是如果不说,她们又怎么向宋白解释轻歌变成这样的原因呢?对小乖她们而言,宋白真的就像一颗定时炸弹一样,稍一不小,他就有可能爆炸。
轻歌病了,他大老远跑过来首先问罪的就是425宿舍的五个人。小乖她们只是普通的学生,无钱无权无背景,怎么得罪得起宋白这样的大神,所以当宋白冷着脸在轻歌病房里问究竟是怎么回事时,她们只好将轻歌和至善的事全盘拖出了。
宋白似乎在极力克制自己的脾气,他紧握着的拳头很快就松开了,然后转过身用冰冷的语气问她们五个:“那个男的现在在哪?”
小乖她们五个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磨蹭了好一会儿,小乖才结结巴巴地开口说:“不、不知道,我们也没、没再见过他了。”
“全部都出去。”宋白低着头冷森森地命令她们。
小乖不放心地说:“可是轻歌……”
“我叫你们全都滚出去!”宋白怒吼着打断她们。
赵飞燕拉了一下小乖,她们五人不敢再逗留,全都离开了这间病房。
宋白静静的坐到轻歌的床边,他伸手极尽温柔的抚摸着她的脸,却用极端愤怒的语气对沉睡中的轻歌说着:“你为什么要骗我?你说过你大学不会谈恋爱的,你那时明明在跟那个叫贺至善的男人谈恋爱,你居然还在电话里告诉我你没有。我以为你只是太年轻不懂我对你的感情,如今看来你并不是不懂,你只是刻意回避。夏轻歌,我那么爱护你,保护你,不让你在娱乐圈里受到一丝一毫的伤害,你就是这么回报我的吗?你以为像周冰这样的影后仅凭名气就能演女主角了?这个圈子里有名气有容貌有演技的人实在是太多太多了,不付出身体和尊严就能得到一切几乎是不可能的。夏轻歌,帝娥那个角色多少人挤破头皮,甚至把导演制片全都睡过来仍然得不到这个角色,你却轻轻松松得到了。我全心全意的爱你,你就这样对我,你真的好可恶!”宋白的手忽然掐住轻歌脖子,并微微开始用力。
睡梦中的轻歌由于呼吸受阻,微微皱起了眉头。
宋白赶紧松开手,爱怜地抚着她颈部被他掐过的地方,紧张地说:“对不起轻歌,我不是故意的,我只是太生气了。你、你不要再欺骗我了,也不要再跟那个贺至善在一起,我什么都可以不计较,好不好?只要你乖乖的待在我身边,我什么都可以不在乎。”他小心翼翼的把轻歌搂进怀里,像呵护着一件世间最宝贵的珍品。“轻歌,我真的很不能没有你,那天早晨在成都见到你时,我就知道自己逃不开你了。不管你相不相信,我这一辈子都不会放你离开的。”
轻歌睡了很久,当她醒过来的时候,发现病房里站着两个人,而且都是她不认识的人。她有些恍惚,以为自己睡错了病房,挣扎着想爬起来,一个人却突然按住了她的左手。
“别动,你还在输液。”宋白就坐在她的床边。
轻歌听到宋白的声音,微微一惊:“宋师兄?”
宋白说:“嗯,你感觉好点了没?”
“好、好点了。”轻歌看着那两个围在她病床边冲她微笑的男子,仍然觉得有些紧张。
“不用担心,这位一个是我的特助姓李,还有一个是我的秘书,姓张。”宋白为轻歌一一做了介绍。
“特助?秘书?”轻歌仍然迷惑,宋白身边不是一直只有个助理吗?怎么又冒出两个李特助和张秘书了?
宋白让李特助拿来四份艺人签约合同,递给轻歌,说道:“这是和至诚传媒签约的合同,我已经让他们根据你的情况做了调整和修改,你看一下,没问题的话,就签吧!”
轻歌吃了一惊,她拿过四份合同,所以的项目已经填好,只等她签上自己的大名,这合同就正式生效了。合同上,经纪人那一栏所签的名字竟然是宋白。她不解地说:“这、这是什么意思?”
宋白平静地说着:“签下这份合同,以后你就是至诚传媒旗下的艺人,我是你的经纪人。”
“什么?宋师兄是我的经纪人。”轻歌不明白,宋白自己也是艺人,怎么会变成至诚传媒的经纪人了,而且,宋白怎么又跟至诚传媒扯上关系了?他不是一直在拍中线影业制作的电影和电视剧么?
李特助替宋白解释道:“夏小姐,宋少现在已经是至诚传媒的副总裁了。”
“副总裁?”轻歌差点咬掉自己的舌头。
“是的,宋少的父亲宋志诚是我们至诚传媒的董事长兼总裁,宋少成为公司副总裁也是宋总的意思,毕竟将来至诚传媒是要交给宋少的。宋少拍完现在这部戏后,就不会再接拍任何戏了,他将专心从事管理工作,当然他在管理企业的同时,还会兼任做夏小姐您一个人的经纪人。”李特助在说“一个人”时刻意加重了语气。
轻歌在听李特助说完后,将目光转到宋白脸上:“你是至诚传媒老总的儿子?”
宋白点点头。
“那中线影业呢?”
“冯三军是我外公。”
轻歌张着嘴,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至诚传媒在上海,中线影业在北京,所以你说你两边都有家,对吧?”
宋白仍旧只是点头。
“原来你是宋大少,我真是有眼不识泰山了。我很奇怪,中线影业不管从资产规模各方面来讲,都比至诚传媒要强很多,中线还是上市企业,你为什么选择至诚不选择中线呢?反正一边是父亲一边是母亲,对你而言,两边都应该是一样的啊!”轻歌嘴边凝着一丝讥讽的笑。
宋白并不在乎,只说:“我从来不认为自己有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