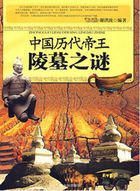众人拾柴火焰高,不大一会儿功夫,热气腾腾的饺子摆上了桌子。
外加竹笋肉片,爆炒肝尖,肉丝野蘑菇,素炒小白菜和一瓶沱牌。
沱牌酒不是好酒,但沱牌酒是川酒,川人喝川酒乃是一种品质——呵呵,我以为而已,非普遍真理,请勿推而广之。
喝酒吃饺子是不是新创意?应该不是吧?
有朋友在餐桌旁就必须有猪肉炒菜,这是古代川人的立下的规矩,我为四川的祖先喝彩,一则显其大方好客,二则可以大饱口福,与客同乐,特别是对长喉结的那类人来说更是有必要一以贯之的优良传统。
一片回锅肉,一口小酒它就是一个世界,爽!透!
秋洁拒绝了白酒,那就来红的,她没有再推辞,一小口红酒入口竟然也映红了她细嫩的脸庞,就像进入了陌生的森林,她的目光静静地从每个人身上拂过。
孕妇可以红酒吗?我是说就那么一点点,妻子同志礼貌地拒绝了,给我的笑那么醇,我如同掉进了酒缸,哪一个细胞不醉呢?
“嫂子,怎么可以不与民同乐呢?为了团聚,为了团结,你就和我们同甘共苦吧,干一杯!”鸭青举起酒杯。
“拜托,你脑子放水一点,再放水一点,好不好?”我义不容辞地担起维护维护妇女儿童正当权利的重任:“青同志,现在马上开始抢答,女人在什么情况下不可以举杯?”
我有点疑惑,不至于吧,他那么快就醉了?如果没醉,他起什么哄?
我说他的脑子该放水,是认为他的脑子进水了。
一个业已进水的脑子是聪明不起来的,换句话说就是他懵神志不清了,白痴。
“皓同志,这我就要批评你了,娶了媳妇忘了朋友,护色轻友的本质可见一斑,再说了,我说来一杯就是一杯酒嘛?不会吧?同志,你的思维能力也在迅速枯竭哦。”说完“哈哈哈哈”地大笑了。
类似得意忘形。
我晕。
原来如此啊,这么说,狼嘴里也能吐出象牙啊?
“得了,你们也别斗嘴了,你们真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见面就要斗嘴,你们也甭斗了,我喝,不就一杯酒吗?来,斟酒!”我亲爱的老婆慷慨激昂地举起了酒杯。
我们都愣住了,神经暂时短路,思维停滞,眼珠的转速陡减。
见没人给她斟酒,她就要从我手中夺酒瓶,自己给自己斟,我下意识地护住了瓶子,连一丝酒香也没有让溢出来。
没有白酒,她稍一欠身把红葡萄酒瓶握在手中,唰唰地就满了一杯,举杯就要往口里灌,动作有条不紊,一气呵成。
说时迟那时快,鸭青出其不意地挡住了她的杯子:“算了吧,嫂子,你知道我们哥儿俩闹惯了的,你又何必当真呢?为了我尚未谋面的侄子,请以茶代酒吧。”
“好吧,这是你说的哈,我可是竭尽全力配合了你们的工作了。”老婆顺势下坡,看看了看秋洁。
秋洁也望着她,她拿不透她眼前的这位姐姐。
事后,我曾问过妻子,假如鸭青不挡住你的杯子你还当真喝下那杯酒?她说,你才喝呢。
我想了半天什么意思,最后我懂了:她不过是做做样子,在另一个女人目前展示胆量,言其意我不会给我老公丢脸,哪怕是喝酒,再言其意就是我和老公是一条绳子的两股,不可分离,你最好歇菜。
女人啊。
看来,懂女人的前提是起码、至少、总要、必须懂一点心理学常识。
谈笑间,酒精进入了我们的每一个毛孔,我们冷落了饺子。
我们的的确确冷落了饺子,饺子在桌子上神态自若地冒着热气,一点也不感到委屈。
但是,我们有违初衷。
“亲爱的饺子啊,我爱你!”说着,我就夹了一个放在嘴里,津津有味地磨起了门牙以及槽牙。
于是大家都向饺子示好,一个又一个饺子香消玉殒,结束了它们短暂而美好的花样年华。
“咯嘣!”一声,鸭青惊喜了:“硬币!”一个五毛的硬币在鸭青手上闪着黄澄澄的光芒。
包饺子的时候我问为什么包五毛的而不是一元的,秋洁和老婆都说两个五毛代表两颗分离的心,它们相遇就代表完整、幸福吉祥,我哑然。
“咯嘣!”一个硬币出现在我宝贝的妻子的手上,她的眉微微蹇起。
鸭青不知所措,秋洁的眉展开了许多。
一丝不悦拥上我的心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