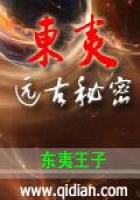在扎日南木措周围,星罗棋布有许多逐水草而居的藏宅村落。那些才冒出嫩芽的小草,究竟要侍奉多少牛羊呢?压在它们身上的负荷该是沉重的?这些绿洲的命运与海子的命运一样,也在不断萎缩、衰竭,被寸草不生的砂砾所替代。再把我们的视线拓宽到整个青藏高原,草场快速退化,世世代代生存的野生精灵正遭到空前的屠杀。藏羚羊濒临灭绝,野牦牛、野驴、野马、黑颈鹤等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减少。原本平衡的生态环境被人类的双手强行给打破了。几年前在双湖工作过的同事告诉我,那儿的动物根本不怕人,常常是车让它们,而不是它们让车。如今这种情形很难看到了。人类文明的车轮每碾过一片土地,那儿的生态便会遭到一次毁灭性的打击。这海拔4500余米的藏北高原也不能幸免于难吗?
全世界的目光都注视着这地球上的最后一片净土。六年前,一代旅行家余纯顺徒步穿越藏北无人区后感叹道:“阿里是地球上的一块无法替代、无法复制、甚至无法破坏的净土。”藏北的确是地球上任何其他地方都无法比拟的,如今这片神圣的净土也正慑服于人类的力量。
风大了,海子涌起的波浪拍打在湖岸上“哗哗哗”直响,岸边的沙滩上滚动着团团水花。扎日南木措的湛蓝又加深了。这份醉人的湛蓝能像蓝天永存吗?在无数年之后,它还能与青藏高原同在吗?在远处的湖面上,跳跃着若有若无的千丝万缕般的雾状物,都是强烈的蒸发作用的产物,那是扎日南木措在流泪。它的泪会流干吗?
四、六月飞雪
走进藏北的人们常这样形容那儿的气候:“一年无四季,一天有四季。”藏北属典型的内陆高寒气候,年温差较小,春夏秋冬四季不明显,日温差却很大,昼夜温差往往可达30多度。早晨寒风劲吹,天寒地冻,中午却烈日高照,炎热难当。在藏北工作的日子里,如果运气稍差,自己也数不清到底要经历几次烈日与风雪的轮回。
那是6月中旬的一天,我们作一套花岗岩体的调查工作。车翻上山口,那儿有一不大的玛尼堆,司机学着藏族司机绕了玛尼堆一圈,向山神致敬。由于前几日运气特差,他希望此举能给今日的工作带来些好运。在藏北,和恶劣的自然环境相比,人类的力量是微不足道的,就是我们这些唯物主义者有时也会暗暗求助于冥冥之中的上帝。也难怪宗教会在西藏社会中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在人类的力量还无法克服自然界的灾害时,只能祈祷神灵,这是形势使然。然而,司机的敬祭并未给我们带来好运,翻过山口还未行1000米,我们的车又抛锚了。
司机检查了一下车子,叹了口气,说一时半会儿修不好。前面的露头点仅有七八百米远。再望望长空,虽然有几团乌云压在南边的天际,但此刻头顶还是湛蓝湛蓝的一片,估计坏天气还不会马上到来。我让司机把车修好后开到那边来接我。自己背上背包向工作点步行而去。
那几团乌云发展速度之猛是我始料未及的。几团黑东西迅速向我这边移来,并不断扩张,不一会儿,整个天空便已铺满了厚厚的一层水彩墨。几分钟前还沐浴着我的阳光被挡在了云层之外。随着乌云,刺骨的寒风从山边扑了过来。山上被白茫茫的雾样的东西给笼罩了。我知道那里已开始下雪。根据经验,那雪花很快便会飘临到我的头上。我赶紧收拾好图纸和记录本,向小车跑去。藏北的原野,到处都是光秃秃的,是找不到任何躲避之处的。
尽管抓紧了时间,但我还是比风雪推进的速度慢了半拍。在距车两三百米的地方,我被茫茫白雪给淹没了。先是一阵风扑面压来,我的帽子被吹落在地,我迅速弯腰抓住它。我的腰还没站直,豌豆般大的冰雹就打将了下来。这些白雪球打在头上、脸上、颈上,有些滑进背脊,冰凉如刀割。冰雹轰炸完头阵,接踵而至的是漫天飞舞飘飘洒洒的鹅毛大雪。大片大片的雪花在狂风中打着旋,飘洒在天地间。这天是6月中旬,四季划分中应属仲夏的普普通通的一天。当内地的人们还不得不吹着空调以驱除夏日的酷暑时,也许很难想象在藏北的我正享受着大自然一种怎样的“恩赐”。
我很快变成了一个雪人,冻得牙齿“咯咯咯”直打架。离开车时,太阳很好,所以把羽绒服留在了车上,身上仅穿了一件毛衣。在这样的寒雪中,人是坚持不了多久的。在西伯利亚的雪原中,人们发掘出了冰冻的猛玛象化石。耐寒性极强的猛玛象都未能从雪灾中逃脱,更何况乎人。我必须躲进车去。逆风雪而行并非易事,我一扑一拜,看起来很像太空漫步。这种“漫步”绝无浪漫可言。我是在逃命呀。
我跌跌撞撞来到车前,打开车门钻了进去。抹掉额头上的雪,才发现司机并不在车上。举目外望,他正站在外面向我招手。风大,他一人无法将车厢盖上。我再次冲进风雪里,和他一起用尽全力把盖子盖上。
司机说此处不能久留,气温陡降,怕水箱里的水冻结成冰损坏车子。车窗外雪越下越大,能见度已降到十几米。我先用GPS定位仪测出我们所在的位置并在图上标绘出来,再用罗盘测出下山的方向。司机发动马达,车慢慢向山下驶去。
前面是一条坡度较缓的沟,大概有三千米长。我们必须从这条沟下山去,然后回宿营地。从地形图和实地坡形看,汽车可以开下去。司机喝了点水,吸了一支烟,然后打起精神小心翼翼向沟下驶去。
这坡远看起来整体较缓,在局部地方却并不是这么一回事。一些陡坎隐藏其中,远看根本就看不出来。加上大雪封路,无疑又加大了行车的难度。但那些陡坎都被我们一一抛在身后。前半段坡总算有惊无险地过来了,行至沟的中央,有一道五六米高的陡坎横在前面。由地理位置和地形判断,陡坎系冰川作用堆积而成,上面全是松散砾石。车开上去,砾石极易滑动,造成车翻人亡。更何况现在上面覆了一层雪。使得跨越难度倍增。
司机停好车,站在陡坎边看了半天,仍找不出可以下去的“路”要想再退回到山顶,已是不能了。上不能上,下不能下,我们真是走到了进退维谷的境地。唯一可以安全脱身的办法便是丢弃小车,人步行下去。然而车是我们项目最贵重的资产,无论如何也不能丢弃的。司机把烟屁股一扔,对我说:“你下去走路,我开过这道陡坎你再上车。”司机是出于对我的安全考虑。他单独驾车下去,即使车翻人亡,遇难的也只是他一个人。他的这种关心是我所不能接受的。在同一片阵地并肩战斗的战友,岂有把危险抛给战友,把安全留于自己的。我坚决拒绝了他。在此种情况下,人最需要的是对自己有信心,而信心又来源于同事的无限信任。我们重新回到车上。司机先把车摆端正,让车身垂直于陡坎,然后敛神屏气,蜗牛般向陡坎下滑去。车尾高高翘起,我前额贴着挡风玻璃,双手紧握住前面的扶手。司机稳稳地把住方向盘,脚死死地踩住刹车。车完全在靠下坠力滑行。滑至陡坎的中央,雪下面的砾石不堪重负,纷纷挣脱泥土的束缚向陡坎下滚去。车失去了支撑点,随着坠石往下飞去。先是一种失重的轻飘感觉,继之人在椅子上重重撞击了一下,人被高高弹起,头再在车顶篷上撞击一下,车便稳稳地停了下来,而且是四轮着地。后面陡坎上的乱石还在往下滚。这种惊险动作很多人也许只有在电影里才能见到。
我侧脸看司机。他正闭着眼睛,痉挛般地瘫坐在椅子里。在这大雪纷飞天寒地冻的天气里,他的鬓角处却沁着两颗汗珠,他的身子在微微颤抖。这位在驾驶室里摸爬滚打20年经验丰富的司机,如此惊心动魄的遭遇也许还是第一次吧?
五、陷车
6月底,在我们的野外工作接近尾声时,一场大雪却把我们一连困了几天。在海拔5000多米的荒野,被困雪中的痛苦可想而知。大家心里都憋着一股劲,希望能一气呵成做完所有的野外工作后往山下撤。长时间在生命禁区线以上工作,身体内脏各器官一直处于超负荷状态,加之缺乏维生素等营养的补给,我们中的每一位都被扭曲得变了人形,十多个人不论年长年轻都无一例外地浮肿了,个个看起来胖胖的。我们天天都盼望着雪能融化得快一点,让我们的煎熬少一点。所以那天一大早,当帐篷周围的雪刚刚化尽,我们就迫不及待地吹响了上山的号角。
车一路颠簸着穿过一片沼泽,爬上了一个海拔5700余米的平台。平台地势高、气温低,雪融化得慢。山脚的雪已融化殆尽,此处却还是白茫茫的一片。车行驶在上面,一点也不觉颠簸,司机戏称为白色高速公路。一则指车行在上面平稳;二则指雪表面看起来平平展展,下面却隐藏着丛丛杀机,稍不留神车便会陷进去。我们提心吊胆走了一大半,眼看着车就要走出雪地了,突然车后身一坠,两后轮掉进了陷阱里。
我们只在心里叹息了一声,感慨今天出师不利,在藏北工作,陷车是家常便饭,甚至成了我们工作中一道凝重的风景线。在无数次痛苦的实践中,我们摸索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自救方法。下车查看,两后轮的大半部分陷了下去。此处为一凹地,大雪之后连晴几日,融化的雪水无法排泄,淤积于此,表面看起来还硬朗,实则下面却是松散的软泥。车辆陷在其中,根本无法动弹。细看轮边,已沁出了汪汪的浊水。这种陷车唯一的自救方法就是用千斤顶把车身顶起来,往轮胎下垫石块。先往车下垫一木板,以最大限度减少千斤顶对地面的压强。尽管如此,当千斤顶伸长时,不是车身往上升,而是木块不断往泥土里陷。此招宣告失败。我们最后可做的便是原地等待援兵的到来。
下午6时,救援车强行突破两条河流,兜了好几个圈才爬上平台发现我们。此时,要靠近我们已比早晨难出十倍。经过一天的日照,早晨成片的雪地已变成块块雪斑,雪水积攒成一个连一个的洼地,汽车甚难跨越。救援车先绕到山脚下,取道积水较少的坡地,才得以来到我们的车前。
在救援车的拉动下,我们的车得以脱离泥潭。可是当两辆车在向外突围时,又分别被陷住了,脱不得身。
太阳已掉到西边那座无名山峰的背后,天际处燃烧的晚霞正逐渐变淡。气温迅速下降,高原的夜风吹得人直打寒战。司机的鞋袜在拖车时被打湿,不胜御寒。他把它脱下来,取而代之套上几只样品口袋。我的肚子叽里呱啦直响。中午只凑合着吃了半罐八宝粥,产生的几卡热量早被消耗殆尽。同时,我感到一阵阵头晕。司机也直喘大气,说头痛得厉害。这是高原反应。我们所处的海拔高度快接近5800米了。
我们唯一得救的希望只能寄托于另外两辆车。晚上10时从电台传来的消息是,在暮色中两辆车找不到过河的地方。此后,电台中断了。我们不得不作好最坏的心理准备——在此过一夜。做地质工作,没有帐篷露宿荒野本不算稀奇,可是在海拔5700多米的生命禁区露宿不知此前有没有先例。饥饿、寒冷都是对人的严峻考验。我们互相鼓励提醒不要睡着。在如此严寒的夜里,睡着很易感冒。
晚上11时许,中断多时的电台终于传来消息,那两辆车已第三次摸黑从日(日喀则)-阿(阿里狮泉河)公路出发了。1时许,又传来消息,一辆车已陷入泥沙。我们的四辆车中未陷的只剩下一辆了。如果那一辆再不幸被陷,后果将不堪设想。我们建议那辆车原路折回或原地等待。但队友仍坚持找寻。他们也清楚,黑夜里,在茫茫荒野找人相当困难不说,即使找到,今夜也不可能把所有的车都救出重围。最终结果也顶多是在此露宿的人多几个而已。他们知难而为之,对我们是莫大的鼓励。我很感激他们。说实在的,我们在静待,他们在行动,危险远大于我们。黑夜,在这遍布陷阱的荒野行车,不但极易陷车,而且很易车翻人亡。本来他们可以待在帐篷里舒舒服服过一夜,而不来这儿受罪。当他们试了两次都无法渡过两条冰水河时,从各个方面讲已是仁尽义至而可问心无愧返回宿营地。可他们没有。在藏北的这几个月里,我们正是靠着这种亲密无间的团队精神,克服了一个又一个的难关。也正因为有了一个团结强大的集体支撑,每当我徒步于渺无人烟的千山万壑时,心头才会是踏踏实实的。
凌晨3时,救援车的车灯终于出现在了我们的视野之内。司机用车灯向他们打着信号。又过了一个多小时,救援车绕到了我们的车面前。试了一下,没有把车拖起来。大家商量决定:所有的人挤在两辆车里(这样可以增加车内温度),就地休息,待天明才开始挖车。
所有的人都是早晨吃了点饭,中午都是吃的干粮,加之连续行车,人早已疲乏得不行。一会儿,同事们便喘着粗气睡过去了。我也同样疲惫,浑身像散了架,然而在我的思想深处,一种游丝样的东西牵绕着我,使我无法入眠。突然间,心里升起一种强烈的冲动,想到外面走走。于是打开车门,离开了“温暖”的车厢。
外面冷得像个大冰窖,夜风吹在脸上,寒气直往骨子里钻。我响亮地打了个喷嚏,随即稳住了自己,既然出来,我就不会轻易缩回去。此刻,白天那雪水积成的洼地已结成块块寒冰,踩上去咯吱咯吱直响。藏北的夜静得出奇,天地间一点声响也没有。冈底斯巍巍的山峦显得静谧而和谐。站在夜中,侧耳倾听,微微的细风中仿佛萦绕着因曷陀尊者(因曷陀尊者为藏传佛教的十六尊者之一,相传住在冈底斯山上)为天下芸芸众生祈祷的福音。今夜是一个晴朗之夜,月色清柔,深邃的夜空中稀稀疏疏地缀着几颗若隐若现的星星。在藏北,天地间的距离拉得是如此之近,几朵浮云仿佛伸手便可触及。在家乡,月朗星稀的夜空是高远的。我委实想念家里的亲人了。来西藏也快三个月了,我无时无刻不牵挂着他们,尤其是在这种身处绝境的时候。
挟着一身寒气回到车上,打了一会儿小盹,便被同事叫醒。睁眼一看,天已蒙蒙亮。揉揉眼睛,即开始挖车。
早晨,土还被冻着,找石头是件相当费力的事。先用钢钎把冰层砸开,再撬松石头。把车轮胎垫平,另一辆车一带,车脱离了陷阱。大家上车,没走几步,刚才还充当救援车的那辆车碾破土表面的冰层,四个车轮全陷了下去。就这样几步一陷,当我们把四辆车全部从陷阱中救出来,并突出那片重围时已是下午5点钟了。这期间,我们一直在海拔5700余米的地方干着最繁重的体力活,从没停歇,没吃一粒米,没喝一滴水。
下午6时,四辆伤痕累累的小车载着疲惫不堪的我们终于回到了日-阿公路。司机把车停在路边,点燃一支烟悠悠地抽起来。我回首望那片困住我们的地方,在晚霞的映照下,那红色的山峰像燃烧的焰火,上面残雪晶光莹莹,远看上去,那儿什么痕迹也没有,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一般,平静如初。不知为何,我的泪泉又一次沁湿了我的眼睛。
结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