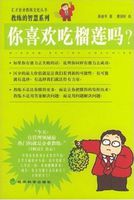晏雨跃下房顶,跳入一条无人的巷中,把张放松开,让他落到了地上,“你能自己走?”
“别把我想得那么不禁打。”张放扶着苔痕斑驳的土坯墙壁站起身,然后靠在上面,咧开嘴冲着晏雨笑,“你怎么会在那里?”
晏雨的声调依旧闲淡,“田夫子说花会是梧丘的盛事,让我出来看看,我便出来看,没想到——”她轻轻瞟了张放一眼,“还真看见了不少热闹,确是盛事。”
张放听了这话有点吐血,心想你是指我被人围殴吗?
“要不是昨天你一直在池塘边不离开,郭冲怎么会以为你——我有意,又怎么会找人追我?”张放看晏雨那副冷淡淡的样子,不知为何,总想撩拨撩拨。
“我为何要离开?”晏雨眉心微蹙,若梅心凝霜,让张放看得一呆。
“因为你不离开,所以惹来了流言蜚语。”他说。
“流言是因你孟浪无行才起,何必反怪我?”晏雨仍是冷着张脸道。
张放无言,心想那天确实是自己喝多了才惹起这事,赶紧转换话题,“喂,既然我给你惹来了流言,你为何今天还来救我?莫非,嘿嘿,你对少爷我并不讨厌?”
张放不是少爷,也知道这自大的姿态会惹人不喜,可他就是管不住自己的嘴。
果然晏雨又皱起眉头,片刻后她道:“流言自然而生,自然而止,与我无干。”顿了顿又道:“至于相救之事,你这人虽轻浮无行,但也罪不及死,为何不救?救下你只因我认为该当如此,与你是谁没关系,你也不须心存感激。”
张放一愣,心想这小妞难道是个外冷内热?忽然他想起个问题来,那可是从昨天开始就一直盘桓于他心头的疑问。
“郭冲好像认识你,你和他到底是什么关系?”
“没有关系。”
“怎么可能,别骗我,他那个样子好像是对你知根知底的,再说若没关系,他干嘛对昨天下午池塘边的事那么在乎?”
“没关系便是没关系,何必骗你。”晏雨漠然道,“你既然已可以走路,我便告辞了,此番之事,也望君深思,引以为戒,日后砥行君子之道,莫再虚浮轻狂。”说罢,她真得就转身离开。
那一袭素白书衫刚刚消失在窄巷的尽头,张放便贴着苔墙,滑到了地上。他捂着胸口,牙关紧咬,刚才言笑自若的模样其实只是装出来的,不想在个姑娘面前显出疼痛无力的样子而已。吴老三那一拳,还有后来击在胸口的大棍,都让他受伤不轻,尤其是胸口挨的那一下,如今还疼痛不已,也不知肋骨是不是折了。这种程度的伤他倒并非没受过,所以明白现在最好尽快找个大夫,包扎抹药。还好,他熟悉梧丘的大街小巷,知道这里已经离自己的小院不远。歇息了约莫半个时辰,他感到力气恢复了一些,便撑着墙壁再度站起。
一路蹒跚,所幸今天梧丘人大都跑去看花车和美女,街上空空荡荡,没什么人瞧见自己,让他还能稍有欣慰。拖着步子慢慢走,最后他终于回到家中。
所谓的家,其实就是个一进小院,坐落在东城的槐花里,虽然窄门陋巷,但他一直觉得自己很运气,因为他本来就一无所有,是书院田夫子认识管闾里门户的小吏,才能给他在城中找了这样一个地方做住处,况且左右都是殷实本分人家,他平时便靠着给街坊四邻写写榜文,算算帐,做些文字买卖过活,郡学里很多同窗是饿死都不肯沾商贾之事的,认为那是下贱行当,可张放不在乎,糊口比什么都重要。除此之外,郡学里还有些给贫寒学子的微薄贴补,田夫子也让张放领着,岱山郡是诗书礼仪之乡,虽然世道陵迟,人心不古,可这文化教育上较之别的地方,倒还是要重视些。
踉踉跄跄地推开户门,他倒在自家床榻上,觉得舒服了好多,过了片晌,他想起该叫人去找个给自己看伤的医工来,于是撑起身体,推开窗大喊:“小狸子——小狸子!”
小狸子是隔壁徐大娘家小儿子的乳名,因为在闾里的私塾上学,所以张放估摸着教子严格的徐大娘不会让他上街去看那些涂脂抹粉的艳丽女人,或许在家,便扯开嗓子大喊。
喊了两声,胸口疼痛,他便停了口,不多时,一个十岁左右的男孩跳进门来,头上两根羊角似的发辫晃来晃去。
“阿放哥,你这是咋了?”男孩看见张放歪倒在草榻上,衣服又脏又皱,龇着牙咧着嘴,不禁大惊。
“没事,你甭问。”张放不打算跟这么个小孩子解释那些事。
“哼,怕是去偷香窃玉,被人打了吧。”小狸子撇嘴道。
这猜的和真相倒有那么点相近,张放闻言胸口又是一痛,心想现在的孩子怎么都这么早熟!
“小小年纪,不知好好读书,净想着乱七八糟的事,小心等你娘回来我告诉她去。”张放吓唬道。
“你咋知道我娘不在家?”
“哼,今天是花会,你爹那个老不修肯定要去看,你娘还能放心?肯定跟去了。”
“你们这些大人可真是,有热闹自己去看,偏要把我们按在家里,等我长大了,肯定要带着我的孩儿一起去看花会。”
“行啦,离你教育下一代的时候还早着呢,先帮帮我吧,去把胡老头给我找来。”
“你等着。”小狸子转身跳出门去。
胡老头就是他要找的医工,说是能行医治病,其实也就是个江湖郎中。这闾里的人家虽殷实却不富裕,一般生病受伤,都找他。不一会儿,小狸子便领着他走进了张放的屋里。
“胡老头,你还真在家啊,怎么没去看花会?”
“呸!老夫我都这么大岁数了,还去凑那热闹做什么?让你们这些年轻力壮的小伙子一挤,还不就得摔个跟头呀。再说我在梧丘这几十年,花会年年看,还不就是那个样么,也就你们这些年轻人觉着新鲜。”胡医工说着,走到塌前,放下药箱,俯身查看张放伤情,问道:“今天又跟谁打架了?”
“吴老三。”
“吴老三!”胡医工立时惊地直起身子,花白的胡子一颤一颤,“北城那个号称梧丘第一侠的吴老三?”
张放嗤笑一声,“呸,什么侠,就是个混混头子,我看也没有多厉害。哎呦——轻点轻点,我这胸口挨了一棍。”
“你没事招惹他作甚?”老头轻轻撩开张放胸前衣襟。
“不是他,我是和他的主子郭冲有过节。”
“郭冲是谁?”
“就是郭家的二公子。”
“郭家?哪个郭家?”
“还有哪个,当然就是那个郭家了。”
“那个郭家!”胡医工猛一趔趄,准备探查伤情的右手不小心按在了张放胸口上,让他疼得倒吸冷气。
“哎呀!你个死老头,轻点行不行,你到底是来看我的病,还是来要我的命啊。”
“你的命还是自己留着吧,郭家的人早晚要来取。”胡医工把手拿开,白了张放一眼,“你这小子胆儿也忒大,平日到处闯祸就罢了,竟敢还惹到郭家的头上去,知不知道脑袋顶上,是有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