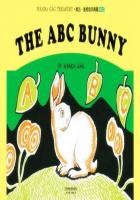?8
才留在他身边三十天,他就养成她若干习惯。
她习惯赖在他身上说话,习惯他环着她的腰弹琴,习惯有他的微笑陪她进餐,习惯他在床边说话,伴她入眠——
她是快乐的!打心底真正快乐。
“哥,我想过一个问题,假设当年我妈妈没嫁给储伯,假设我们没在那个时候碰上,你会不会、有可能爱上我?”
“不需假设,我会爱上你,你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女孩。”没有思索,纯粹的意识反应。
“你回答得太快,没用心,敷衍我。”
“爱情不需要思考,只需要凭感觉。如果生命肯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会好好珍惜。”
他的话温暖她的心,虽然一切都已来不及,但他说,他会珍惜。
她的爱情呵!总算有了价值、意义。
偎在他怀里,甜甜地笑开。
“哥,知不知道我第一次看见你的时候,心里想到什么?”
“想到什么?”拥着她,想起那两年,他的心没有这般踏实过。若能这样拥她一辈子——笑容跃上他的面容。
想象力永远在满足人类不能被满足的部分。
“王子!城堡里英勇的王子,带着一把金光闪闪的宝剑,骑着一匹白马,穿着盔甲,拯救落难的公主,然后用琴声安抚公主的恐惧不安,用低沉的嗓音对公主说:不要怕,我会保护你,不让恶龙来侵犯。”
“我并没有保护你。”甚至于,他根本就是那只恶龙,一点一点吞噬掉她的快乐。
“有,你忘记我们一起走路回家的时候吗?我还记得,有一个爱欺负我的男生,老是从我后面推我,你用球狠狠K他一下,还警告他,要是再欺负我,就去告诉我们老师,请他的家长来。从那以后,我就知道,你是我的屠龙英雄。”
“要是时间一直停留在那段日子,不知道有多好!”抚着她的头发,又细又绵密的头发,握在手中,沁鼻的清雅香味传来。他喜欢长头发的女孩,一直都喜欢!
“是啊!不过,要是真停留在那时,这个世界就要损失惨重,损失了你的音乐、损失了你的才华,有多少女孩子、爱乐人,都要掬起眼泪。”
“你说得太夸张。”
“不夸张,这几年,我剪下每一篇有关你的报道,珍藏起来,那里面的每个乐评人对你都有很高的评价。哥!你是我们全家人的骄傲。”
“为什么去搜集那些东西?”他问,想问出一份真心。
“因为——”能说因为爱吗?不能,他的感情已经标上专属标志,“因为你是我哥啊!我可以跟每个朋友很骄傲地说上一声:你看!这是我的哥哥,全世界最年轻、最有成就的小提琴家。”
“傻瓜!”这时候,他多希望自己不是她的哥哥。拥着她软软的身子,她就在他的怀里,一不小心就成了他的一部分。
拂开她的头发,在她肩颈交接处看见一块美丽的蝴蝶红斑。
“小优,你有一块很特殊的蝴蝶胎记,以前,我都没有注意到。”他的手在斑纹上轻轻搔刮,酥麻轻颤在她身体蔓延开。
又严重了?医生已经下通牒令,要她去住院,可是——怎舍得离开他?
“哥——不要,好痒——”抓起他的手,笑倒在他怀中,她和他靠得好近好近。这回,他们不止身体相近,心灵也是相依的。
“我信了你那句话。”英丰突如其来说。
“哪一句?”
“你是让天神谪贬的仙子,滚滚红尘数十年,谁能有幸握有你的手?”这句话是感慨,也是懊悔。
“曾经——我把它交到你手上,可是你不要——”
握住他的手,他的手很大,却握不住她的命运。细细画着他的掌纹,清晰干净的纹路,诉说着他的婚姻会美满。
于优祝福他。
“现在?还有机会吗?”只要她给他一分分可能,他一定会倾尽全力去争取。
“现在你要不起、我也给不起了——哥,好好珍惜你手中的幸福,嫂嫂是个好女人,值得你一生付出。”
一句话勾引出他的罪恶感,为什么总是只要小优在,他就将蜜秋彻底遗忘?
“又赖在哥哥身上?真受不了,我怎么会有一个这么爱撒娇的小姑!”
蜜秋的声音传来,于优忙挺身坐直,笑眼对人。
“嫂嫂,你坐。”于优招呼。
“坐哪里?我老公身边,还是你们对面。真是的,还没嫁进门,就要和小姑抢老公。”她笑说,女人特有的敏锐,嗅出他们兄妹间的不寻常。
“小气,不然以后我老公身体借你赖好了。”挪挪身子,于优作戏。
“老公?你连男朋友都没有,哪里来的老公?”英丰拍拍她的后脑勺。
“那可说不定,这次出远门,我去勾引一个金发帅哥,来个闪电结婚,到时,我会比嫂嫂更快成为‘已婚妇女’。”
“你啊!别多想,安分点儿,先乖乖当我的伴娘再说。”蜜秋眼光调向英丰,“我妈咪和爹地说,中国人有个习俗——父母去世百日内要赶快结婚,不然就要再等三年,他们的意思是希望——”
“我懂!”英丰截下她的话,不想在小优面前讨论这些。
“哥,嫂嫂,我先进房整理行李,你们继续谈论,不过别指望我当伴娘,要我当,得等我站得起来再说。”
深呼吸,藏起失意,她把自己挪进轮椅里,几个转动,她对着花园唤人,“阿强哥,麻烦你送我上楼。”
“等等,你要整什么行李,想搬回公寓?”英丰从她话中嗅出离别,心一惊,他快步走到于优面前,拉住她问。
“我说过,我要出国工作一段时间。”她说谎。
蜜秋的出现提醒她时光匆匆,戏早该落幕了。
“去多久?”他问得咄咄逼人。
“不确定,看工作进度,哥——我会尽快回来参加你的婚礼。”又骗人。
“能不去吗?”他皱起眉,“推掉它。”
“不行,工作是我的成就。十年前你执意要出国念书,我没拦你是不是?我还帮你整理行李,送你到机场。你要公平些,支持我、鼓励我,不要阻碍我。”
她还代替他挨撞。他记得,记得很清楚。吐口长气,他没权利反对。
“什么时候的飞机?我送你!”
抱起她,他主动送小优上楼、帮她整理行李,全然忘记客厅里还有一个等着他商议婚礼的未婚妻。
二○○○年初秋
相迎不道远,直至长风沙
他三十一岁,她二十七岁。
交出曲子,于优累坏了,趴在床上,一动也不想动。
这几年,她的独立让人刮目相看,她练琴、她作曲、她卖歌,她成了演艺界的红人。
人人都知道“余忧”是个多产的名作曲家,但除了和她合作的制作公司外,没有人知道,她是一个美丽清灵,却不良于行的女孩子。
五年前,她搬出储家后,就停止复健。
其实,她可以拄起拐杖一步步走得很稳,但她不走,一部轮椅,她欺骗自己最好的状态就是这样。
童昕取笑她,说她是个完美主义者,非要自己能在人群中走得优雅从容,像个一流的芭蕾舞者,才肯抛弃轮椅。她没反对。
也许吧!她一生的努力都在求完美、求登峰造极,所以学什么都是铆足全力去做,功课是、钢琴是、舞蹈是,连学走路都是,她只要把最好的一面呈现人前。小时候是怕挨打,长大了,怕什么?不清楚!
小语分析她这种争取掌声、注目的行为,解释为缺乏自信。
自信?她有过这东西吗?
闭起眼睛,想睡又怕睡,这些年,她常在夜里被噩梦惊醒,她梦见失速车子撞来,高高飞起、重重落下的是哥哥不是自己,她尖叫着送哥哥就医,谁知,整个医院里几十个染血小孩从四面八方聚来,指责她,怪她不小心、怒斥她害人——一声声责难在她脑中回荡——她是凶手、是凶手——
缠起棉被,她将自己紧密包裹,她想反驳、想告诉他们,她不是凶手,但她的声音是那样虚弱而缺乏说服力。
电话铃响,她挣扎起身,童昕、辛穗上班去了,赶了一夜稿子的小语好梦正酣,绝听不见铃声。
接起电话,轻轻一声喂,电话那头传来储伯的声音。
“小优,你还好吗?工作累不累?”他慈蔼的声音温着她的心。
“刚忙完,我正想休息几天。”
“上次——我跟你提过,英丰下一年度的工作计划在国内。”
“我知道,他回来,您一定很高兴。”他要回来了,这个想法让她好快乐,纵使不见面,她知道他就在离她不远的地方,知道储伯会常常捎来他的讯息。
“小优,英丰回来,你愿意回家住一段日子吗?你妈妈希望一家团圆。”
一家团圆?他承认过她是他的“家人”吗?她在电话这头沉默。
“你想躲他一辈子?”
一辈子——她的一辈子所剩不多,几个闪躲就能避开。
“储伯,我想——”
“英丰不会住在家里,他另外找了房子,如果你不想回来住,就回来吃顿饭吧!见见面、说说话,说不定他已经和以前不同,不再冷漠、不再拒人千里。”
见见面、说说话?她已经五年没“演戏”,再上场,她只会僵立在“舞台”之上。
“就一顿饭好吗?回来吃个饭,不然你妈妈会怀疑,好几次她问我——”
“储伯,我回去,什么时候?”阻下他的话,也阻下她心中的纷乱不安。
“星期天晚上,我们在家里替他接风。”
“我六点到。”切断电话,她全身都在发抖。
他要回来了,想过多少年、盼过多少日子,他终于要回来——他是一个事业有成、万众瞩目的音乐家,她却是一个不良于行的残障人士,再见面,要她情何以堪——
一家人见面客客气气,倒是英丰的未婚妻康蜜秋显得热络。她是个细心体贴的好女人,光是第一眼,淑娟就能确定。
“小优真是的,说六点到,都快七点了还不见人,真不好意思,要不,我们先吃饭,不等她了。”淑娟提议。
她又逃开了吗?储睿哲在心里暗忖。
“没关系,反正还不饿,我们再等等。”蜜秋一脸笑,这家人很好相处。
“应该让阿强去接。”睿哲自喃,这趟路对不常出门的小优来讲是件大工程。
“我在美国听妈咪说,小优是个很棒的舞者,她现在在哪里工作?”她的无心撞出淑娟一脸挫败。
“小优很久没跳舞——”叹过气,她忙笑开,不冷淡客人,“她现在在作词曲为生。”
“对不起,我说错话了吗?”蜜秋看看突然揪眉的睿哲和淑娟。
“没有,你不要多心——”当淑娟正要解释时,客厅门开,于优推轮椅进来,“小优,你回来了?”
“储伯、妈妈、哥——嫂嫂——对不起,我来晚了。”
再见她,英丰的心被重槌敲过,痛!他痛得皱眉。怎么会?一样的不食烟火、一样美得赛过精灵、一样的轻愁染眉——可是,她却——
很想一把拥她入怀,但他提醒自己,为什么要在国外一待多年?就是为了躲开她,不让自己心系于她、不让爱情毁掉自己对妈咪的忠诚,他不容许自己才见上一面就就此沉沦——脸是冷的、目光是寒的——心头却是热烈澎湃——
全身都在发抖,于优牢牢按住脸上笑得温婉的面皮,不让它掉落。她的王子就站在面前,教她魂萦梦系的脸——仍面无表情、仍吝啬对她一笑,他还是厌她,尽管是多年之后。
看见于优,蜜秋立即知道自己说错什么话,她寻来新话题,“你就是小优,我听妈咪说过好几次,她说你是个对音乐很敏锐的女孩子,她还常对学生说,你是她教过最有天分的女孩子呢!”
都是胡阿姨在跟她谈她吗?他从来就不提、不说她这个“妹妹”?是彻底忘记她,或是压根就不承认她和他有过关系——
“嫂嫂你好,你比照片上更漂亮。胡阿姨还好吗?”她客套虚应,心全落在那张不见表情的脸上。
他还好吗?想过她吗?忘记他们之间——肯定是忘了!否则怎会有一个体贴的“嫂嫂”站在眼前——
“嫂嫂”两字吐在嘴里,痛在心里,利刃一刀一刀切、一分一分割,她和痛苦在比赛,看谁僵持得久。
“她很好,就是想念你们。”
“有话大家到餐桌上讲。”淑娟招呼众人。
餐桌上,他保持静默,对于父亲的问话,他一概简单回复;于优也是安静的,惶惶然的心令她食不知味,入口的全是对他的思念。
他就在她眼前了,她仍然触不到他。苦笑,是她的心在坚持,告诉过自己几千次,他早就不属于她,只不过,痴心在,人不能不蠢——她的暗恋,早该沉入大海,任波浪撕碎。
停下筷,她抬眼看每个人的表情。
储伯、妈妈是热情而欣慰的,嫂嫂是愉快喜悦的,他呢——她探不到他的心思,一如多年之前。
有好一阵子,她几乎以为他已经不再恨自己,以为冷漠是他的性格使然,并不是专针对她,现下有些些明白——他仍是含恨的,不过年纪渐长,他不再口口声声将恨挂在嘴边,他选择用冷淡来阻隔她的关怀。
他的眼神对上她的,微微一颤,于优的碗差点滑落桌面。
蜜秋往他碗里夹菜,亲昵相依的身形刺痛着她的心,他们是相衬的一对,自信大方、事业有成,他们都是音乐人,心灵相通,这种婚姻没有不幸的机率。
垂下眉,长发覆盖脸庞,掩护了不该掉下的珍珠。水滴在米饭上,一摇晃,从缝隙间落入碗底,她——没有伤心。“对不起,我吃饱了,你们慢用。”笑挂得太勉强,一不注意就要掉落。
“小优,你吃得好少,你在节食吗?”蜜秋说。
摸摸自己的月亮脸,这阵子类固醇吃太多,水肿得厉害,不过,医生说病情控制住了,下回剂量会减少一点,到时就会回复。
“是啊!我去院子走走。”推起轮椅,将自己推离众人。她需要空间平复心情。
桑树长高,人在树下,任她怎样伸长手,都够不到枝枝节节。
月亮在树梢头懒懒挂起,清清冷冷的光线把她的影子在地上拖出好长一道。
关节又犯痛,免疫系统对她发动攻击。长期的药剂让于优严重的失眠、郁闷、水肿和胃出血,她知道接下来还会并发糖尿病、高血压、骨质疏松——最后死于肾衰竭。
死——其实已经不觉得恐怖,患病之初她还恐慌过,几年拖下来,太多的疼痛折磨,早把她的求生意志一点点消磨掉。
死,不过是停下心跳、停下和这世界的所有关连,但可以换得安宁和——不痛。
没生病时,不知道光是不痛,就是一种幸福。
她不怕死,却要争取活的机会,她的心还有牵挂,牵挂着母亲白发送黑发的伤痛,牵挂储伯、张爸张妈的疼惜,牵挂——那根早该断的爱情线。
所以,她和疾病搏斗,再痛她都不倒下、不喊输,就算现在,爱情城墙在她面前倾颓瓦解,她也不哭不喊。挫折,她受得太多,早练就出一副铜墙铁壁身。
“他们说,那场车祸中,你没事。”英丰的声音从身后传来。
心跳得飞快,那段在一起的日子从记忆中跃出,那时,她爱他!
肺喘得厉害,异乡游子的孤寂不安,在见到她时沉淀安定。那时,他爱她!
再见面,他不确定,她还爱他?但他肯定,他不能爱她!
理由?很简单,他不要输!他输了父亲、输了家庭,他不要再输掉自己的爱情。
她怔愣住。是他,他来了,为寻她而来?或是寻怨而来?
转过轮椅,她让自己和他面对面。他还是她记忆中的那个男人,只不过,时间把他洗炼得更成熟稳重,年轻时的霸气让沉稳取代。
“在那场车祸中我没事的。”面对他,她没打算说实话。她习惯了当他的糖衣锭,报喜不报忧,甜的给他,苦的留下自己尝。
“你的腿——”
“在另一场倒霉意外中造成的。哥——我没事,即使不走路,我也过得很好。”扬脸,她又在笑,“你这几年在国外很好,为什么突然回来?”
他没回答,定定地望住她,想在她眼中寻找欺骗的蛛丝马迹。
他失望了,这些年,她说过太多谎,不仅仅骗得过别人,连自己也被骗。
“胡阿姨好吗?很久没跟她联络,我
<img src="http://3gimg.qq.com/book/images/newyearAct/newyearActLogo.jpg" alt=""/>
【求生卡】答对以下题目,您即获得抽取船票的机会:
在个人中心里可以对好友做什么?想她很忙。”她自顾自说开,习惯他的不理会。
“嫂嫂长得很漂亮,你们是很合适的一对,你们结婚是乐坛大事呢!将来你的宝宝——”
宝宝——曾经,她也有一个宝宝,要不是她的缘故,也上小学了呢!她会拼命赚钱,让他学小提琴,说不定有机会,父子成师生,说不定同台表演,说不定——好多的“说不定”,都是因为她的疏忽而没有——
“不会再好了吗?”
“什么?我没听懂。”突然一句,问得于优满头雾水。
“你的腿。”
他在关心她?不!他的表情没有关心、他的声音没有关心、他的心没关心过她,她逼打消他正关心她的念头。
“能不能走,我不在乎,我过得非常非常好!”清清柔柔两句话阻止他的探索。
推开轮椅,她往外走。她很好,非常好,有没有腿她都好、活不活得下去她还是很好,在他身上她不要同情怜悯,她只要爱,既然给不起她爱情,就别再制造关心假象,害她认不清楚事实。
“小优。”他阻下她的轮椅,立在她面前。
一声呼唤,使她泪湿栏杆。
“哥——我们不要再见面了好吗?我好不容易适应没有你的生活,好不容易忘记我们的过去,好不容易让自己过得好,不要你一出现,我的努力全成泡影。”
“你恨我。”
“不!是你恨我。不管你怎样克制,眼底仍会流泄出对我和妈妈的恨意,不管时光过去多久,我们都是夺去胡阿姨幸福、破坏你美满家庭的坏女人。我欠你的,眼前是还不起了,如果你有耐心等待,就等我有能力时再还债好吗?”
“我没向你索债。”隐隐地,他知道她不同了,从前惟惟诺诺的小优也敢在他面前对他长篇大论。毕竟,九年了!他躲避她、躲避自己的心,整整九年——
“那么就放开心胸,不要再恨,感情是无从解释的。放过我们,你才能放过自己。”侧过脸,擦去泪,她又问:“不再见面,好吗?”
她已经不要他了,在他躲开九年后,她也要躲他?也好!这样他们就扯平了。
“好!不见面。”他跨开长脚往屋里走。
这句话,让他们在未来一年中,没有瓜葛,直到储睿哲和于淑娟死亡——
三十天的幸福,一下子就被他们耗尽,才一眨眼,时间就从洪流中跳出来告诉她——GAME OVER!结束了,他们之间要在这里真正划下句点。
不过,庆幸的是,这次,他们谈开说开,两人再无恨无怨无遗憾。
然而,遗憾——真的没有了吗?
英丰推着于优去机场。
“一到美国,记得打电话回来,还有,记得跟妈咪联络。”
英丰的叮咛反复十几遍,但于优不觉得烦琐,她在他话中,温习起被担心、关怀的宠爱。
担心?是的,他把她放在心上了,她知道这一离去再无相见日,但是想到自己就在他心上——她的心像淋上了蜜般。
握住他的手,请容许她再撒娇一回,“哥,抱抱我好不好?”高高伸出两手,她笑得好畅意。
“好。”俯下身,他将她抱起、紧紧圈住,无视于来来往往人潮的眼光,他要将她锁在自己心里。
嗅着她的发香,汲取她身上暖暖的体温,他多希望她成为他生命中的全部,“小优。”
“嗯——”陶醉在他怀中,她知道在他心底一角,他爱她!这个认知对于一个将亡女子,是恩惠。
“再问一次,我们能从头来过吗?”不想死心,尽管背负着道德良知谴责。
“我们还能不能回到童年时?我八岁、你十二岁;你教我拉琴,我帮你背书包;你拉我的辫子,我骑在你背上——能不能?能不能再回去?”她再追问。
“不能。”对光阴,谁都束手无策。
“对了,有很多事,过去就再回不来,就算重头,也不会有相同的感觉。我们只好学会珍惜眼前,过去的,只能凭吊。哥,我们来打勾勾好吗?”
“要约定什么?”
“这一轮,我当你的乖妹妹,你当我的好哥哥;下一次,再碰上,我就当你的妻子,你当我的丈夫。到时,我们中间不准有嫌隙,只有包容和爱。”
“好!那我也要跟你说定,不要恋栈国外,不要让高鼻子帅哥迷昏头,工作一忙完就回来,回到好哥哥身边,让我宠你、保护你。”
“到时,你身边会有个嫂嫂吗?”
“你要一个嫂嫂吗?”
“我要!我要你幸福平安,我要有人专心对你,我要有人爱你、疼你,像你爱我、疼我一样。”
“好!你一回来,就会有个嫂嫂在家等你。”
“说定了!”一击掌,她握住他的幸福和安心。
“小优,有个问题问你。”
“请问。”偎在他身上,有些不舍得——不舍得放手——逼她放手的不是心,是命啊!
“在国外那几年,我回国数次,为什么你总是不在家?”
“我自惭形秽躲起来了,本想把脚练好,等你回来,娉娉婷婷站在你面前,哪里知道,天不从人愿。你呢?我也要问你,为什么那些年,你都不向人问起我?”
“我以为,你恨我。”他实说,毕竟,他的行为太可恨。
“你看,我们都让自己的盔甲,挡住了自己的视野和对方的真情。”
“下次再见,让我们把盔甲都丢弃了吧!”
“好!一言为定。”他们勾勾小指头。
一声呼唤打断他们的谈话,回头,一个二十来岁的小男生站在他们身旁,“于姐,我来了。”
“他是我们公司的工作人员,我要过去和他们集合了,哥,你回去吧!再见。”于优对他挥手。
“我送你过去。”他说。
“不!你先走,我要看你的背影。”她拉拉他的衣服软声哀求:“这次你将就我,下次,我再迁就你好不好?”
叹口气,站起身,挥挥手,转过身后他可以感觉到她灼热追随着的目光。
半晌,大男孩问:“于姐,我们要去哪里?”
“阿杰,麻烦你送我回公寓。”闭起眼睛,于优叹息。永别了——亲爱的“哥哥”。
当夜,公寓里四个女子喝了一肚子伤心酒,隔天剪去长发,远走垦丁。
总以为,这趟旅程结束后,要断该断的都能断得干净,谁知情事纠葛,心仍放不下、情仍断不净。
关上公寓大门,结束五年的同居生涯,挥别她们的单恋公寓,互道一声珍重再见。
故事开始、故事终场——她们在彼此脸上看到情伤——
“小语,在国外安定下后,打电话给我们,不可以断了联系。”童昕叮咛。
“我知道,等我找好住处就打电话给你们。”独自远走他乡,小语需要她们很多的支持和鼓励。
“我和辛穗会先找个地方住在一起,要是联络不上,你有我和辛穗老家的电话。”童昕再叮咛,对这个年纪最小的天真小语,她有太多的不放心。
“如果在国外住不惯,就回来找我们,到时我们再租一个多情女子公寓。”辛穗一路说一路笑,眼泪在眼角处偷渡。
“不要再说,你一说我都不想走了,还没出发,我就幻想起我们的小宝贝,他一定很可爱、很漂亮,我要当他干妈。”
小语指的小宝贝,是躲在童昕肚子里的小小生命,还没出生,他就负担了四个女人的期望。
“不想走就别走了,我不也说要当修女,还不是改变主意。留下来吧!”
辛穗娇声恳求,小语脸上有着为难。
“辛穗,别勉强她吧!让她出去飞上一圈,要是她觉得窝穴比外面的天空诱人,她会回来的。”一直静默的于优出声替小语说话。
“没错,单飞得不顺利,我会回来。”小语指天指地,发誓。
“好吧!于优你呢?你一直不告诉我们以后要做什么,你有新计划吗?”
“我——计划?”她的计划——操在老天爷手里吧!
“要是一切顺利,我会和你们联络。”叹口气,她将钥匙放入填好住址的牛皮纸袋,递给辛穗,“麻烦你帮我寄出去。”
“好!我们一起下楼!”推着于优进入电梯,四个多年相处的女子,紧紧交握双手——别了。
坐入出租车内,于优轻轻一声:“麻烦,华大医院。”这次入院,怕是出不来了——
*本文版权所有,未经“花季文化”授权,谢绝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