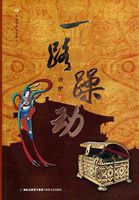朱利安·劳埃德·戴维斯随后播放了特里审讯加里的录音片段。他向法官请求当庭播放录音的理由是,劳埃德·戴维斯相信一个人说话的语调和内容同等重要。但萨拉猜想他这样做的真正原因是,即使萨拉不让加里出庭作证,陪审团仍能听到他粗俗野蛮的讲话方式。萨拉虽然提出了抗议,但并未极力反对。当朱利安·劳埃德·戴维斯获得法官的允许后,还朝他的助手自鸣得意地一笑;但萨拉内心一阵窃喜,因为朱利安·劳埃德·戴维斯偷鸡不成蚀把米,犯下了迄今为止最大的失误。
从录音中可以听出,加里表现粗暴、好斗,不愿配合警方的工作。他说自己离开驿站酒店之后,跟朋友肖恩一起去了另一个酒吧。他们在那里碰上了两名妓女,靠着酒吧的墙和她们发生了性关系,每人还给了10英镑,不过他都想不起妓女们的名字。年纪稍大些的陪审员听了以后面露惊骇反感的神色,这反应正是劳埃德·戴维斯所期望的。
录音中,特里坚持说加里去过雪伦的房子,闯入之后当着她孩子的面强奸了雪伦,但加里予以否认。“她如果这么说,就是个撒谎的臭婊子。”
“但她的确是这么说的,加里。她认出了疑犯,就是你。”
“哼,那她就是在撒谎,她怎么可能认出是我,臭娘们!”
“她为什么不可能认出是你,加里?”
“因为我他妈的压根没去她家,这就是原因!”这声抗议之后是一段漫长的沉默,许久之后加里紧张兮兮的声音才打破了这阵沉默。“你听到我说什么了吗,条子?她不可能认出我,因为我压根没去她家。”然后又是一阵沉默。“你能证明我去了吗?接着说啊,我倒要听听你凭什么冤枉我。”
紧接着,萨拉听到了那句曾引起她注意的话。
“我们之所以知道是你干的,就是因为雪伦·吉尔伯特认出你了,加里,她看到你的脸了!”
萨拉仔细观察着陪审团的痛苦表情,接下来的沉默持续时间更长。录音中加里说话的口气产生的效果正符合劳埃德·戴维斯的期待:声音极大,透着蛮横和嘲弄。“蠢到家的臭婊子,全是扯淡,她胡扯!她还认出老子的屁股呢!”
当法庭书记员关掉录音的时候,劳埃德·戴维斯转向证人席上的特里·贝特森。“现在,警官先生,关于那段审问录音,我要问你几个问题。”
“好的。”特里瞄了一眼萨拉,她正襟危坐,全神贯注地看着特里。萨拉的眼神中没有一丝调情甚或友善的意思,那眼神冰冷得就好像是蜥蜴在对苍蝇虎视眈眈一样。
“你去找过这个肖恩吗?他姓墨菲、马利根、或者是莫里亚蒂什么的?”劳埃德·戴维斯惯用讽刺挖苦的伎俩,而现在他又在故技重施了。“就是哈克先生声称在事发当夜跟他在一起的那个人?”
“是的,先生,我们找过了,但并未找到。”
“没找到,那你们找到他声称遇到过的两名妓女了吗?”
“也没有,先生,我们没有她们的姓名或住址,更没有具体的描述……”
“那你是怎么看待加里·哈克所谓的不在场证明呢?”
“我认为那全是谎话,先生。”
“谢谢。你在问讯中反复告诉被告,他被吉尔伯特女士认出来了,他对此作何反应?”
“嗯,你从录音当中也能听出来,先生。他当时非常吃惊和气恼。但当我告诉他受害者被强奸,甚至是当着她孩子的面被强奸的时候,加里·哈克并未显出一丝不快,似乎不是很担忧。真正惹恼他的是受害者声称认出了他。我说这句话的时候,他脸色煞白,一时语塞。”
劳埃德·戴维斯在特里说完之后沉默了一会儿,佯装沉思,而真正目的是让特里最后一句话深深烙印在陪审团的脑海中。他继续沉默,直到格雷法官挑起眉毛,以示询问,劳埃德·戴维斯才不情愿地坐下。
“谢谢你,督察,请留在原位。”
萨拉站起身,她看向法庭对面的特里·贝特森。他们对峙着,没有闪现出一丝相互认识的眼神。一小时前轻松愉快的畅谈已经被抛到九霄云外,他们现在就像两个萍水相逢的陌生人。当萨拉开口发问的时候,特里背后的汗毛都竖了起来。
“贝特森督察,你欺骗了哈克先生,不是吗?”
特里沉默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让我帮你回忆一下好了,你还记得这些话吗?‘我们之所以知道是你干的,就是因为她认出你了,加里。她看到你的脸了!’这是你说的,对吗?”
“是我说的。”
“这是真话吗?”
“吉尔伯特女士认出了加里·哈克,没错。这就是我们逮捕他的原因。”
“但她的确看到他的脸了吗?”
“没有。”
“所以你骗了哈克先生,对不对?”
特里稍稍恢复了镇定,然后按照警察训练要求的那样,面向法官回答问题。这是侮辱辩护律师的微妙技巧,让萨拉在陪审团眼中显得无足轻重。
“她确实没说自己看到了他的脸,法官大人,这倒是事实,但她非常清楚地表明,她认出性侵犯自己的人就是加里·哈克,而且我这样做的原因……”
“我并没有问你为什么骗人,督察先生,我问的是你究竟有没有说谎。而你的回答是肯定的,对吗?”
法官向前探了探身子,“不管怎样,我认为让督察先生解释一下原因,也许会有助于陪审团的判断。督察先生,请继续。”
感谢上帝还有法官在,特里暗想。“原因很简单,法官大人。我想知道如果加里以为自己被受害者认出了会作何反应,而他的反应相当明了,正如您在录音中听到的一样,他陷入了沉默,而且当时他脸色惨白,这一切都证明他的确有罪。”
萨拉瞄了一眼法官。看样子他回答完了,至少目前已经无话可说。她再一次感受到那种触电般的万众瞩目的感觉,但在这一刻,多数都是仇视的眼光。
“我明白了。督察先生,如果我告诉法庭的各位,今天午餐的时候你将手伸进我的短裙里,并且非礼了我,你会怎么辩解呢?”
整个法庭上的人都倒吸一口凉气。旁听席上甚至有人开始忍不住傻笑起来。特里张开嘴,想要辩解,但一个词都说不出来。
在他恢复理智之前,萨拉平静地继续说道:“我想陪审团十分清楚地看到你描述的情景了。你脸色灰白,无言以对。好吧,请众位陪审员放心,这只是一个假设,督察先生从未非礼过我,众位陪审团成员,即使清楚这一假设并不成立,他仍然震惊得无法言语,你们已经看到了。”
陪审团里的一年轻女性忍不住笑了起来,而邻座的那位也咧嘴笑了。其他成员的表情从欣慰、失意到反感,各不相同,至少,萨拉吸引住了全体陪审团的注意力。
但这不是萨拉原定的进攻路线——接下来怎么办?阐述完一个观点后,就该乘胜追击。萨拉以一种沉静而充满说服力的语气问道:
“督察先生,你在加里·哈克的公寓里有没有找到蒙面头套?”
“没有,法官大人,我们没有找到。”特里的语气僵硬冷漠,但内心强压怒火。这女人也太贱了吧!在酒吧的时候,她是否就盘算这一招了?她的问题排山倒海地压过来,势如破竹,尖刻无情。
“你们有没有找到雪伦·吉尔伯特所说的那块手表?”
“没有,法官大人。”
“既无蒙面头套,又无手表。你们确实搜查过加里·哈克的公寓,是吗?”
“是,我们搜查过了。”
“你们既没有找到蒙面头套,也没有找到手表。那请问你们有没有在那间公寓里面找到任何足以指正加里·哈克强奸了雪伦·吉尔伯特的罪证呢?”
“没有,法官大人。但是……”
“所以,你们当天凌晨5点逮捕哈克先生的唯一理由,就是基于雪伦·吉尔伯特的指认,而她并没有看到过罪犯的脸。以上陈述是否正确?”
“这……就是当时逮捕他的主要理由,没错。”
“还有其他理由吗?”
“没有。”
“这么说,那并不是你逮捕哈克先生的主要理由,而是唯一理由,不是吗?告诉我,督察先生,你当晚为吉尔伯特女士做笔录的时候,她意识清醒吗?”
“我……我知道她喝过酒,法官大人,但她看起来没怎么醉,她清楚自己在说什么。”
“你说她没怎么醉。吉尔伯特女士已经告诉本庭,她当晚在派对上喝了6杯伏特加,外加一杯双倍杜松子酒,更不要说在你抵达现场之前她还喝了一杯伏特加镇定情绪。为什么这在你看来,雪伦·吉尔伯特还没怎么醉?督察先生,女性饮用酒精在多少份限度之内才可以安全驾驶?”
特里迟疑了。“呃……我觉得,一两份吧。如果是与食物同服的话,也许是3份。”
“你觉得?你是一名督察,这你都不确定吗?”
“实际情况根据环境与个人体质的不同而变化,更何况我不是交警。”
“那么让我来告诉你好了。如果一名普通女性在3个小时之内饮用超过3份酒,就不适宜驾驶了。雪伦·吉尔伯特至少喝了8份。她饮酒的分量几乎是安全驾驶上限的3倍了,而你仍然说她没怎么醉。”
“我并没有说她适宜驾驶,而是说她能够认出是哪个男人强奸了她。”
“即使强奸犯当时戴着蒙面头套?”
“是的。因为罪犯是受害者熟识的人。”
“好吧,督察先生,在我看来,你想要陪审团相信两件不可能的事。你要么是认为一个喝了6杯伏特加以及一杯双倍杜松子酒的女人仍然完全清醒,要么清楚她已经喝得烂醉如泥,仍能准确无误地认清一个戴着蒙面头套的男人。你究竟坚持哪个观点呢?”
陪审席传来一声闷笑,听起来既像是为萨拉喝彩,又像是对特里的嘲讽,特里叹了口气。
“两者都不是。正如我说的,她并不是完全清醒,但她的意识清醒到足以认出强奸自己的罪犯。而且第二天,在完全酒醒之后,她仍然坚持当时的指控。对此指认她自始至终都坚定不移。”
“我明白了。然而,督察先生,哈克先生是不是也同样在被捕当天就否认强奸指控,而且每逢问讯时都坚定清楚地否认这些指控呢?”
“是的,法官大人。”
“很好,你们在他的房子里或衣服上没有找到任何实质性证据来支持这一指控,我的表述是客观准确的,是吧?”
“是的,法官大人。”
“很好,法官大人,我问完了。”
萨拉提了提法袍,坐下身去。她脸上挂着一丝神秘莫测的微笑,目送特里向法庭后方走去。那微笑意味着什么呢?特里边走边暗自揣摩,讽刺?嘲弄?自满?
贱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