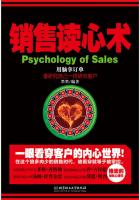大殷国位于中州的腹地,他的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分别被人称之为东荒,南岭,西漠,北原,其地貌和字面上的意思差不多。东方为一片荒地,南面是丘陵,西面多为沙漠,北面多为草原,而中州则多为高耸的大山。东南西北中,每一块都是无垠的土地。
无论世间有多少个种族,他们随着种族繁衍而传承的神话中却有一点是出奇的一致,世间的万物都是由同一个神创造,那个神被称之为天之树。天之树扎根于苍穹,向着大地生长。天之树有漫天的枝桠,它们一直长,最后长到到了地上,化作中州十万大山。因此中州是天下福地,所有人都相信这一句话,得中州者得天下。很多时候东南西北四方被统一以后,中州的战火依然熊熊燃烧,难以熄灭。传说毕竟是传说,没有多少可信度。但是有一点却是不变的,历来中州的主宰亦是天下的霸主。要成为中州主宰,必须得同时面对东南西北四个方向的威胁,可是中州的霸主亦无力再征战四个方向,数千年以来,中州被上百个国家坐拥,却没有一个可以实现那个神话。有的国家在刚刚建立就被东南西北四个方向的主宰联手毁灭,或被另一个崛起的国家摧毁。
而大殷的存在则是一个传奇,还有三个月,他就一百岁了,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中州的国家,包括那些小国。他每活一天,这个记录就被刷新一次。一百年前,天下还是战火连天,每天都有无数的人死去,又有无数的人出生。大殷的开国皇帝大日氏欲念天带领大日氏一族强势崛起,横扫中州,在东南西北刚刚被统一的紧要关头,统一了中州,成就无上霸业。现在,他看起来像是才步入壮年,强大到了极致,完全统一了中州的十万大山。这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每一年,他都要举行国庆,每一个节日都在都是无比顺利的度过,向国都朝歌运送的贡品没有丢失过一件。大殷的每一个为国而死的将士都会得到连他的孙子都会笑着进棺材的高额抚恤金。每一场败仗哪怕是一个一百人都不到小队全军覆灭,都会被视作耻辱载入史册。
皇帝爱戴他的子民,臣民拥护皇帝,他的手每时每刻都在向外面伸,这是一个国家强大的必然。
花枝镇位于大殷的南疆,晚上居民可以听到来自南方的兽吼。严格来说,这里属于南岭,三十年前,它还是属于一个叫尾的国家,而尾每一年还要向南岭的主宰上氏一族进贡。在花枝镇唯一一条通向城池的官道上,一支十一人的小队坐在马背上奔驰,往花枝的方向而去。
蹄音在山谷回荡,激起一山鸟雀。他们都穿着奇怪的甲胄,那甲胄是用百年的巨鳄的背部的皮做成的,那个时候的鳄鱼正值壮年,而它背部的皮则是最坚硬的,经过大殷最好的工匠的打磨,变得柔软而不失韧性。甲胄紧紧勒出胸腹肌和背部肌肉间的沟壑,黝黑的手臂裸露在春风中,手臂上的血管粗壮如虬龙,那里面流动的是惊人的力量。他们并不是那种铁塔大汉,但是你丝毫不会怀疑他们可以轻而易举地掀翻一头壮牛。一身的尘土也掩盖不了他们的可怕的气息。
他们的脸上戴着京剧脸谱,如果他们正在戏台上翩翩起舞,当然不会有什么好奇怪的,可是他们骑在马上。奔驰在最前方的禁卫军的肩头纹着大殷国的图腾,大殷国的神——暗神龙。龙展开铮铮铁翼,以撕毁一切的姿态扑向苍穹。在诸神之中,暗神龙是最叛逆的,但同时也象征着大殷的强大。这种绝美的腾纹并不是什么人才能拥有,守护朝歌的禁卫军可以,但也只是少数。他们的背后绑着黑色的长刀,闪烁着的寒光比寒风更加渗人。
这几个禁卫军身下的战马比普通的马要大上两个马头,纯黑种,他们在朝歌被称之为踏瀑流,意为踏着坠落的瀑布奔驰。民众眼中的千里马也只能一日奔走八百里,但是踏瀑流却可以以千里马最快的速度不停歇地跑三日三夜。每一匹踏瀑流都是大殷的财产,他们的身上都打上了独一无二的标志,那个标志从它的祖先为大殷服役的第一天开始就以一种特殊的方式传承着。军部每个月发给它们的钱是禁卫军一名普通士兵的两倍。贵族在黑市交易时要用于踏瀑流十倍体积的黄金来换取,但是这样的交易一旦被抓住了就是死罪。它们的身上完整的覆盖了和他们主人身上穿的一样材质的护甲。
就是这样的一群人,到底什么地方会用到他们?
军队中会用到一些。一般是十个人中会有一个,但是除了他自己谁都不知道哪个才是禁卫军,普通士兵的甲衣遮住了那耀眼的腾纹。战场上,总会有一些人,像箭一般冲向敌方的首领。如果一场战斗即将失败,他们会投出刀隔着百丈的距离结束一名敌方指挥官的生命,一脚踏爆一具尸体,然后蛮横地撕开身上的甲衣。这个时候,那个腾纹成了战场上最耀眼的存在,不需要有人吹起冲锋的号角,士兵们会在神的感召下,不要命地反击。大殷国建国百年,几乎没有败仗。他们出现的时候,是钦差大臣般的姿态。
现在他们出现在了大殷边疆的一个小镇。
鹿久突然调转马头,驰上官道一侧的山峰,他的部下紧随其后,没有人问他为什么会如此奇怪的举措,禁卫军的训练交给他们的只有四个字,绝对服从,即使那是无法完成的任务,也要挥出手上的刀。
从山下到山顶长着许多两人高的矮树,枝桠横生交错,以踏瀑流的体形无法穿过,但是它依然向前飞跃,挡在它前面的枝桠被一股神秘的力量绞断飘向两边。鹿久勒马停在山顶,踏瀑流的右前蹄重复着擦地的动作,鼻孔里发出像驱赶苍蝇一样的响声。他们和主人的心是想通的。鹿久静静地望着花枝,面具下不知是什么表情。
他的背后背着一个小背包和一根被黑布包裹着的半丈长的轴,他的手绕到背后在背包里取出一个碧绿的玉镯,镯子用的玉并不纯净,里面有许多杂质,像被固定在里面的小虫。这种玉放在玉器店里也是被扔在一边的废料,以大殷每个月发给禁卫军的银钱可以随随便便的买一大堆。他凝视着玉镯,片刻,他收起玉镯,提起缰绳,踏瀑流向后退一小段距离,鹿久猛夹马腹,踏瀑流前冲,跃起。前面是山崖,落差有十丈。
“葫芦,以后不要跟着陈佳彤。”米小花小声说。
“啊。”葫芦愣住了。
“那样只会让自己遍体鳞伤,难道你就一点都不爱惜自己的身体?”米小花说,“你可以用这些时间帮你嫂嫂干些活,也可以去捕鱼,去酒屋当一个侍者,你可以用那些时间做许多事。无论做什么,都好过在这里受欺负。”
“陈佳彤,可以把那块玉送给我吗?”毛妙妙昂着头一手叉着腰一手伸到陈佳彤的面前,“我很喜欢那块玉。”毛妙妙长得比葫芦还高,还比葫芦瘦,长得很漂亮,是葫芦在花枝镇除了米小花外最喜欢的女孩儿,葫芦最喜欢看她走路的时候那一头顺滑的长头发在空中飘扬,但是葫芦不喜欢她的自以为是。
“那可不行。”陈佳彤抓着毛妙妙的一小束长头发,头发又从他手中滑走,他微笑着说,“下次吧,下次有就给你。”
“你要给米小花?”毛妙妙看着米小花的背影。
“不能说。”
“哼。”陈佳彤想再抚摸她的头发,她扭开头,在陈佳彤的旁边坐下。陈佳彤盯着葫芦和米小花,笑容消失了。
她在关心我,葫芦在心里狂喊,他感到自己的心跳正在加速,血液向着脸部涌去。他低着头笑,那不是假装的笑,“不啊,大家都对我挺好的,我可以把他们不要的衣服带回去。”他的声音越来越小,笑容也渐渐消失,因为米小花走回休息区去了。“那可是丝绸,蛮值钱的。”他用只有自己才能听的声音说。
“你很关心他?”陈佳彤面无表情地说。
“我只是觉得你们做得有些过分。”米小花瞪着陈佳彤,坐在一旁,离陈佳彤有些远。
陈佳彤哼一声坐在地上,仆人过来给他揉肩,他的眉头却越皱越深。
葫芦坐在休息场的角落里,拿着那条丝巾傻笑,洁白的丝巾上有一半沾了血,血干了之后呈现出一种暗红色,丝巾看起来有点恐怖,回家一定要好好洗一洗,他想。公孙长文走到他的旁边,打断了他的幻想。
“那么大的一个球,你看不到?”公孙长文的眼睛里似乎要喷出火来,“跟你说个实话,那块玉我本来就打算给陈佳彤那个家伙的,他第一眼看到就找我要,所以我们约定用一场蹴鞠比赛来决定那块玉是否该给他。可是这么容易就被他拿走了,很让我窝火,尤其是他嚣张的样子,真的让我很不爽。你最好能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否则我就跟陈佳彤那家伙说你拿着米小花的东西意淫。”公孙长文冷笑,他知道葫芦是不会把这些话说给陈佳彤听的,“后果你是知道的,说不定我会连你的那个没有人要的嫂嫂一起赶出花枝镇,这是对你最轻的惩罚,相信我。”
“我在看,我在看..”葫芦哆嗦着嘴唇,恐惧占据了他的内心,公孙长文绝不只是吓吓他而已,如果他真的说不出什么让他满意的答案,那..他的嘴巴有些发干,不敢看公孙长文,“我在看,我在看,那儿好像有个什么东西,不过我没有看清。”葫芦指着北方。
“那儿,那儿只有一间马厩。”公孙长文哼道,双手互握,发出劈啪声,“你对马厩很感兴趣?还是马?”
“不是,我没有看清楚。”葫芦用祈求的声音说,“兴许是我看走眼了,眼睛有点不舒服。”
“那就过去找找,希望能让你不盯住球的那玩意儿还在那里。”公孙长文忽的提高音量,有不少人看过来。
“哦。”葫芦向着北面走去。
“葫芦,你在干什么?”米小花喊道。
“没什么,公孙少爷让我过去看看。”葫芦僵硬的笑笑。
这座玩儿蹴鞠的场院只是陈佳彤家后院的一部分,里面有好几间马厩,里面养着马,陈佳彤有的时候会在这里骑马射箭。葫芦来到北面的一座马厩,里面有一匹枣红色的马正在吃草,它看见葫芦过来很不客气的哼着。葫芦小心翼翼地接近着,一面观察是否有什么可以用来作为答案的东西。结果很令人失望,里面只有一坨马夫还没来得及清理的马粪。
如果我跟他说我是被一坨马粪吸引住了,兴许马厩上面还有什么东西。他爬上马厩,看着远方,他希望可以看见一只长着三个脑袋的鸟,或者是一头牛在天上飞,怎么可能。他看见了远方山崖上几个黑点跃下,十年前的记忆浮现出来。那是.“是禁卫军。”他大声喊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