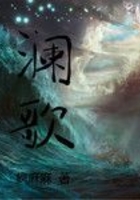公元三百五十四年秋,在武关城外打了一场恶仗。
夕阳的余晖中,绿色衣甲的步兵骑兵集结在南面高地上,军旗上的“晋”字清晰可见。北面山坡上白蒙蒙一片,白色衣甲兵团肃立排列在“秦”字军旗下严阵以待,愤怒的望着南面高地上的晋军,随时准备冲杀。南面山地上的晋军结成步骑两阵,愤怒的眼光充满杀气,已做好了冲锋准备。血红的残阳在渐渐消退,战场一片寂静,只能听见军旗飘扬的瑟瑟之声。
“嘟,嘟…”号角响起,秦军令旗一挥北面山地的骑兵军团发起了冲锋,晋军令旗一挥步军方阵闪出五千名弓弩手万箭齐发射向秦军,冲锋在前的秦军骑兵纷纷中箭倒地,但秦军骑兵没有胆怯依然挥着弯刀继续冲锋,整肃的晋军骑兵在主将的带领下也催动战马发起冲锋迎战秦军。双方厮杀一片,战马嘶鸣声兵器相拼声响彻天地。幕夜,双方收拢人马各自回营,只在战场上留下累累尸体和几匹孤马。
这场战争,没有胜负,两败俱伤。
白色军团由秦太子苻苌率领,半日激战中斩首晋军两万,淮南王苻生率领三百精骑直突敌阵,一举擒获晋军骑兵主将戴施!如果战争到此结束,秦军可算大获全胜。出人意料的是,晋军骑兵在主将被俘后并没有溃退,反而拼命死战,企图夺回主将。苻苌见弟弟被围,情急之下,挥动长剑,亲率五千精骑冲入敌阵。两军会合,秦军士气大振。
晋军主帅桓温面色严峻,厉声命令:“上霸弓,给我射死敌军主将!”
“是!”传令军士挥旗下令。步兵方阵闪出一辆兵车,车上载着一方巨弓,车上的十名军士拉动弓弦,瞄准正在砍杀的苻生。“嗖”,一支冷箭飞出,眼见就要射到苻生,苻苌看到飞箭来袭纵马挡在苻生身后,箭中胸前,苻苌痛彻心扉,低吟一声,跌落马下。
“大哥!”苻生急忙下马抱住苻苌。
苻苌面色苍白,低声道:“王弟,收兵…据关而守…”说完便昏了过去。
苻生将苻苌抱上战马,率军左突右冲终于杀出重围,秦国大军收兵回关。苻苌胸前的箭头竞深五寸,伤口周围红肿渗血,军医急得大汗淋漓,却不知如何下手?
“能拔除吗?”
“铁簇深入胸肺,如果冒然拔之,成败不可知啊,哎…”军医摇头叹息。
“这可如何是好?”苻生急的在帐中踱步。就在此时苻苌醒了过来,慢慢睁开双眼,喘着粗气低声道:“王弟…我不行了,这是调兵虎符你收好,城防之事就拜托你了。”
“大哥放心,有我在武关固若金汤!”苻生跪拜在地接过虎符,潸然泪下。
“可惜不能再驰骋疆场了!”苻苌一声高吼后便咽了气。
帐内响起一片哭声,这时斥候进账禀报军情,苻生呵停哭声询问道:“有何军情?”
斥候禀报:“晋军水军已进汉水攻占了南郡,晋军大将司马勋率军经子午小道偷袭了上洛,我大军屯在上洛的粮草尽数被毁。”
“什么,岂有此理?”苻生气的拔剑要杀斥候,被众将劝阻。
“殿下,为今之计我们只有退守蓝田求援长安。”前军主将雷弱儿献策,雷弱儿少年从军,,为人刚正耿直有勇有谋,跟随先帝苻洪南征北战平定关中官拜二品辅国将军,后年迈归隐赋闲在家,此次晋军犯境,符健亲自登门邀请出山,辅佐太子苻苌率大军抗敌。
苻生冷笑一声:“撤退?亏你能想得出来。”
雷弱儿继续劝谏:“殿下切不可意气用事,我大军粮草尽数被毁,军中无粮,其心必散,况且晋军水军已经占了南郡如若包抄我军后路,待到那时,我大军困守孤城四面受敌,又无粮草接济,将不战自溃已!”
苻生思忖良久,后拱手谢罪:“老将军所虑甚是,请恕我唐突!”
雷弱儿急忙还礼:“殿下言重了,我大军可乘今夜月色撤离,此外太子架薨不可发丧,以免动摇军心。”
“一一照准,就有劳老将军处理退兵事宜!”雷弱儿领命后走出帐外。
乌云遮月,秋风萧瑟。远处山地上篝火明亮,守卫的士兵聚在火旁烤手驱寒。双方白日一番厮杀各损元气,今夜头等大事就是养精蓄锐,明日决战,才是真正的你死我活,晋军除部分巡逻将士,其余人等皆进入梦乡呼呼酣睡。秦军趁着月色悄然离关,晋军却没有丝毫察觉。
旭日东升,秋霜晶莹。晋军埋锅造饭饱餐一顿后,大军倾巢而出,准备和秦军决一死战。大军行至武关城下,见城墙上旌旗招展城门大开,却无人防守,晋军将士都愣住了。
桓温命令大军扎住阵脚,派百骑冲入城中,试探敌情。桓温乃是东汉名儒桓荣之后,少有才名,在平定苏峻之乱时立有战功升迁荆州刺史,桓温为人豪爽,姿貌伟岸,风度不凡,
后娶南康公主为妻,至此仕途扶摇直上成为权臣,此次被任命征讨大都督,率领水陆大军十五万北伐中原。
不久斥候回报:“禀告大都督,城中并无秦军,具百姓所言昨日夜里秦军已经弃城而逃。”
“什么?”桓温略显惊讶,片刻又哈哈大笑。
“将军为何发笑?”部下不解发问。
桓温捋了捋胡须淡然说道:“秦军悄然弃关必是后援粮草不济,看来一定是司马勋得手了,烧了秦军粮草!”话音刚落,司马勋就遣使来报偷袭上洛烧秦军粮草之事。
“将军神算,我等望尘莫及。”众将纷纷称赞。
桓温高声命令:“传我军令大军进关休整,三日后兵发蓝田!”
“敌人望风而逃,将军何不引兵去追啊!”参军周楚(字元孙)提出异议。
桓温微笑道:“元孙不必多虑,常言道穷寇莫追,秦军退撤有序,我料其必设伏兵于追路,如若引兵去追必中埋伏,损兵折将得不尝失;不如休整几日徐图缓进步步为营,此乃上策!”
“将军高谋!”桓温哈哈大笑,率大军入城。
秦军主力赶了一夜路程,黎明时,大军已经退到青泥城,求援特使飞马驰向长安,大军短暂休整后,又向蓝田撤去。晌午埋伏在清沙涧的两万精骑在前军主将雷弱儿的率领下缓缓退出山涧,向蓝田奔去。
秦军进入蓝田山谷,哀声震地,军中扬起白旗,埋葬太子苻苌于孤缈山,在墓前杀晋将戴施祭祀太子。
渭水南岸的大道上,一个白衣骑士向北飞驰,渐渐进入山坳。
正是夕阳西下时,荒凉的群山峻岭显得冷酷肃立,让人不寒而栗,骑士拿起水袋狂饮一阵,催动战马继续向北奔驰。这片绵延山脉就是闻名天下的桃林高地。据《山海经》记载夸父逐日渴死途中,手杖化为桃林躯干成为山脉,便就是这桃林高地了。这片高地东起崤山,西至汉水渡口,莽莽苍苍数百里,高地沟壑纵横,峻阪迂回,一条大道在山脉之中曲折蜿蜒,向西三十里就是南面通往关中的唯一路径-潼关!
潼关北临黄河,南踞山腰,雄踞秦、晋、豫三地要冲。几十年后,魏郦道元的《水经注》这样记载潼关:“谷深崖绝,山高路狭,涧道之峡,车不方轨,细路险与猿猴争,人间路止潼关险。”后李渊据守潼关占据关中以成盛唐基业,可见潼关之险!
白衣骑士风驰电掣般飞到关下时,潼关城门正在隆隆关闭。那匹神骏的红色坐骑竟是通灵之极,长嘶一声,从行将合拢的城门中腾越而过,引起城头兵士的一片高声喝彩。
“闯关者何人?”守城将军高声喊问。
“求援特使!”骑士留下一声长长回答,还没等守城将士回过神了,却早已在一里之外。
潼关是秦国咽喉要道,往常过往行人都要严格盘查,但秦晋开战以后出入关口的斥候不断,守关将士时常因为盘查过细,而遭恶言侮辱。久而久之见到这些斥候老爷们守关将士都是简单询问,打发他们赶紧上路。守城将军见入关者秦军装束,又报号求援特使,也就没有派出飞骑追赶细问,反而在城头高声议论赞叹这个特使的那匹良驹和高超骑术。
在夕阳落下的余晖中,骑士骏马像一朵彩云,向西掠过空旷的原野和滔滔的河流。骑士向坐骑猛抽一鞭!神骏的红色战马突然发出一声长长的嘶鸣,四蹄腾空加速奔驰,箭一般向西而去。
渐行渐西,遥遥可见苍黄的原野上矗立着一座黑色孤城。随着白衣骑士的骏马飞驰,渐渐可见背向夕阳的东门城楼上有白衣甲士游动,猎猎飞动的黑色军旗上大书一个白色的“秦”字。
这就是秦国的都城长安,它坐落在渭水河畔。长安是秦的第二座都城,西晋末年群雄豪杰并起,氐族首领苻洪率部众进入中原,一路聚集流民在枋头建都,自号“氐王。”苻洪死后,其子苻健代统其众占据关中,迁都长安。公元三百五十二年,苻健称帝,因占据古秦地,遂称国号秦,史称前秦。
飞马渐近,白衣骑士并没有减速,却伸手在怀中摸出一支足有两尺长的金制令牌高高举起。虽是傍晚,狭长的金制令牌依旧在马上划出一道闪亮的弧线。
“特使进城,行人闪开!”城门守将高声大呵,守门军士肃然立定,过往行人“哗”的闪于路旁。
白衣骑士飞驰入城。
长安城内,街市萧条冷落。和建康城繁华锦绣的夜市相比,这里简直就是荒凉偏僻的山村。店铺灯火星星点点,街边行人疏疏落落。幽幽摇曳的灯火下,可见市人衣着粗简,时有担柴牵牛者在街中缓步穿过。店铺前的人们进行着简单的交易,或钱货两清,或物物交换,都在默默进行,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争执。老城短街,静而有序,一切都是静悄悄的,但却没有一点儿慌乱。所有这些都在无声的表示,这座老城经历了无数惊涛骇浪,已经不知道恐惧为何物了。当骑术娴熟的特使纵马从街中驰过时,马不嘶鸣人不出声,也没有任何一个市人高声呼喝,街中行人迅速闪开,一副司空见惯的坦然神色。
瞬息之间,白衣快马逼近街头一片高大简朴的红砖平房。
这片砖房被一圈高高的石墙围起,仅仅漏出一片绿灿灿的屋脊。正中宫门由两扇硕大的红色木板构成,庄严肃穆。宫门前两排白衣侍卫肃然侍立。特使骤然勒马,骏马人立,昂首嘶鸣。门前侍卫统领拱手高声道:“陛下有旨,前方军情无须通禀,可直入武德殿。”
白衣人从马上一跃飞下,甩手将马缰交给统领,大步匆匆的直入宫门。不想几步之后却一个踉跄倒在地上爬不起来,他嘶哑的呼喊:“快,扶我,武德殿…”两名侍卫立即抢步上来,扶起使者疾步进入武德殿。
长安的宫殿很小,也很简陋,只是一座八进大庭院而已。且不说与晋国、燕国的宫殿不能相比,就是和自己的老国都枋头城相比,也是粗朴狭小了许多。此刻,武德殿已经亮起了灯光。这是一间陈设整肃简朴的书房,地上没有红毡,四周也没有任何纱帐窗幔之类的华贵用品。最显眼的是正对中间书案的墙面上悬挂了一幅巨大的列国地图,地图两旁挂着长剑与弓箭。所有的几案书架都是几近于黑的沉沉紫红色,使殿内颇显得威猛神秘。房间有四盏粗大的牛油灯,不是很亮,风罩口的油烟还依稀可见。一个人站在地图前沉思不动。从背面看,他身材佝偻,时时传来阵阵咳嗽,一副病态。端详片刻,他一声长吁,一拳砸在地图上,忧愤而沉重。
急促沉重的脚步声从院中传来。内侍警觉,立即轻步走下台阶。两名侍卫扶着白衣使者匆匆而来,内侍看了一眼使者立即高声报号:“龙骧将军晋见!”
咣!”的一声,殿内有人好像撞倒了什么,一阵脚步,书房主人迎了出来。窗户透出的微光下,可见他是一个敦厚的中年人,眼睛很细很长,嘴唇很厚,嘴角隐入两腮极深,只是两鬓斑白,印堂发黑,一脸病容。他不是别人,正是秦国皇帝苻健。他看了一眼白衣使者,一句话没说便要将白衣使者扶进殿******侍拱手拦住,“陛下您龙体要紧,我来。”说着两手扶住白衣人,步履轻捷的走上台阶走进殿内。苻健对两名侍卫匆匆说一声:“你们去吧。”侍卫们躬身应命间,他已经走进殿内。
白衣使者被平放在宫殿内床榻上,满面灰尘,大汗淋漓,胸脯急速起伏。他见苻健进来,连忙挣扎起身,“陛下,大事不好。”苻健摇摇手,“你先别开口。”回头吩咐,“张怀,热茶,快!”话音刚落,内侍已经从殿外拎来一壶热茶。苻健接过一杯热茶递给使者微笑道:贤侄,先喝杯热茶,这一路上一定累坏了吧。”白衣使者接过茶碗一饮而尽,这白衣使者不是别人,乃是龙骧将军苻坚,按辈分论是苻健的侄儿。苻坚自幼聪慧,八、九岁时,言谈举止犹如大人,在九岁时进宫面王,请求指派儒学老师,其祖父苻洪深为震撼,遂派人教授,苻坚醉心儒学,潜心研读经史典籍,常有经世济民、匡扶天下之心,曾有相面者言,苻坚有王霸之相。其父苻雄死后,苻坚承袭龙骧将军之位,苻坚待人宽厚,赏罚严明,深受秦军将士爱戴。
苻坚低声说道:“陛下,太子,他,哎…”
“太子怎么了,快说!”苻健急切问道。
苻坚哭诉:“他,中箭身亡了!”
苻健听到噩耗头晕目眩晕了过去,内侍张怀将其扶助。
苻坚高声呼喊:“快传太医!”站在宫殿外的侍者急忙跑去传唤太医。
太医诊脉后徐徐说道:“陛下此乃急火攻心所致,我用银针将陛下胸前淤血逼出,在服几剂汤药,定无大碍!”
苻坚拱手谢道:“有劳太医了。”
“龙骧将军言重了!”太医将两根银针分别插入苻健胸前的紫宫穴和中庭穴,苻健慢慢睁开眼睛,身体仰起。
“快,痰盂!”
一口黑血吐出,张怀拿来一块白布将苻健嘴角鲜血拭去。
“我无大碍,太医你先下去吧。”苻健孱弱说道。
太医拱手而道:“臣告退!”张怀带领侍者也出了宫殿,殿内只剩下苻健和苻坚。
苻健面色蜡黄,伏在床榻低声道:“前方战事如何?”
“我军粮草悉数被毁,太子又中箭而亡,军心浮动,幸得雷老将军稳住军心又亲自断后,使大军转危为安,现已退守蓝田。”
苻健脸色阴沉,听苻坚说完半晌没有说话。
“陛下?”苻坚有些惊慌,轻轻叫了一声。
“哎,多事之秋!”苻健一声叹息。
“如今朝中将领老得老小得小,不知谁可领军增援?”
苻坚没有说话,此等大事责任重大,他想皇上一定有了合适人选。
“本想御驾亲征,奈何这病体不堪啊!”苻健言语透露出自责与悲伤。
苻坚跪下说道:“陛下,臣愿率军增援,为您分忧!”
苻健扶起苻坚欣然道:“快快请起,果然是我苻家好男儿,朕封你为骠骑将军,率军五万前去增援!”
苻坚拱手道:“微臣领命,军情紧急,臣告退!”
“去吧!”苻健挥了挥手,苻坚走出宫殿。
望着苻坚远去的背影,苻健陷入了深思:“自己病体沉疴,自知时日不多,本想将身后大位传于太子,可惜太子不幸身亡,丧子固然心痛,但令他更担忧的是秦国的未来,皇子之中除了太子和苻生令他有些欣慰外其余皇子都是纨绔,虽然迁都长安后秦国国势日固,但外有强敌,内有忧患,秦国依然是举步维艰,将国家交于这些皇子,怎能让他放心?苻生虽然刚毅勇猛但其刚愎自用,过于好强又不能虚心纳言,喜杀狠毒又不重修德,为将尚可,为君则福祸难知。苻坚聪颖好学,为人宽厚,倒是合适人选,但如果传位于他,只怕是诸子不服祸起萧墙,历来皇室之乱,都是骨肉相残,后赵覆灭就是前车之鉴。想到这里苻健倒吸一口冷气。
西进散关的山道上,有一支军队正在兼程疾驰。
大军一路偃旗息鼓,粮草辎重都在后队。车队中有一辆精致轺车惹人注意,车中坐着一个中年人,却是那个晋国大将军桓温!这支军队一路疾行,绕行城郭,只走荒凉山路和偏僻小道。几日之间,便到达秦国重镇散关。
斥候飞马来报:“都督,散关并无异常,过往行人商旅络绎不绝!”
参军周楚大喜:“真乃天赐良机,都督下令攻城吧!”
“不,时机未到,命令大军原地休整!”桓温淡淡微笑。
周楚微微皱起眉头,不解问道:“将军何意啊,为何不趁机攻下此城?”
“兵者国之大事不可不慎,虽然我命司马勋率领两万人马伪装成我军主力向蓝田进发迷惑秦军,此中环节谁能知晓不会出现差错,被秦军探知真实意图,就算秦军没有知道我军意图,这散关乃是秦国重镇必有重兵把守,如果我们冒然攻城,守军据城而守,短时必难攻克,待到那时秦军主力从我后方包来,与守军成夹击之势,我军危矣!”
“将军所虑甚是,只是现今如何是好啊?”看到周楚一副忧愁的样子,桓温哈哈大笑。
“元孙不必烦忧,我自有筹划。”
桓温从容命令:“其一,速派细作进城打探秦军布防;其二,选出五百名精干军士化妆成百姓商贩混入城中,于午夜偷袭东门守城秦军打开城门;其三,大军趁月色埋伏在东门城外,待城门大开时,杀入城中。”
“妙,太妙了!臣领命!”周楚走出军帐。
午夜时分,秋风刺骨。东门军士又冷又困,依偎在墙角。几十个黑影悄悄的向东门移动,一名军士起夜,刚走到城边街巷,突然眼前闪过一个黑影,军士大呼:“什么人?”黑影手起刀落,军士惨死。声音响动惊起东门军士,双方一阵混战,片刻之间东门军士死伤殆尽,城门被缓缓打开,晋国大军杀入城中。
桓温厉声命令:“迅速封锁各城门,勿要放跑一人!”
“诺!”先锋大将豪爽答道。
周楚微笑:“将军是要封锁消息奇袭长安啊!”
“知我者,元孙也!”桓温大笑。
苻坚率援军赶到蓝田大营却迟迟不见晋军,派出斥候沿路打探得知晋军每日只前行三十里,心生疑惑于是前往雷弱儿营帐。
军士进账禀报:“将军,苻坚公子求见!”
“快快有请!”雷弱儿放下刀叉,起身相迎。
苻坚进入帐内拱手说道:“叨扰老将军了!”
“公子多礼了,请!”苻坚坐在账内东侧的椅子上,雷弱儿也回到座位。
“来人,上茶!”军士撤走餐食,端来两杯热茶,分放在雷弱儿与苻坚桌案上。
“公子尝尝我的苦丁茶!”苻坚端起茶碗抿了一口,顿时眉头紧锁。
“怎么样?”
苻坚微笑:“苦中有苦,令人回味无穷!”
雷弱儿呵呵一笑:“这苦丁茶我每日必饮,用它时刻提醒自己不可享于安乐,忘记忧患。”
苻坚称赞:“老将军真乃是我辈之楷模!”
“公子谬赞了,不知此来何事?”
“晋军迟迟未到,我派出斥候探知晋军每日只前行三十里,心生疑惑前来找老将军商议一下。”
雷弱儿捋了捋花白的胡须起身走到军图前,苻坚也跟了过来。雷弱儿指了指军图,“公子请看,从武关进入关中共有两条路,一路经上洛、蓝田,一路取道散关穿过关中腹地直到长安,只是武关与散关之间并没有路,只能绕道千里走陈仓小道才能到达,这样费时费力,我料晋军不会绕路,缓行只是故弄玄虚,公子不必多虑!”
“兵法有云:虚则实之,实则虚之,攻其不备,出其不意;两地山中村户以狩猎为生,来来往往,岂能无路,我料两地之间必有小路,只是不被外人所知,若桓温得知此路,袭了散关,长安不保矣!”
“公子所说有理,你我一同去面见淮南王请求分兵支援!”
“我正有此意!”苻坚和雷弱儿一同来到苻生大账。
“快去通报淮南王我们有要事求见!”雷弱儿冷冷说道。
侍卫长低声道:“淮南王有令任何人不见,还请二位大人见谅!”
骤然间,雷弱儿脸色变得铁青,高声怒喝:“大胆,军国大事岂可延误,快去通报!”
侍卫长支支吾吾不敢进去通报,雷弱儿推开侍卫长和苻坚走进大帐,只见大帐内混乱不堪,桌案上摆着一盘熟牛肉、半只肥羊腿、两坛秦风酒,还有几个空酒坛散落在地上,苻生袒胸露背躺在床榻上呼呼大睡,鼾声如雷。
雷弱儿转身质问侍卫长:“这是怎么回事,军中禁酒你不知?”
侍卫长急忙跪下回道:“淮南王酷爱饮酒,卑职执拗不过,还请雷将军恕罪!”
“你纵容淮南王饮酒犯禁,触犯军法乃是死罪!”侍卫长听闻急忙跪地求饶。
雷弱儿厉声道:“甲士何在,给我拉出去斩了!”
几名军士进入大帐拖着侍卫刚要出去,“慢!”苻坚呵停,又对雷弱儿拱手说道:“老将军,他只是遵命从事罪不至死,还望你能给他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雷弱儿长吁一口气淡然说道:“既然公子说情,老夫饶你一回,若要在犯,定斩不饶,拉出打二十军棍!”侍卫长哭泣拜谢后,被拉出军帐。
雷弱儿和苻坚见苻生深醉鼾睡,久唤不醒,只能无奈的离开军帐。二人商议,由苻坚率军三万急驰大散关!
旭日东升,秋风袭来,飘来阵阵麦香。只见官道两旁黄澄澄一片,在微风吹拂下泛起金色波浪。一支大军急驰在官道上,为首的将领正是苻坚!
远处飞来一骑,渐渐接近大军。那人到达苻坚面前,急忙下马禀报:“将军,散关失守!”苻坚听闻心头一惊,他虽然想过桓温会绕道攻打散关,但没想到失守会如此之快,散关城池高深,有两万精兵驻守,纵然敌军强攻,也不会在几日内攻下。
“将军,我们该怎么办?”身旁副将张忠问道,苻坚从沉思中惊醒,高声命令道:“大军转向灞水,急速前进!”
“诺!”众将拱手领命。苻坚又遣斥候,将散关失守的军情通报给蓝田的秦国大军。
灞河北岸的山地上,苻坚凝神南望。
遥遥可见灞河之水劈开山坳,从白云深处澎湃而来,在郁郁葱葱的广袤平原上缓缓向东流去。那滚滚滔滔的大河水,带着黄土高坡深厚的泥沙,带着关中草原的青绿,在万里无云的蔚蓝天空下,就像一条闪亮透明的绸带,温柔的缠绕着雄峻粗犷的山坳平原,竟是壮丽异常。
“这是晋军进取长安的必经之路!”苻坚指着滚滚的河水。
副将张忠会然一笑:“将军要半路截杀?”
苻坚微笑自信而道:“你只言对一半,我要截而不杀!”
“我军只有三万,敌军却有十万之众,如何拦截?”张忠质问。
“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乃《孙子兵法计篇》你可熟读?”
“这…未曾听闻!”张忠惭愧而道。
“为将者不但要勇于上阵杀敌,更应熟知兵法!”
“诺!”张忠拱手回道。
“那片谷地,扼守要道,正可安营,你带领三千军士伐木建寨,所建营寨要可容十万兵马!”苻坚望着东北方向的一片山谷淡然说道。
“诺…我懂了!”张忠笑着离开了高地。
关中的原野上烟尘蔽日,晋国十万大军大举压来!晋军偷袭散关得手后,大军没有休整,日夜兼程奔袭长安,桓温坐在轺车上正在思虑:“拿下长安后朝廷如何封赏于他,想当年他率领五万大军伐蜀,轻兵速进势如破竹一路打到CD收复了巴蜀,班师回朝时皇上(晋明帝)率领群臣出城十里恭迎,封为大司马掌管军权,晋爵吴国公食邑三万户,可以说殊荣一时;而这次如果灭了秦国,朝廷至少也应该封一个王,这些年晋国如果没有他四处征战开疆拓土,嫣能有如今的国力?想想那个懦弱无能的皇上(晋成帝)自己就气不打一出来,这个白痴偏听偏信倚重谢安、王导来制约他,总想夺他的军权,这次伐秦朝堂那些尸位老臣又是一片反对,自己力荐才迫使晋帝勉强同意,如今进展顺利,等到大军凯旋时,看那些老家伙还有何话可说?”
远方起了尘土,一骑飞驰过来。
斥候禀报:“大都督,秦军已在灞水北岸扎下三座营寨,互成掎角之势!”
“什么?”桓温惊的微微起身,又落座下来。
“都督!末将愿率军攻之!”偏将王召(字奉达)跪下请命。
桓温走下轺车扶起王召微笑道:“奉达莫急,秦军必然有备,不可盲动,传令大军在灞水南岸建营安寨!”
“诺!”众将拱手领命。
月光皎洁,秋风袭来阵阵凉意。一个魁梧的中年汉子遥望河岸,对岸星火闪耀,炊烟袅袅,波浪轻拍河岸韵律有声。一个身穿绿长袍的士子走了过来将一件蜀锦披风搭在中年汉子的肩上,汉子转身微笑:“是安国(孙盛)啊,什么时候到的?”汉子望着孙盛,“来,陪我走走!”孙盛拱手道:“刚刚赶到,都督,秋风刺骨,还是回到帐中吧!”
“无碍,你看那山头,正可观望敌军,我们到那去!”桓温指着不远处的一座小山。
桓温和孙盛带着几名侍卫登上山顶,只见在不远处有三座营寨,寨内军灯高挑,习斗声声,一片热烈景象。
“此寨依势而起扼守要道,寨前沟壑拦索纵横,寨墙设弓弩口、长枪口,寨门旁又有两座瞭望楼,如此防守深谙兵法之道,不知敌军主帅是何人?”
桓温哈哈一笑,“我也不知啊,这三座大寨可容十万大军,不知是疑兵之计还是真有此事?”
“哦,都督为何如此之说?”孙盛疑惑反问。
“安国你刚从吴中来有所不知,武关外一场恶战,秦太子苻苌中箭而亡,司马勋奇袭上洛烧了秦军粮草,秦国大军连夜撤退到蓝田,我让司马勋率领两万人马作为疑兵进军蓝田,我又亲率大军从小路进军袭了大、散关,就是想攻其不备直取长安,如今却在灞水对岸出现了秦国大军,这怎能不让人心生疑惑?”桓温徐徐说道。
孙盛眉头紧锁反问道:“消息走露,秦军回师灞水?”
“不可能,我曾命细作乔装混入蓝田刺探军情,如果秦国大军调动必有消息!”桓温摆摆手断然否决。
“如若秦军主力尽在此地,以我疲惫之师对其以逸之师,我军又深入秦地,此战可是下风啊!”“哎…”桓温一声叹息。
孙盛思忖后微笑道:“都督莫忧,我倒有一计可探知秦军虚实!”
桓温惊讶:“哦,是何计策?”
孙盛自信道:“明日都督可派出五千骑兵渡河,如若秦军趁机袭之,则可知秦军主力就在营中,如若不袭,则秦军人数必定不多,此乃虚张声势尔!”
桓温微笑:“好计,明日必知其虚实!”微风吹拂,秦军营寨内的火把越燃越烈。
第二日中午时分,晋军五千骑兵奔袭毛家口,毛家口离晋军大寨十里左右,此处河水流速缓慢,水深有一丈多,河底青砂碎石可见。
苻坚正在帐中看书,斥候进来禀报:“将军,毛家口发现大量晋军。”
苻坚思忖后说道:“毛家口滩浅水缓,晋军要渡河,快,擂鼓聚将!”
片刻后中军帐内聚集了数十名将校,苻坚身披一副银甲大步走入军帐,在作案前落座,众将齐拜:“恭迎将军!”
苻坚起身:“各位将军快快请起!”众将起身分列账内两侧,苻坚落座。
苻坚面色冷峻:“斥候来报毛家口出现大量晋军,如果我没有猜错晋军将要此处渡河,各位将军都说说该如何应对?”
副将张忠走出队列拱手高声道:“末将愿率一万精兵击之!”
“不可!”副将额日托走出队列拱手说道。
张忠厉声道:“为何?”
额日托拱手道:“敌众我寡,不可贸然出击,不如坚守营寨,等待大军回援!”
“原来是想当缩头乌龟啊!”张忠哈哈大笑。
额日托指着张忠骂道:“你…你这个白痴,老子带兵打仗的时候,你还不知还在哪个婊子肚子里!”
张忠大怒,上去就给额日托一拳,额日托也不依不饶与张忠厮打起来。
苻坚大喝:“都给我住手!”张忠和额日托松开了对方衣领,一脸怒色。
苻坚高声道:“甲士何在?”四名军士进入大帐,“将二人拉出去各打三十军棍!”
“诺!”军士们拱手答道。
众将跪下求情,苻坚脸色变得铁青,高声怒道:“军法无情此事不必再议,拉下去!”军士将二人带出营帐。
苻坚起身命令:“传我将令,留下三千军士看守营寨,其余人马全部随我出击!”
“诺!”众将拱手答道。
斗大的日头在蔚蓝天空高悬,一阵阵热浪腾地而起,热的河边的老牛喘着粗气跑入水中,躲避这炎热的天气,晋兵三五成群躲入河边的小树林里,一个个东倒西歪躺在树荫下乘凉,栓在林边的战马偶尔发出几声嘶鸣。
一名军士敞开胸倚在树根对旁边的一名老军士抱怨:“老军头,这天咋这么热啊?”
老军士微笑道:“秋老虎的日头毒着呢,更何况在这关中地,慢慢忍吧!”
“关中地怎么了?”军士疑问,“一看你这娃子就是从军不久,没离开家乡吧。”老军士眯着两眼微笑。“你怎么知道?”军士惊讶坐直了身,“这关中不比江南,这地四季分明春夏秋冬依次更替,要说最毒的日头还是这秋天,夏季虽然炎热,但多雨所以不是那么难挨,可是到了秋天这地一两个月也难见雨水,热气上浮万物干燥,便觉得最闷热,常年老军都知此理。”老军士缕着胡须得意说道。“哦,原来如此,以后还请老哥哥多多照顾。”军士拱手。“好说,好说!”老军士呵呵一笑。
王召站在林边遥望河岸,额头渗满了汗珠他用手拭去骂道:“娘的,这鬼地方,早晚冷的刺骨,日中太阳却这么毒!”一个小校拿着一个牛皮水袋走了过来低声笑道:“将军,喝点酒,消消暑!”
王召转身打量小校一番,冷笑道:“酒,哪来的,军中禁酒你不知吗?”
小校慌忙跪下战战兢兢:“知道,我军军纪严明明令禁酒,可这酒有解暑之功效,前几日大军路过村镇小人特意购来准备献给将军以解酷暑,将军身系万军之众不可有失,至于犯禁之罪,卑职愿意承担。”
王召嗜酒军中共知不可一日不饮,只是此次跟随桓温出征,深知桓温执法如山不容私情,所以才没敢犯禁。这几日王召早已酒虫翻腾,此刻只是故作镇定。“快快请起。”王召扶起小校,又对着耳语道:“可有人知晓?”“将军放心,无人知晓!”小校微微一笑。王召锤了一下小校右肩爽朗笑道:“好小子,以后少不了你的好处。”“多谢将军关照。”小校双手恭献。王召拿起水袋拔出袋塞,一股香醇酒香扑鼻而来,王召一口气饮了半袋,爽朗直呼过瘾!
对岸扬起一片尘土,王召看在眼里,他将剩下的半袋酒别在腰间,高声命令:“整军!”躲在林子里的军士慌了神,边跑边整理衣衫盔甲,片刻后军士们都骑上战马,列队在河边。王召走马巡视一圈后厉声命令:“渡河!”五千骑兵驱马渡河,刚行至河中,突见北岸箭雨飞来,许多军士中箭坠马。王召见此大呼撤退,北侧林边冲出数万精骑,刹那间双方混战一起,刀箭声、喊杀声响彻天地。
清澈的河水染成雪红一片,水中尸体几乎堵塞河水,孤零零的战马矗立在河中,等待着主人的归来,栖息在树上的乌鸦发出几声哀鸣。王召一身血污刚一进账就跪下哭泣道:“都督,卑职有罪啊!”桓温急忙扶起王召悠然笑道:“将军何罪之有?”“五千人马,伤亡殆尽,若不是王珏将军接应,恐怕就要全军覆灭了,卑职丧师辱国,此乃死罪!”王召拱手下跪。“在我看来,将军不但无罪,而且有功!”桓温摆摆手,示意王召起身。“今日一战,秦军虚实尽知,损兵折将乃我之过也,是我调度有失,与将军无关,将军乃是按计行事,赏王召三百金,绸缎二百匹,晋爵一级。”桓温微笑。“谢大帅!”王召拜谢。“下去疗伤吧。”桓温挥挥衣袖,王召走出军帐。“你们也都下去吧,安国留一下!”众将散去,只留下孙盛一人在帐。“安国今日之战你怎么看?”桓温笑问。“数万精骑埋伏掩杀,应是秦军主力所为!”孙盛拱手答道。“我想也是如此,看来定有一场苦战了!”桓温油然一叹。
秦军大胜回营众将一脸喜悦只有主将苻坚神情自若,一到营帐就急忙修书,派遣特使奔赴蓝田求援。雷弱儿几次请求回师都被苻生严词拒绝,苻生自信认为晋军主力依然在蓝田方向,散关失守之事,只是桓温故意散布流言意图调开秦国大军,好趁机占了蓝田。苻生自幼独眼,性格孤傲固执异常,年幼时,其祖父苻洪与侍者言道:“独眼人不流泪不知真否?”苻生闻之大怒,拿出匕首刺向其臂鲜血直流,笑问:“老儿此等为何物,不是泪吗?”苻洪发怒,拿起鞭子抽打,苻生坦然一笑:“生来不怕刀刺,岂能受不了鞭刑。”后众人劝解此事才作了,苻生这倔强脾气却是秦国朝野皆知。
雷弱儿心情愁怅,在帐中踱步,侍卫进账禀报:“骠骑将军特使求见!”“快快有请!”雷弱儿急切回道。特使进账参拜:“参见将军!”“快快请起。”雷弱儿扶起特使。“这是骠骑将军给您的信。”特使从衣袖拿出一封书信递给雷弱儿。“带特使去用饭。”雷弱儿吩咐道。“谢将军。”特使跟随侍卫出了军帐。雷弱儿拆除信口蜡印,抽出信件读到:
雷老将军台鉴:
晋军十万兵临灞水长安危急,我部依靠地势施疑兵之计与敌周旋,两军对峙灞水,然则日久天长敌军必知我军虚实,大军攻之我军必破,长安不保也。军情似火,望将军以国家社稷为重,力谏淮南王回师救援,我部盼援军如大旱盼甘霖,我面南叩拜,乞求将军玉成此事,望速之,速之。
永和十年秋苻坚亲笔
雷弱儿收起信件急匆匆赶往苻生营帐,要面见苻生却被拒见,呈递苻坚手书苻生依然置若罔闻,不肯发兵救援。雷弱儿来到中军大帐前敲起军鼓,军营内响起阵阵鼓声。众将急忙赶往中军大帐。“谁在擂鼓?”苻生惊讶。侍卫惶恐低声道:“小人不知。”“去看看。”苻生带领侍卫来到中军大帐,只见账内分列众将。苻生厉声道:“没有我令,何人聚将?”雷弱儿高声回应:“是我!”从队列中走出。苻生一声冷笑:“你好大的胆子,私自聚将该当何罪?”“我无罪,倒是淮南王迟迟不肯发兵救援,不知是何居心?”雷弱儿大笑回道。“来人,拖下去杖责五十军棍!”军士进入账内正要拖拽。“且慢,我有话讲?”雷弱儿挣开军士。“勿要狡辩,拖下去!”众将求情,苻生执拗不过挥挥手示意放开雷弱儿。“桓温大军已经兵临灞水,如果再不回师援救,长安危矣,秦国危矣!”雷弱儿陈情而道。众将闻之大惊,纷纷请命率军回援。苻生见此形势思忖后说道:“我亲自引军去救!”“众将听令,雷老将军率领三万精兵据守蓝天,不得有误,其余各将各司其职,今日申时大军开拔,兵进灞水!”苻命令道。“诺!”众将拱手答道。雷弱儿深知苻生勇武少谋,好意气用事,知其不是桓温敌手,况且与苻坚有嫌隙,不放心其率军救援,于是拱手说道:“淮南王,老夫愿意率军去救,由您镇守蓝天。”苻生走到雷弱儿面前冷笑道:“哦,你轻视我?雷弱儿拱手回道:“臣不敢!”“既然如此,那就遵令吧,散帐!”苻生拂袖而去。
雷弱儿一声叹息踉踉跄跄走出军帐,账外吹起一阵狂风,中军大旗被风折断。雷弱儿心里不安:“上天啊,上天,难道你真要灭亡秦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