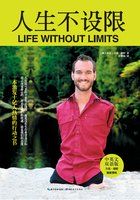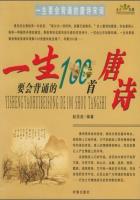“军旗,军旗,在心中飘啊飘……
再理理飘带,整整军帽
我们踏着波涛远航归来了
你好啊,亲爱的祖国,妈妈呀你好,你好。”
这首不记得名字的军歌现在已经唱不全了,不过一直觉得这首歌的曲作者应该是体验过远航生活的,旋律中那种跳跃并且欢快的感觉极为准确地捕捉到了水兵们远航归来的欣喜之情。
经过几天航渡,我们舰艇由南向北,日夜兼程,终于回到了那片我们所熟悉的海区,进入了我们已经当作回家一样的那个熟悉的军港。
不出我们所料,舰艇在缓缓靠上码头的时候,远远地就看到了码头上已经有支队领导和欢迎我们的人群等候在那里了。在支队业余军乐队演奏的铿锵乐曲声中,真的感受到了一点儿凯旋的意思。
抛锚。
撇缆。
搭上舰桥。
舰艇靠上码头,我们重归陆地。
在双脚踩上坚实的码头时,似乎有些不适应,平时脚底下都是飘动着的,一踩上码头,倒觉得腿有些发软,码头都有些飘移的感觉。
老兵们管这种现象叫“晕码头”,正常的身体反应。
尽管在前两天在航渡的时候,政委就在全舰搞过教育,意思就是靠上码头之后大家要继续保持在南沙的作风,不要一靠上码头就跟撒欢似的,忘乎所以。要求各部门加大管理力度,好好总结任务,总结在执行任务过程中的什么好经验、好人好事之类的。
但教育是教育,现实是现实。
有时候,舰领导自己也难以做到教育中提到的那些要求的。比如说晚饭时,好像是支队领导的车吧,把舰上的一号二号都接走了,应该是洗尘的饭局吧,我们其实挺盼望头头们都不在。舰上还剩一个舰副长值班,大概是一号二号走的时候放话了码头范围内自由活动,副长也就半管不管的了。
等到天黑下来了,舰上除了运气较差正好轮到值更的,谁都没在舰上呆着。
军港里到处能看到我们舰上的人,不过最多的还是电话亭边上。三个话亭后面排起了队伍,一看差不多都是我们舰上的熟悉面孔。
我看到余大可也排在队伍当中,他和后面等着的战友们一样,目不斜视一脸期待地等着前面拿着话筒的那位哥们说完。别的舰上要打电话见这阵式都离开了,大概他们也能理解远航归来的心情吧。
毕竟两个多月的时间了,打个电话,或是给家中的父母报一个平安,或是跟自己的爱人缠绵几句别后的思念。
然而我呢?突然有一丝隐隐的孤单袭上心头。
我没逗留,绕过电话亭,一个人往俱乐部那边走了。
看了一会儿书,觉得没意思,又从俱乐部里出来,不知道为什么,好像自己是下意识地又走回到刚才电话亭这里。
余大可正站在电话亭里面,一脸幸福地说着什么,我在不远处的路灯底下看着他。
可能是看到了我,我发现他正在亭子里和我招手,像是让我等他一会儿似的。
不到一分钟的功夫,他放下电话,朝我这边小跑过来。
“干嘛呢,深沉兮兮的啊。”他站定,问我。
“刚好路过啊。”我说的时候迈步往码头方向走了,不想让他看出来自己刚才的那种落寞感觉。
“怎么不打个电话回家?”余大可这句话一说出来,他自己也意识到有点不对,他是知道我的一些家庭情况的。
“人太多了,我明天再打。”我让自己轻松一些,免得让他觉得刚才的问话不合适。
“对对对,打电话还得排队,一个字,落后!咱们上那边转转吧。”余大可不知道是征求我的意见,还是命令似地,不等我说话,自己已经往前走了。
他说的是露天影院那边。
那个露天影院是依傍着一座小山而建,靠着山的一面修建了半圈水泥台阶,一级一级的一直顺着山势,建成一个弧形,与对面的浅弧形高墙连成一个封闭的椭圆形空间,高墙的中间稍微平整一些的地方刷着很白的一块四方形,那就是放电影时的屏幕了。
这大概是军港礼堂还未建起来时的第一代影院了,一直到现在,特别是夏天奇热无比的时候,礼堂的风扇不管用,电影还是在这个露天的地方来放映。
余大可在边上的小卖部买了两瓶啤酒和几袋小吃,我们一起从小卖部的侧门进了露天影院。
里面有几个和我们一样的兄弟舰的战友,坐在底下的台阶上一边喝着啤酒,一边大声说话。倒是显得里面有一些空旷的静。
从高高的台阶和那面高墙围成的空间抬头往上看时,不知道为什么竟然让我想起古奥林匹克那个椭圆形的体育场来。
几颗星星挂在头顶上方幽深的天幕中,泛着或许与古罗马时期一样的光芒。
余大可像是什么时候侦察过一样,提着装啤酒的袋子轻车熟路地走到台阶的最高一层,然后转角,再跳下几级台阶,就跳到了眼前的这块平地上。
这是一块山腰的平地,挡在台阶的后面,几棵不知名的树掩映着从侧面飘过来的军港上的灯光。
余大可一屁股坐到地上,放下袋子,用牙咬开啤酒瓶盖,递给还站着的我一瓶,说:
“靠,坐啊你!”
我接过大可递过来的啤酒,坐在一块裸露的石头上。
坐下来的时候,我环顾了一下四周。才发现这儿是个不容易被人发现的隐幽之地,至少不会有被军港纠察发现私自饮酒什么之类的担心。从地上散落的一些易拉罐和被雨水冲刷的有些泛白的蒙牛伊犁的包装袋能够看得出来,这个地方肯定也不只有我们来过。
余大可靠着对面的一棵树坐下,我们相对而坐。
他把刚才提东西的塑料袋铺在地上,再把买的那几袋小吃撕开,放在袋子上面。也没看我,就用他手里的酒瓶碰了下我的瓶颈,一仰脖,咕咚咚地喝了几大口。
“青岛啤酒,真他妈爽口!”他半举着酒瓶,跟做广告似地感叹了一句。
“青啤找你形象代言啊?”
“哈哈,找我还不一定去呢。”
余大可一边笑,一边又举起酒瓶。
依稀灯光里,能看到他手里握着的瓶子倒过来时酒花泛起,我看到他在仰头时,他的喉节随着饮酒的吞咽节奏上下移动,瓶子从他嘴里拿下的时候,有啤酒白色的泡沫从瓶口里溢出,他赶忙用嘴去含住瓶口,又有些怕我会笑话他似的,边抬眼看我。
“慢点,没人跟你抢。”
“嘿嘿,口渴。”
“啤酒能解渴啊。”
“那是,差不多就是饮料吧。”
我拿起刚刚大可递过来的酒喝了一口,觉得味道确实有些甜甜的,仿佛有一些那天晚上星月与空气中清新的味道。
这样两人对面而饮的感觉,又让我有了某一种期待。这种期待不同于远航途中的那个小舱室里,那次或多或少总有些盲目的,对他是未知的,而现在怎么说也多了一些对他的了解,至少觉得他不会很排斥,至少还记得他在那一刻时的表情是那般的遇推却迎的复杂和可爱。并且我一厢情愿地认为,在这样静无人迹的地方,只有两个人,期待,在我和他之间,总有一些心照不宣的意味。
只是那时刻,我们不知道如何开始而已。所有相关不相关的话语,动作,表情,在我看来,似乎都在徘徊着、接近着,慢慢地靠近那个我们所“期待”的中心。
“丛深沉,求求你,别老这么深沉行不行啊?”
余大可放下酒瓶,打破短暂的安静。
“我有深沉吗,在欣赏青啤代言人的代言形象呢。”
我看着他的眼睛说。
“靠。”
他犹疑地躲闪开我的眼神。
“不知道这次咱们出海费能发多少钱?”
余大可看着远处军港的灯光说。
“应该比较可观吧,海上那么长时间呢”
“估计能有多少啊?”
“那我哪儿知道,我又不是军需,不过你要是等这钱娶媳妇那肯定不够。”
“你还知道娶媳妇呢?”
“我干嘛不知道,什么意思啊?”
“哈哈,上次你不是说只喜欢那个,什么吗?”
“那个什么?”
“什么什么啊,你小子喜欢什么,关我鸟事。”
“你知道当然跟你有关的!”
余大可选择迂回,但我单刀直入。
“靠,丛深沉,现在要是有DV把你录下来,你就知道你的眼睛有多吓人了!”
“是吗,肯定没有韩版帅哥的单眼皮更吓人吧?”
我仍然盯着眼前的余大可说,我都能感觉到自己当时的眼神有多么肆无忌惮。
余大可又拿起啤酒瓶,掩饰他的某种不安似地,喝了一大口,他的那一瓶已经快要见底了。放下瓶子的时候,他突然用一种关心,又像是在求证什么似的语气问我:
“丛彬,那你想过以后怎么办吗?”
“什么以后?”
“就像你现在这样的啊,以后怎么办呢?”
“我现在哪样了?”
“靠,你小子再跟我绕,就回去了啊。”
“回吧,又不是我要来这儿的。你这么问,是好奇呢,还是关心?”
“当然是关心!——也有好奇,都有吧。”
“要是好奇我就不说了。”
“关心,关心,关心!靠。”
“这还差不多。我没怎么想过以后啊,走一步算一步了,过自己想过的那种生活吧,反正也不会有亲人这边的压力了。”
“但还会有社会上的!如果一直都是一个人的话!”
“人活着怎么着不都得有压力啊。如果不是一个人,如果结婚,那只会让我更有压力,我何必找一个无辜的女孩来分担这种原本不必要也根本不属于她的压力呢?”
“你不试试怎么知道?”
“这就是天生的,是不可能改变得了的。”
“也许试试会有改变的。”
“不可能!”
“可是我要试试!”
余大可又拿起瓶子,仰脖喝的时候,才发现酒瓶已经空了,就顺手扔在一边,从衣服口袋里掏出烟来,点燃。在打火机点燃的时候,我发现他的脸不知道是那火光映的,还是因为什么,红红的,像一个做错事的孩子正在坦白什么一样。
“我发现这段时间我老在想那天的那种感觉,真的,控制不住地想。我一遍一遍跟自己说,我们是好哥们儿,只是好哥们儿,但又老往那方面想,靠!!我是不是也完了啊?”
余大可很迷惘,有些苦闷地看着我。
在他眼神当中,我坐到他身边,手放在他的肩上。谁知他突然甩开我的手,猛地一把将我推开,一不留神,我摔倒在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