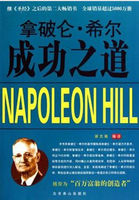入夜,我点上油灯,望着跳跃的火苗怔怔发呆。
“吱嘎——”一声,窗子被一阵冷风掀起。我起身正要合窗,只觉得“嗖——”的一下,一个黑影从耳边划过。
我愣愣地回头,已有一个黑衣人站在身后。我惊讶地失声要喊,那人却早已快一步贴近身侧。他提剑的手捉住我的左手背在身后,将整个人扣于胸前,另一手紧紧捂住我的嘴,使其不能发出一点声音。
我瞪大了眼睛,凝视着这黑面纱上的眼睛——漆黑如墨,光影流转。那眼神与我四目交接,竟闪过一丝的诧异。
“别喊——你只要安静——我就不伤害你。”他压低了声音,我听着却觉得有几分熟悉。我使劲点了点头,依稀间嗅出一丝甜香——是他!
“是你吗,章大人?”我用力掰开他覆住口鼻的手,难以置信地问。
“……”他撇开眼眸,似在默认。
容不得我再次开口,窗外的夜色越来越亮。隔着桃花糊纸,已经隐隐约约可以看到那高涨的火把上跳着的火光。
“宫里有一个刺客,还不给我好好搜搜——”我辨得出,那是尹魏胜的声音。接着一阵纷沓的脚步扰乱了这夜色宁静。
“怎么回事?”我回头问他。
“一时说不清——”章居对我梁摇着头,“但相信我,我不是刺客。”他放开了我的手,眉头一皱,发出呻吟。此刻,我才发现,原来他的肩膊早已受伤。汩汩的血流与黑色的夜行衣融为一色,难以辨别。
听着外面渐近的吵闹声,显然,尹魏胜动用了场工的密卫在大肆搜索。我住的“仕女馆”只怕早已被团团围住。此刻,章居梁就是插翅也难飞。我知道多说无益,为今之计,只有赶快引开尹魏胜的注意。
“拿你的剑刺我——”我拉起他手中的剑,指着自己的肩头。
“什么?”章居梁莫名地看着我,不明白其中的意思。
“刺我!”我急着低低地喊。“快——”
“不行——你会受伤。此事,与你无干。”他摇着头,欲意转身。
我深吸一口气,捉住他拿剑的手,身子猛地往前一挺。那锋利轻薄的剑身便“哧——”的一声没入筋肉,鲜血瞬时染红了整个肩头。我的脸猛地一抽,再次提气,将他往后狠狠一推,剑身又倒抽出去,离开肩膊。我只觉得一种剜心的疼痛,险要晕阙。章居梁一个箭步上前,将我抱在怀中。他茫然地看着我,仿佛在问,这是为何?
“你——不要离开这个房间——躲到我床上,用褥子盖好全身——快”细细密密的冷汗凝在额头。我努力喘息着,用力将他往内屋床的方向一推,“记住——无论发生什么——都不要出声。”
章居梁看着我的眼神依旧满是困惑,但他还是听从我的话往内屋走去。
我估摸着他隐藏得差不多。一咬牙,大声喊了一句“救命——”便扑出了门外。
“尹场主——救命。”我飞扑到尹魏胜的脚下,一手捂住流血的肩头,一手拽着他的袍子哭喊。
“是你——”尹魏胜蹲下身子,借着火光,看清了满身血污的我。“你这是——”
“尹场主——刚才,刚才有一个黑衣人闯进我的屋子——”我啜泣着跪在他脚边,“奴婢很害怕——正要叫喊——哪知道那黑衣人不容多说就一剑刺来——如果,不是奴婢躲得及时,只怕已经丧身他的剑下。”
“那黑衣人呢?”他揪住我的衣领,瞪大了眼睛问。
“他恐是怕场主追来,也不与奴婢纠缠,就又飞身窗外逃出去了。”我指着屋子外一条小道,“侍女馆为了能及时服侍各宫主子,每条路都通向各宫。奴婢窗外那条路是通向咸阳宫的——”
听罢,尹魏胜站起身果断地下达指令:“留下五十个密卫围住侍女馆,其余的都追去咸阳宫——记住,要不动声响——免得惊扰了纯嫔。”
“是——”
“果沫儿姑姑——”尹魏胜皮笑肉不笑地拉起我,“既然你是最后一个见过刺客的人——就劳烦你跟咱家走一趟养心殿,给皇上回个话吧。”
养心殿的地砖是用上好的大理石砌成,光如明镜,硬若金刚。我捂着肩头,跪在堂前,膝头只觉得刀割锤砸般的生疼。太医对伤口做了简单的处理,撒了点止血粉便退下了。肩膊虽不再流血,但刚才被小太监们半搀半拽地过来,筋肉错位,到现在,我都痛得直冒冷汗。
“你这伤可是被尹魏胜围剿的刺客所伤?”灵帝披着一件江绸龙褂,浅金色的寝衣露出了金丝银线绣得五爪金龙的一角。如云的青丝被一条皇绸束着,深邃的眼睛下略显青痕——看来这场夜袭真的没有让他休息好。他斜靠在龙爪扶手上,半寐着细长的眸子。其中的深意,让人实在难测。
“是——”我忍着伤口的痛楚,有气无力地点头。
“你可记得——那黑衣人的样子?”他问。
我心中一抽,琢磨着这句话究竟有多少深意?灵帝和尹魏胜究竟有没有看清章居梁的样子?我究竟又该如何帮章居梁隐瞒?
脑子在短短一瞬百转千回。我知道,此刻除了撒谎已无他法。只能心一横——若是被识穿便也是为他一死。常年在深宫谨小慎微,我不知道自己怎么变得会如此莽撞糊涂。但未来得及深思,我已开口回答:“此人脸蒙面纱,奴婢并不能看得真切。但是奴婢记得,他身形颇高,大约——大约,”我故作回忆地锁住眉头慢慢说着,“大约高过奴婢半个身子。而且体格精瘦。还有——虽遮着面纱,但奴婢记得清楚——他的眉眼细长,且——左眼下方有一颗黑痣。”我掺着真真假假,假假真真的话,只望灵帝能够相信这些。
他沉默地看着我,脸上没有任何表情,深不可测的眼眸让人难以猜测。
尹魏胜见状,便身子微躬道:“皇上——那黑衣人身手极快,奴才问过手下,大多没有看清。果沫儿姑姑是唯一一个与黑衣人正面交锋,且受他一剑,所说的多半不会有假。”
灵帝依旧静默地看着我。此刻,肩膊的剧痛瞬间消失。替代而来的,是来自于帝王巨大的压迫。他虽不言语,也不曾靠近,但是我的身子却是止不住地颤抖,仿佛赤身地面对着眼前这个男人,所有的话语都变得没有说服力。
“你起来吧。”他终于开口,语气平淡的没有声调。我猜不透,自己有没有过这一关。只能颤颤巍巍地勉强起身。
岂料,肩膊的伤处被牵动了经脉,人因为一丝阴冷的刺痛,不由一个踉跄。一方丝帕悄无声息地从胸口滑落,静静地躺在那泛着青光的大理石上。
“这是很么?”我来不及佯装跌到,企图用衣裙遮住那方丝帕前。尹魏胜眼尖早已发现。他快我一步捡起那方青色娟帕,冷眼质问。
“这——是奴婢,无意中在御花园捡来的。”我叩首回答,心里的恐惧如同突然而至的暴雨,将整个人浸透在惶恐之中。原本颤抖的身体更加抑制不住。我狠狠咬住嘴唇,牙齿深深切入嘴唇中——只希望用这疼痛来换得一丝冷静。
“是吗?”一直沉静不语的灵帝突然冷笑起来,“尹魏胜,呈上来。”
“是——”
丝帕在他手中反复把握,他眯着细长的眼眸像是在研究古董一样,探究着这方简单的娟帕。“这看上去像是一个男子的贴身之物——你是说,从御花园里捡来的?”
“……是。”颤抖的嘴唇抑制不住,发出的声音都在发颤。
“如此,朕就觉得奇怪,一个陌生男子的私物,你为何一直收纳在贴身之处?”他冷冷叱责,“难道你要告诉朕,打算随时还给失主这样的蠢话?大胆——你这小小的宫婢,真的打算把朕当做蠢物愚弄吗?”
“奴婢不敢——奴婢不敢——”头重重地磕在质地坚硬的大理石上,没有几下,额头只觉得一阵黏腻。鲜血慢慢滑落,零星渗入眼眸。我却顾不得擦拭,只能磕头如捣蒜求饶。
“大胆婢子——竟敢凡欺君之罪,皇上——奴才这就将她活埋乱葬岗。”尹魏胜借机应承。
“哼——先不急——如若你肯说实话,朕且饶你这一回。如若你不想说实话——朕就将你交由尹魏胜处置。”他淡淡的语气,像是此刻的氛围毫不紧张,“这一回,你可别想再次借太妃之名,求得生机。”
事已至此,我已退无可退。供出章居梁,我怕此生难安。但是,若说一个普通的谎话,灵帝心细如尘,只怕会被轻易揭穿,瞬时命丧九泉。
灵帝心细,但而今他内心最大的忌讳,就是当朝的太后——思及此,我决定拼上性命,为章居梁,也为自己搏一搏。
“奴婢该死——但奴婢实不是有心欺瞒圣上。只是,有些事,奴婢尚未查明,不敢随意乱说。”我用尽全身力气,让自己面不改色地扯着这个弥天大谎,“这丝帕确是奴婢捡来——只是——不在御花园——而是,今日白天,奴婢被太后叫去问话时,在凤阳宫的路上捡来的。”
“胡说——凤阳宫是太后的寝殿——怎会有男子的私物。难道你是指太后与人私通?”尹魏胜眼话虽语带叱责,但口气却带着几分讥讽。
“奴婢不敢再欺瞒圣上。”我立时回答,“正是如此,奴婢心中又惊又恐,不知该与何人述说,又不晓得如何处置这方丝帕,只好先贴身收藏。”我心一横,继续道,“奴婢想着,这丝帕虽遗落在凤阳宫,但究竟此人来见太后还是来见凤阳宫里其他人,暂且不明。又或许是哪个大人或御医探视太后,不慎将私物遗落也未可知。”
“**御医闻诊后。宫向来规矩颇多,也行为恪守——要遗落这样的私物,怕是不会。”尹魏胜若有所思地说着,“若是有旁的男子与凤阳宫的宫人私通?太**规甚严,这人岂不是胆大包天——只是若有哪个大人探视太后遗落私物——倒是有几分可信。”
“够了——”灵帝一扬手,“此事,由不得你们私下揣测——果沫儿——这事你可还与别人说过?”
“兹事体大,奴婢不敢。”
“尹魏胜——将着脏东西拿去,派你场工的密卫好好调查一番。”
“是——”
“皇上——恕奴婢直言——”如果尹魏胜的密卫去查,要查到物主是章居梁,恐怕是轻而易举。如此一来,只恐是我将祸水泼在了他的身上。“这丝帕还是让奴婢悄无声息地放回凤阳宫为好。”
“你说什么?”灵帝皱起眉头。
“虽然场工的密卫做事来去无踪。但是此事一查,难保不会生出枝节。太后在深宫久居,耳目众多,只怕打草惊蛇——”我冷静地分析,“再者,此事若只是宫人私通,尹公公的密卫只怕是大材小用。奴婢愚见——以为将丝帕放回原处,守株待兔——兴许,牛鬼蛇神是谁,就会现出原形。”
“……”灵帝沉思半响,他的眼睛不停地在我的脸上来回扫视。我若不是豁出一死的心,鼓足力气支撑,只怕也要败露马脚。
“皇上曾要奴婢接近太后,盯住凤阳宫的一举一动——此番调查,实属奴婢分内之事,定当竭尽心力。”
“你小小年纪——心思倒深沉。”灵帝一直毫无涟漪的冷脸终于淡然一笑,“好吧——这事就交予你——”尹魏胜按着灵帝的示意,将丝帕再次交回我的手中,“你下去吧。”
“是——奴婢告退。”走出养心殿,我紧紧将丝帕按压在胸口——章居梁——你到底是为什么?
“皇上——可信的过果沫儿?”看着朱赤大门被合上,尹魏胜疑惑地看着眼前的帝王。他向来生性多疑,此刻怎么就这样轻易放了过去。
“呵呵——她自以为聪明,所作所说,不过是为了护住那帕子的主人。若朕一味揭穿,只怕只会让她拼死不说。”周煜想着那张还带稚气的脸,却如此坚定不移地说着弥天大谎,可见她心里有多在乎这个男子——偌大的深宫,自己姬妾诸多,却只怕没有一个女子愿为自己拼死守护,“她要护的不过是她的情郎——朕却丝毫不关心此事——朕要的是她竭尽所有,做太后身边的细作——若此前,她还有半分退路。此次——只怕如何都要给朕一个交代。”
“原来如此——皇上圣明。”尹魏胜顺势拍马。
“好了——闹了一夜,朕也倦了——那丫头诡计颇多,却也不失为一个细作的人才——她刚才说的关于黑衣人一事,你只可听其一二——再暗自去查,明白吗?”
“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