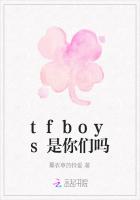昨日才立过夏,今个儿的日头就毒辣起来。
凤阳城西门口有个茶摊,四根竹竿插在地上,撑起一块满是油污的帆布,底下四方摆了八张条凳,中间支了三口大锅,锅里盛满了煮好的茶。
卖茶老汉随意坐在其中一条凳子上,吧嗒吧嗒抽着旱烟,身旁摆了一个大瓦罐,谁来了想喝碗茶,往里丢一文钱,然后自个儿拿碗去锅里舀茶喝。赶脚的汉子们都称这里“一文茶摊”。天愈热,茶摊的生意愈好。城西门口当值的官差有些热不住,分批来一文钱茶摊喝茶乘凉。
官差们故意拿架子,闲汉脚夫们却也不怕,与官差们一起聊些谁家女娃长的愈发俊俏了,哪家寡妇与谁生出什么风流事儿了。说到动情处还会有哪个不顾面皮的家伙模仿女人搔首弄姿一番,惹得大伙一阵哄笑,真真是官民一家,其乐融融。
不知何时茶摊边站了一个中年和尚。
和尚既瘦且高,一身灰布长袍,肩膀几处破洞也未打补丁,右手拄一根树枝,左手拿一只钵盂。若不是还算整洁的面相和脚上八成新的草鞋,直当他是个乞儿了。
估摸着他听晕段子有一阵了,却也脸不红心不跳,扫视了一圈,将钵盂挂在树枝突出的枝丫上,对着卖茶老汉单手施了一礼,道:
“我佛慈悲,贫僧欲讨碗水喝。”
见老汉拿烟锅子朝装茶的大锅指了指,和尚便取下钵盂,舀了一钵茶水,小心翼翼走到一根竹竿旁坐下,不让一滴茶漏出。喝一口茶,咂咂嘴,而后一脸满足回味,似是喝了什么了不得的好茶,看的闲汉们也忍不住喝了一大口。
“啐,真难喝。”
有道是希望愈大,失望愈大,连往日喝惯了的茶也变苦了。
闲汉们不再不理会那和尚,自顾聊了起来。
“诶,要说咱们县令大人,这许多年来兢兢业业,为民做主,真是咱们的父母官,却也不知哪里得罪了老天爷,夫人难产去世不说,连小公子也得了十分罕见的怪病,当真是好人没好报么?”
“我说陈二,咱们江大人已够烦心,你就别再嚼舌根了,真要为大人好,每日上三炷香替大人祈福一番才是正经。”
官差们平时多得县令大人的照顾,此时必然护着自个儿的大人。
陈二感觉中自己并无恶意,却平白遭了一顿呛,当下憋红了脸,却也不敢发作,一口将碗内茶水喝尽,转身便走。
陈二是个老实的庄稼人,也是个苦命人。三年前一场大火,烧去了陈二的双亲、陈大、一头老黄牛,只剩下陈二成了家里的老大。年仅十六的陈二在废墟前呆坐思考如何能去找他们,只坐了两天就饿昏过去,醒来才知县令大人把他的命捡了回来。而后又给他出资修了新屋,拨了几亩良田,去年还替他保了个媳妇,如今有了个儿子已冒了四颗牙儿了。
陈二心中感恩,给大人当牛做马也心甘情愿,只是受了大人恩惠的百姓不计其数,轮不到他陈二报恩。因此陈二每日里都会往大人府上送些自家种的新鲜时蔬水果,让自己心中好受些。陈二离开茶摊,并未直接返家,而是进了西街的古玩集市。左挑右选,花去全部私房购了一只还黏着潮湿泥土的香炉。生怕遭有心人惦记上,将香炉抱入怀中匆匆往家赶。用店家的话说,此乃宋朝年间某某妃子为天子祈福用的香炉,是天师开过光的宝物。
满香正抱着儿子在树下乘凉,一边摇扇子一边打瞌睡,哺乳期的女人总是睡眠不足。
“吱吖”一声,满香被惊醒,是丈夫陈二回来了。
“娃他爹,这光天白日的,你鬼鬼祟祟的莫不是做了贼。”
满香见丈夫偷摸进了屋,也不打声招呼,有些疑惑。
“他娘的,我若做了贼,先偷了赵平(官差)家的闺女。”
陈二说着,一手将香炉从门里伸出来晃了晃。
“瞧见没,这乃是天师开过光的宝物,皇后娘娘都用来祈福的宝物。从今日起,我便每日为县令大人烧香祈福,望大人早日摆脱厄运,福泽加身。”
满香听丈夫是为了大人祈福,也不去管丈夫先前的胡言乱语,甚至连买这香炉的钱是何处来的也忘了盘问,抱着孩子进了屋。
见陈二已将香炉摆在台案上,燃了三炷香,便走到丈夫的身旁,抱着孩子与陈二一同拜了三拜。
看那香烟袅袅升腾,陈二心中总算通了口气,仿似那好运已降临到大人身上。
“南无阿弥陀佛。”
突如其来的佛唱将夫妻二人吓回了神。回头一望,只见门中立着一个高大人影,再仔细一瞧,正是那茶摊上讨茶喝的和尚。
“我佛慈悲,贫僧不请自来,多有叨扰,还望施主勿要见怪。”
那和尚说的客气,身体却已走到桌旁坐下,将树枝放在一边,拎起茶壶将钵盂倒满凉水,咕嘟咕嘟喝下一大口。
陈二对这和尚并无好感,一心想快些打发他离去。
“不知大师前来所为何事,若是化缘,灶屋里还有些昨日刚蒸出来的馒头,这就让咱家婆娘取些来送与大师。”
“不急不急,馒头是要吃的,贫僧还有一事欲请施主解答。”
“嗝...”
和尚打了个水嗝,又趁机喝了口水。
“方才听闻施主所说,县令大人家中似遇上了难事,还请施主将其中详情告知贫僧。”
陈二刚生了闷气,不想说,但这陈二又当真是个实在人,他想这和尚敢前来询问此事,许是有什么本事,未必不能帮助大人。一念及此,他也不去想这位是否是招摇撞骗的野和尚,一五一十地将情况说了出来。
原来夫人难产离世后,江左郎心中悲痛难当,然而对天生糟老头儿的儿子,更是悲上加愁。这毕竟是与夫人的骨肉,既然决定要尽一个父亲的责任,就一定会全心全意待他。可是寻遍了全程乃至方圆几十里的有名的没名的大夫,也医不好儿子的毛病。甚至有大夫明言,此子命不过七。
江知命已六岁出头,体型与同龄的孩童无异,只是枯瘦如竹竿,皮肤粗糙暗淡,满是褶皱,白发稀疏乱如杂草。口不能言,足不能行,终日只能瘫在榻上。若当真如大夫所说,这孩子的寿命已不足八月,整个凤阳城都替大人着急,替小少爷担忧。
和尚喝了口水,闭目沉思片刻,将钵盂中剩下的凉水一饮而尽,提起树枝便转身出了门。
“馒头烦劳施主且先打包起来,贫僧晚些时候便来取。”
陈二追出门外,看着和尚高深莫测的背影,心想这或许是大寺里的高僧出来游历的。
“大师,你若是医好了小少爷的怪病,我每日也为你烧香祈福。”
“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惟闻女叹息。”
二丫时常跟小姐一同念书,学了不少学问,年幼的二丫却是最喜欢这篇《木兰诗》,已经熟记于心。这会儿陪少爷在桂树下乘凉,便坐在一旁诵给少爷听。
诵完一遍,二丫见少爷整个人软在椅子里,头侧靠在扶手上,两眼无神,不知是看向何处,口水顺着嘴角流到了耳根,形成了一滴晶莹的水珠,犹豫着要不要滴下去。二丫起身,讲少爷扶正,再一手将少爷脸上的口水擦去,随意抹在衣服上,又坐下,准备再诵一遍《木兰诗》。
少爷口不能言,手脚不能使力,基本无法交流。二丫只比少爷大了半岁,却从三岁就开始帮忙照料少爷,现如今一人就能将少爷照顾周全。别人见了少爷都是摇头叹气,她却与少爷很亲近。她请福伯在少爷床边支了张小床,随时照顾少爷。少爷不能说话,她便念书给少爷听;少爷手脚不能使力,她便在院子里抓蝴蝶给少爷看。她记得少爷也是吃娘的奶长大的,所以心里也把少爷当弟弟一般护着。
木兰还未替阿爷出征,管家福伯来吩咐二丫随他将少爷带去前厅。
二丫的爹爹会些木工活,给少爷的椅子两侧装了轮子,方便行动。二丫只比椅子高出一个头,即使椅子可以推行,也有些吃力。福伯回身接过椅子,二丫便跟在福伯的身后,感觉中福伯虽待人和蔼,却一向不喜说话。
到得前厅,老爷,小姐,陈主薄都在,还有个光头男子背对门站着,大约是个和尚。
见众人目光移向这边,光头也转过身来,扫了一眼,便又转过身,向江左郎施了一礼道:
“我佛慈悲,公子的症状当真如江施主所说,如此病魔缠身,公子小小年纪如何才能承受住这样的痛苦啊。贫僧定当全力以赴。”
“如此,有劳大师了。”
江左郎双手合十,回了一礼,心中却并未有多少希望。这许多年来名医何其多,初时多少豪言壮语,都无功而返。
和尚将钵盂置于茶几上,走到江知命身前,示意旁人闪开。福伯退到一边,二丫跑去了小姐身旁。
“小姐,这和尚是来做什么的?”
“说是叫觉梦,在街市上听闻小弟的病,来与小弟医病的。好奇怪的名字,人也奇怪,已经喝了四碗茶了,瞧这身打扮,莫不是来混吃骗喝的。哼,希望他有些真本事。”
江小婷已十岁了,除了身体变得修长,那一双大眼却是没变,只是眼中多了与其年龄不符的沉静。似乎从那一年起,她就很少与二蛋哥哥他们一同玩耍了。
“我要去读书了,你去么?”
二丫说她不去,他要留下来看着少爷,感觉中她比江小婷更符合姐姐的身份。
江小婷望了椅子上的弟弟一眼,径自转身去了。
觉梦和尚拄着树枝,绕着江知命行了一圈,将手搭在其脉门上听了一会儿,而后又是看眼白、看牙齿、瞧耳背,听心脏、肺腑,捏手指、足底,全身上下摸了个遍。
江知命任觉梦和尚摆布,只是翻了个白眼就睡去了。
和尚一番动作下来,也不言语,径自盘膝坐下,左手搭右手,拇指相抵作了个圆放在两腿之间,闭目沉思。厅中一干人等俱是安静地站在一边,不做打扰。
约莫过了一炷香时间,觉梦起身,连喝下两碗茶水,又端起第三碗茶,道:
“公子的身体本无什么毛病,问题是出在体内,这体内又非内脏的问题,而是神魂缺失。”
“什么神魂鬼魂的,满口胡言,满口胡言,我看你就是招摇撞骗的野和尚。来人啊,将这个野和尚轰出去。”
陈主薄似是有些激动,指着和尚骂道。
“休要放肆,大师乃是来为我儿医病,你这叫什么待客之道,飞槐,这里没你什么事,先忙你的事去吧。”
陈飞槐涨红了脸,瞥了眼眉头紧皱的江左郎,不敢再多说,只得离去。经过觉梦身边时,不忘冷哼一声。
“大师莫要往心里去,我这兄弟并无什么坏心。关于我儿身体情况,还烦请大师知无不言。”
“无妨无妨,出家人不打诳语,神魂一说确实与公子的病有关。”
第三碗茶也喝尽了。
“人有三魂七魄,三魂之中,一名胎光,主生命,久居人身则可使人神清气爽,益寿延年;二名爽灵,灵,乃人与天地沟通的本领,能使人阴气制阳,使人机谋万物,劳役百神,决定智慧,能力;三名幽精,主灾衰,使人好色嗜欲,溺与秽乱之中,耗损精华,神气缺少,旦夕形若尸卧。而七魄为尸狗、伏矢、雀阴、吞贼、非毒、除秽、臭肺,掌管人喜、怒、哀、惧、爱、恶、欲。”
“贫僧观公子七魄健全,问题所在乃是三魂。依公子现下的状态,我料想公子乃是三魂缺了一半——爽灵全失,胎光剩了半吊子,才维持住着脆弱的生机。而这半分胎光生机只怕也是他人导入的。”
“想必这就是公子出生时夫人难产过世的原因,而至于公子为何会缺了生魂,恕贫僧见识有限,不敢妄下定论。”
“大师,大师既已查出病症根结所在,还请大师出手救救小儿性命,江左郎不胜感激。”
江左郎上前紧紧抓住和尚的双手,终于显得激动,枯寂许多年的眼中闪出了光彩。许是为了儿子,许是为了亡妻,许是二者皆有吧。
和尚任江左郎抓住双手,也不挣脱,一脸淡定地注视着江左郎,真真是云轻风淡,超凡大师的风采。
“江施主莫急,因果轮回,贫僧既然种了此因,就要了解此果。谁说这不是佛祖安排给贫僧的造化呢。”
江左郎感觉精神一清,松开了手,躬身行了一礼。
“江左郎无意冒犯大师,还请大师见谅。”
“无妨无妨,当务之急是公子的病,贫僧曾有幸读过一本奇书,书中多述人神魂魄之事,其中也有搜魂寻魄的秘法。”
“还请江施主与我安排一间静室,切勿让人打扰。”
江左郎思忖着后院书房较为合适,便亲自在前头引路,和尚拿起钵盂与树枝跟着,二丫推着少爷跟在最后。
“嘎吱”,二丫将少爷推进书房后,退出来,带上了房门。
江左郎静静守卫在门侧,似是恢复了镇定,只是眉头依然皱着。
福伯搬来一张椅子,见老爷摆了摆手,便将椅子放在一边,也静静立在老爷身侧。
二丫坐在了门廊台阶上,双手撑着下巴,有些出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