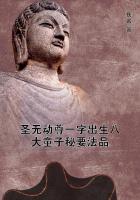权倾瞥了一眼影碟上面刻着的“盛世”两个字,瞬间了然,拿起桌子上的打火机捏在指尖把玩:“擎女士,该解释的不是你吗?你就这么关心我的私生活,把碟子都刻出来了。”
擎书瘟怒:“你说你怎么跑到1234房间去了?我明明给你定的1314房间。”
“哟,承认是你做的了?我说擎女士有你这样的吗?给自己的儿子下药。”男子嘴角扯出一个讥笑的弧度。
擎书火大,对他的态度简直恨铁不成钢:“这还不是怪你自己?马上就三十了,不找女人,不去相亲,也不结婚的?当妈的我什么能退休抱孙子啊?”
“那你也不能让我去和白婉婷那个白痴女人在一起啊?”
擎书白了他一眼,人家哪里白痴了?长相好,家世好,还对他死心塌地,不过吗……
“你到是给妈找个不白痴的呀?”她身体前倾,用手指狠狠的敲了敲桌子,贼贼一笑,话锋一转:“不过,我知道我儿子不是不举,我也就放心了。”
权倾顿时脸黑了,有哪个母亲这样说道自己儿子的。
擎书看自己成功把他惹火了,心情很好,很满意,站起来,三寸的小高跟敲在地面上蹬蹬响,拍了拍他的肩膀,在他的耳边道了句:“儿子,功夫不错。”
她得意的看着儿子的脸又阴沉了几分:“那女孩看起来气质干净清纯,很不错,我看了,人家可是第一次,你娶回家也行。”
权倾烦躁的抓了抓头发:“我不会娶的。”平常他最讨厌女人接近他身边,她们身上的脂粉味让他窒息,不过昨天那个女人身上到是没有这种庸俗的味道,自带了一股清香,逼近鼻端,似乎很诱人。
他昨天一定是被下了药的缘故,才会觉得那女人可口,要了她一次又一次。
“我要去开会了,你请便。”权倾猛的站起身来,他现在想起来,居然也没有觉得厌烦,真是见鬼了。
“你知道她是谁吗?”
权倾往外走,就当没听见。
“她就是当年那个幸运的女孩。”
权倾往外走的身子立刻顿住,蹙紧了眉头:“是可儿指定的那个,林木?”
擎书郑重的点点头,很快又换上了轻松的语气:“不过,她现在要和别人结婚了,儿子你难道要看着和自己春风一度的女人成为别人的新娘?”
权倾不语。
“听说那个男人娶她是为了报复她,难道你希望……”
“地址?”他冷冷的问。
“盛世庄园。”
权倾赶到盛世的时候,新郎新娘已经站在舞台的中央,新郎俊逸非凡,新娘美丽倾城,只是那一双本该黑亮的眼睛,此刻却如一滩黝黑的死水,平静无波。
司仪含笑问着新郎:“你愿意娶美丽的新娘,一生一世陪伴她吗?”
新娘看着这个男人,想起一首诗:若离于爱者,无忧亦无怖,她对他曾经的喜欢早就终止了,那么她就没有什么可期盼和害怕的。
她淡淡的开口:“我愿意。”
新郎也望向新娘,嘴角泛起一抹笑意,眼底却渐渐的化为淡淡的嘲讽、失望,愤怒,薄唇轻启:“我不愿意。”
新娘本来惨白的脸色此刻更加的白了,她的拳头攥起来,又松开,黝黑的眼睛泛起一股奇异的光,很快归于平静。
安臣的势力不小,请到的人很多,还有媒体记者,似乎等的就是这一刻,下面的宾客都指着她窃窃私语,嘲笑她,羞辱她,摄像头的镁光灯对着她啪啪直响,而她一如一颗静静绽放的百合花,悄无声息,无怨无艾。
似乎那些谩骂声充斥的不是她的耳膜,新郎冷笑的面孔也不是对着她。
新郎对她这样的反应很不满意,英俊的面孔升起淡淡的恼怒:“林木,你知道我为什么不愿意吗?”
林木不想知道,因为她知道他即将出口的话会让她处于更加难堪的境地,可是她无能为力,她阻止不了他。
“因为你和别的男人上过床,不是一个干净的女人。”
宾客席喧哗的声音更大了,甚至有人吹起了流氓口哨。
“这女人居然是这样的水性杨花,白长了一张清纯的脸。”
“现在的女人不能只看表象,越是清纯无辜,越是有毒。”
宾客席的一角,有一个坐着轮椅的中年女人,在这新婚喜宴上,她一身盖住脚底的白衣特别的惹眼,她很瘦,露在外面的皮肤干瘪苍老,望着台上和周围发生的一切,嘴角露出残忍的笑意,再配上凶狠的眼神,让她整个人看起来那么的恐怖。
林木感觉自己的血液上涌,浑身冰冷,对于那样令人摆布的自己,不干净的自己,她也厌恶至极,可是她别无选择,林森还在病床上等她。
新郎接着冷道:“你知道我为什么又要娶你吗?因为你说过你这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和心爱的人一起走进婚姻的殿堂,所以我给你,林木,你觉得这份礼物够吗?”
是的,她是这样说过,亏得他还记得,她的原话是:安臣,我这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嫁给你,和你一起走进婚姻的殿堂。
他给了她一个这样的机会,和他一起走进婚姻的机会,然后又在婚礼上亲手摧毁她,摧毁她的梦想,就像摧毁她一样。
原来他非要和她举行婚礼,居然是因为这个。这就是他对她最后一步的报复,最残忍的报复。
而且他把她卖给别的男人,还把,干不净的罪名按给了她?
摧毁的真彻底,恐怕从今以后她在这座城市就成了人人喊打的老鼠了吧。
林木的身体在发抖,控制不住的发抖,她咬着牙在坚持,不能倒下,不能被他打败,这是她的信念,她忍气吞声了这么久,从天堂到地狱,什么没有经历过?
她张了张嘴,终于挤出一抹笑,她黑亮的眼睛望着他,就如黑夜里的一束强烈的光线,权倾在下面看着她,突然被那一道光线刺到,心脏没来由的收缩一下,他感觉到了心疼。
他大步走过去,强势的拨开人群。
她在说,声音带着一丝颤抖的平静和静立的凄楚:“安臣,你是不是弄错了,那个心愿只是我五年前的,现在早已经变了,我现在的心愿是:你、不、得、好、死!你能满足我这个愿望吗?”
“说得好。”权倾大声喝彩,不由得鼓起掌来,把前面挡路的白色椅子一脚一个的踹开,向着礼台上的新郎新娘走去。
这个女人没让他失望,并不是任人摆布的木偶,一如既往的毒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