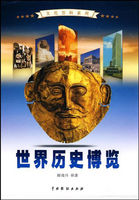建平五年的初春似乎格外的寒冷。已过了立春的节气,然而大地并没有冰雪消融,也没有春的萌动和生机盎然。冰冷的气氛仍然笼罩着邺城。
石勒的身体每况愈下,短短两三年的功夫,他似乎已经变成了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他形容枯槁,须发皆白,已经再没有了往日的神采,已经如同即将熬到油尽灯枯。
石勒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了,但他仍然牵挂和操心着大赵国,这个他一手建立的庞大帝国。
这几年大赵国东征西讨,已经几乎平灭了所有环绕在大赵国周围的各个大小胡人部族。
可是,让石勒真正担心的并不是各个胡人部族,尽管他们貌似强大,但他们和自己的羯人部族一样,来自草原,来自荒漠。他们并不是这片土地的真正主人。游牧的性格让他们不会真正为了这片土地浴血奋战,不会即使抛却一切也要世世代代战斗下去。
他真正担心的还是汉人,是那支无论如何都无法剿灭的乞活军。他们从没有放弃,即使在他们弱小的时候。因为他们是这片土地的主人,他们会永远战斗下去。而且,更可怕的是乞活军在李农的率领下已经不断发展壮大,他们已经逐渐威胁到了大赵国的统治。
团结和组织起来的汉人的力量是无与伦比的,是可怕。石勒感到一阵阵的寒意。
皇宫的内殿,石勒已经无比的虚弱,但他仍然将石渊、石宏、程暇、孙伏都等心腹招至书房。他们要仔细地商讨征伐乞活军。与往日不同的是,这一次没有喊上石闵。
石勒不断地剧烈咳嗽,几乎很难完整地说完一句话。洁白的手帕上不时沾染上咳出的血丝。
“皇上,不能再等了,乞活军不断坐大,再耽搁下去必成心腹大患。”程暇沉沉说道。
众人没有说话。
石勒微微点着头,他看向石渊。
石渊沉思片刻,有些犹豫地说:“胡汉共处的怀柔策略一直是我大赵国立国的基本方略之一,现在大举征伐是否合乎事宜。”
这些年几乎都是石渊代石勒亲征挂帅,他现在是石勒最为依仗的肱股,他的话有着极重的份量。众人沉默着。
石勒喘喘地说道:“不一样了,或许终有一天我们要面对面一决生死。”
石勒眼睛一亮,闪过一丝往日的神采,似乎又重回那血战沙场,号令天下的英雄时刻。然而,只是一闪而过而已。
“父皇言之有理,”石宏说道,“胡汉的相互忍让或许只是暂时的,冲突最终是无法避免的。这些年我们已经平定了各胡族势力,现在帝国疆域空前广大,人心归附,帝国的实力也今非昔比。现在是对付乞活军最好的时机。”
“是的,”孙伏都朗声说道,“不过这几年乞活军趁我们无暇顾及,不断扩大势力,抢夺地盘。而且在汉人中威望不断提高,现在已经不容小觑。现在不加征伐,恐怕以后会越来越难。”
石勒微闭着双目,静静地听着。
“我们大赵国不会永远居于北地,日后还要跨过大江,南征晋室,一统天下。”
石勒吃力而沉重地说着,眼中再次闪过一丝年轻时的神采,语气有说不出的威严。
石渊点着头。
“皇兄言之有理,如要行动,可是宜早不宜迟。”
石勒欣慰地点了点头。
“又要烦劳六弟挂帅出征了。”
石渊笑了笑,“皇兄言重了。”
程暇说道:“六王爷挂帅自然是好,单将军自然也要一同随行。”
孙伏都点了点头。
石宏说道:“我也去。”
石勒点了点头。
程暇欲言又止,“只是四殿下?”
石勒陷入了沉思。
程暇接着说道:“征伐乞活军非比寻常,不比胡族各部。汉人用兵灵活狡诈,加之李浓调度有方,这可说是我们最强劲的对手,千万不可掉以轻心。若论文武才能,四殿下随军再好不过。只是他这汉人身份,确实为难啊。”
“是否可调麻秋等人随军出征。”石宏说道。
“不可,”石渊有些忧心地说道,“麻秋属石琥一党,平阳大战险酿大祸。他若随军,是好是坏实在难料。”
“况且,”石渊有些犹豫地说,“据说石琥近来常有异动,不断加紧活动,联络属下各部,似乎有冒险犯事的迹象。”
说完,石渊看着石勒。
石勒痛苦地闭上了眼睛,这是他的一块心病,可他却没有办法化解。
半晌,石勒粗喘着缓缓说道:“还是带上闵儿吧。”
众人点了点头。
石勒冲大家艰难地摆了摆手,说道:“你们都走吧,六弟你稍待片刻。”
时辰到了,内侍走了进来,端来一碗刚煎熬好的粘稠油黑的汤药。汤剂散发着浓烈的药味,说不上好不好,只是看着就是十分的名贵。
石渊接过碗,亲自帮着石勒服下。
石勒喝完后,剧烈的咳嗽稍稍平缓了些。
“六弟,闵儿大了,而且本领冠绝群雄,这可是猛虎出笼啊。”石勒忧心忡忡地说道。
“皇兄,闵儿智虑忠纯,您尽可以放心。”石渊安慰道。
石勒点了点头。
“这个我放心,只是,他这汉人身份,随你征讨乞活军,我怕他难以管束,更怕节外生枝啊。”
石渊无言以对。
石勒若有所思地说道:“有些事终将面对,有些选择终将作出,也是难为闵儿了。”
“六弟,你还记得过去我们羯人接纳汉人降臣所要经过的仪式吗。”
石渊心中大惊。
“为了万无一失,为了大赵的将来,也为了闵儿,六弟,你,按照这个再来一次吧。”石勒艰难地说着,又剧烈咳了起来。
石渊失神地坐着,但最终还是艰难地点了点头。
骊音依然在细心地帮助石闵整理着行装。几天前圣令已经传到了府上,石闵将随石渊出征中山荒,讨伐乞活军。骊音已经习惯了石闵的远行。只是每次他要走的时候,她仍然是那么的不舍和担忧,期盼着他早日平安回来。
过去的每次出征,石闵总是略带着兴奋。尽管战场上总有意想不到的事,总有他不愿见到的场面,但毕竟是为大赵国出征,而且是征战其他胡族,石闵没有一丝的犹豫和为难。每次临出发,他都会亲自细细整理自己的盔甲战袍,细细擦拭他的碧血银枪。
只是这一次,他再没了心情。当接到圣令要随军讨伐乞活军时,他感受如晴天霹雳一般。尽管他早有思想准备,早就想到这一天终会到来,但是当这一天真的到来时,他还是那样的震惊和无奈。他感受到了虚弱,感觉人仿佛被整个掏空了。
自从面见李浓以后,石闵整个人都变了,他无比的沉默。他已经想不起来那天是怎么回来的,只觉得昏昏噩噩如五雷轰顶一般落魄而回。当李农要他脱离大赵回到乞活军时,他不知如何回答。他从小在这里长大,这里有着他全部的童年记忆。他已经接受了这里的一切,这里有他的至爱亲人。
他不知道李浓的话到底是不是真的,他不知道自己的身世到底是怎样的。可是,直觉告诉他李浓是对的。为什么他要遭受这种命运,为什么他是冉良的儿子,为什么他就不能做一个纯粹的汉人或者胡人,为什么他要承受这两种不同的身份和命运的纠缠。
遥远而疑惑的身世,难以割舍的现在。
他到底该怎么办。他感到一种深深的无奈和悲凉。而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始终沉默着。
骊音的心如刀绞一般。女孩的心总是那么敏感,何况聪慧灵巧如骊音。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石闵也没有对她说,但她明显地感到自从石闵那次出门回来后,整个人如同丢了魂魄一样。她也曾试图询问,可是石闵总是沉默地摇摇头,一人失神而无奈地望着远方。
或许很多事石闵也无法向她求证吧,或许很多事真的只能自己面对吧。
骊音仍在细细地收拾着,两人都沉默不语。石闵半躺在床上,双手枕在头后,失神地望着屋顶。盔甲战袍散在一旁,碧血银枪斜靠在架子上。石闵已经懒得去拾掇了,还是骊音将他们重新理好。
这可是头一回,骊音深深地感到石闵这一次出征非比寻常,她总有一种预感,石闵这一次会遭遇人生的重大变故。只是她无能为力。
“少主,早点歇息吧,明天大早就要出发了。”骊音低头轻声说着,准备退出去。
既然他不愿意多说,自己又何必勉强呢。
石闵没有讲话。
“少主,我走你,你早点歇息吧,东西都已收拾好了。”
骊音又轻声说了一遍。
石闵仍然失神地望着屋顶,似乎根本没有听见。
骊音走也不是,留也不是,有点左右为难。
他看看石闵没有动静,轻轻退到门口。门“吱”地一声轻轻响动了一下。
“骊音”石闵轻轻唤了一声。
骊音心潮澎湃,她回过身,又轻轻将门关上,来到石闵窗前。
“少主。”
“骊音,你坐下。”
石闵突然拉住了骊音的手,却没有说话。
“少主,是不是有什么心事。过去你有心事不都会对我说的吗。”骊音温柔的声音如从醉梦中飘来。
“是啊,可是很多事只能自己去面对。”
“骊音,我是不是变了很多。”
骊音轻轻点了点头。
“骊音,我了解到自己的一点身世,可是我无法确信。这些遥远而模糊的过去,我没有任何记忆。可是不管怎样,总要有一个决断。”
“骊音,你有没有想过离开这个地方。”
骊音心中大惊,转而心中突然涌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和释然。离开这个地方,她曾经渺茫地幻想过,却从没有想过如何去实现,毕竟她只是一个柔弱的女孩,何况这里有她深爱的人。
“少主,不管你到哪里,我都愿跟随你。”骊音轻轻低着头,烛光将她的脸映得通红通红。
“我是汉人,却是羯人将我养大。过去的身世,我并没有最终知道真假,或许以后也很难求证了。我始终在这两种身份中摇摆了,你说得对,我是汉人,血脉的渊源是无法割断的。但毕竟羯人对我也有恩,我想这可能是我为羯人打的最后一仗了,算是了却这段夙缘。从此以后,我只想两不相帮,安静地做回自己。”
骊音脸上渐渐露出欢喜的神色,她将头轻轻靠在石闵的胸口。石闵轻轻抚摸着她的头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