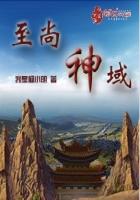万朝三百零一年三月,高祖殁,太子即位,号贤宗。同年七月许,贤宗帝身患恶疾,于八月甍于硕和行宫,时年三十四。
其后三月间,高祖二子皓朝、三子皓阳先后遇刺身亡,四皇子皓冉于时休妻,迎娶两朝丞相南应天之女为妃,得当朝第一世家南氏拥戴,力排众议,于腊月初请天旨祭太祖,登基即位,尊号万延宗,改年号嘉文。
短短九月间,万家天下,先后二次更年号。江山易主,不过转眼之间。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皇后南氏,嗜奢侈,又好妒,积与上忤,恃宠而骄,跋扈骄纵,横行霸道,三年无子,罪犯七出,尊我朝太祖遗训,故废之——钦此。”
宦臣高亢尖细的嗓音空空地回响在偌大的宫闱中,殿中的女子一身墨绿华服,双膝跪在冰凉的地上,微微垂着头,教人看不清她面上的神情。
“皇后娘娘,”宦臣的脸上挂着一丝讽刺的笑意,一声“皇后”亦是喊得实打实的讥诮,他一扬手中的拂子,随后又将手中捧着的明黄绫锦递将给她,道,“难得皇上宅心仁厚,你接旨谢恩吧。”
闻言,女子却并未伸手接旨,而是沉默了半晌,顷刻后,却又像是听了天大的笑话一般,唇角微扬,竟是低低地笑出了声。
“接旨也便算了,还要本宫谢恩?”她抬起右手,细细地端详了一番那鎏金嵌玉的护甲,一双桃花杏眼微挑,眉间一朵盛放的红莲妖冶无双,她望向那宦臣,“不应该啊,江路德,你跟着你家那位愈发剔透的皇帝主子,却怎地愈变愈蠢了?”
“你……”
她面上一派地不屑,只缓缓从地上站起身子,回身一把拉开了身后沉重的宫门,几道阳光倾泻而入,映在那张艳丽绝伦的容颜上。
唇角携着丝坦然无谓的笑,她提步迈过高高的门槛,走出了宫门。
凤仪宫?她冷笑着抬起右手,举过头顶,一把扯下了绾发的凤冠,随手扔了出去,一头如瀑青丝便披散而下。
“你、你!南泱!咱家奉劝你莫要太嚣张!”江路德在她身后扯着尖细的嗓门儿嚎道,“皇上今儿早上便已下了旨,将你一家二百余口流放荒城,你还当自己是丞相之女当朝国母么!”
“随他的便吧。”她淡淡地回眸,睨了睨身后的那人,几缕青丝在秋风中飞舞,莞尔道,
“江公公,你的主子想今日,想了这么多年,如今终于如愿,你应该替他高兴才是。”
“南泱!你自封后以来便勾结御医院毒害皇上,垂帘执政,独揽朝权,加害皇嗣,论罪当诛九族!皇上宅心仁厚,留你性命,你竟还口出狂言!”
“不然呢?”她的声音极轻,道,“他这般作为,莫不是,还要本宫对他感恩戴德?”
“你!”
“宅心仁厚……”
她低声地呢喃了一句,不禁又是一声冷哼,复又回过身,迎着微凉的风,头也不回地朝着远离凤仪宫的方向缓缓走了过去。
万皓冉是个什么样的人,这世间,再没有人比她更清楚。
嘉文三年十月,南后被废,丞相革职,也正是在南家举家流放的当晚,南府走水,大火整整烧了三天三夜,至此,在大万王朝风光了百年的南氏家族,顷刻间化为残瓦废墟。
北国境内的陌阳城,迎来了初冬的第一场雪。
夜幕微垂,星月高悬。
夜色之中,一抹微微佝偻的人影手中提着一个灯笼,一双玄色的短靴缓缓跟在那人影后头,踏过铺地的白雪,朝着皇宫的西方走了过去。
来人一袭玄色的衣衫,罩着玄色斗篷,掩去大半容颜,一双露出的唇生得极薄,微微开合,便发出了一道清冷微寒的声线,“去月陨冷宫。”
前方引路的人面上急速地掠过一丝惊异,却仍是俯首应了声“是”。
“去外先候着。”
“是。”
“吱嘎”一声,陈旧破败的宫门被缓缓地推开,落下了些许灰尘,提灯的宦臣眼瞧着那人步入了那扇门,方才又缓缓地将门合了起来。
一双骨节分明的手微微抬起,解下了挡雪的斗篷,现出一张轮廓锋利的面容。
冷冽的双眸微动,他的眼中映入了一抹墨绿的身影,只见那人端端地立在漫天的飞雪里头,冶艳的面上挂着一丝浅笑,朝他甚亲切地招了招手,便像是在那儿等了许久一般。
“就晓得你一定会来,”她招呼了一声,含笑道,“我在此处等了你数月,还以为你真将我忘在这冷宫中了。”
“……”他如玉般的面容上没得一丝表情,只漠然地上前几步,方才薄唇微勾牵起一抹笑,沉声道,“怎么会呢?”
“也是,”她仿若了然地颔了颔首,双眸仍是带着笑意望着他,“你我之间还没个了断,你又岂会不来。”
话音甫落间,一道剑影便如闪电般朝他掠了过去,他面上没得半分的讶然,身躯在瞬间便朝一旁闪过,不费吹灰之力地躲过了那致命的一袭。
缠斗只是片刻的事,她一个回身间,终究还是没能躲过那毫不留情的一掌,连人带剑飞出了丈远,手中的长剑落地,发出一声脆响,她只觉喉头一阵腥甜,便呕出了一口血水。
“困兽之斗——”他唇畔携着一丝笑,伸手拂了拂沾上衣角的灰尘,居高临下地望着她,道,“何必呢?”
“呵呵呵……”她低低地笑出了声,望着他,刹那间双眸中的狠戾之色尽显,“万皓冉,便是今日你杀了我又如何?你这辈子也休要忘记,你的这锦绣天下,是我南家给的!”
“南泱啊南泱,”他微微摇头,面上浮上了一丝叹惋,又道,“你聪明了一辈子,可知道,你这一生,输在何处么?”
“……”她一声冷笑,又咳出了一口血水,鲜红的血缓缓地浸入雪地,在月光下泛起一丝幽光。
“论野心,你不输朕;论才智,你不输朕;文韬武略,计谋手段,心狠手辣,你样样不逊于朕,”他朝她走近了几步,缓缓地俯下身子,望着她,道,“你唯一输的,便是生得了一副女儿身。”
“……”她垂眸,一阵沉吟,忽而却又笑了,低声道,“不,我唯一输的,是嫁给了你。”
“哦?”他挑眉,似是起了极大的兴致。
“先帝膝下四子,太子忠孝,二皇子英勇,三皇子仁善,唯独那四皇子最不成器,是个生得颇好的草包……”她垂着眸,蓦地便忆起了当初父亲的一番话,顿觉可笑得厉害,不禁放声笑了起来,“好一个生得颇好的草包,难为阿冉你心机城府如此之深,竟是连我也没将你看透……”
“过誉了,”他微微一笑,又道,“你同你父亲献计,决意佐朕登基,无非便是想朕遂了你的心意做个傀儡皇帝,皇后每日端来的芙蓉汤,若是朕真的每日服用,如今,恐怕你南泱,便真是一代女尊,这天下,便真该姓南了。”
“只可惜……”她眉头深锁,眉心的红莲染血一般地诡艳,只觉呼吸益发地困难,“我仍是、仍是棋差一招……”
“南泱,那日江路德问朕,为何不治你的死罪,诛你的九族,”他微顿,清寒的双眸淡淡地略过她,道,“你猜,朕是如何回答的?”
“……”
“死,并不是最痛苦的。要你南家后人,眼睁睁看着家族百年基业付之一炬,从天堂跌入地狱的痛苦,才是真正的折磨。”他俯下身,伸手抚上她的容颜,轻声道。
她最后呕出了一口血水,终是缓缓合上了双眸。
“三年来,你垂帘执政,亦将朕的江山治理得甚好,是以……”他徐徐直起身子,俯视着她恬静如昔的容颜,笑道,“死,也算是朕对你的报答。”
夜间的风夹杂着丝丝雪花,冰凉得刺骨,江路德裹紧了身上的厚实棉衣,朝着那扇紧闭的宫门张望着。
忽而,那扇紧闭着的宫门开了,从里先步出了一抹玄色的挺拔身影,几近与夜色融为一体。
“皇上。”江路德上前几步,弓着身子恭敬道。
“差两个信得过的太监,将她的尸体连夜运出宫。”他淡淡开口,左手抚了抚拇指上的白玉扳指,随后便旋过了身子朝前走去。
“……”江路德听得一愣,只觉心头惊了惊,却仍是快步跟了上去,半晌方才又小心翼翼地问道,“回皇上,南泱罪犯滔天,如今她‘畏罪自尽’,尸身却是要送往何处?”
“……”闻言,他的唇角微扬,勾起一丝笑,一双冷冽得冰凉的眸子淡淡地望了身旁的宦臣一眼,缓声道,“一个畏罪自尽的废后,该如何处置,还要朕教你么?”
他话音甫一落地,江路德的额角便泌出了一层细密的汗珠,讪笑道,“奴才一时糊涂,奴才明白了,明白了……那御医院的那三位御医……”
“唔……”他脚下的步子沉稳从容,微微蹙眉,半晌才缓缓吐出了三个极轻的字眼,“凌迟吧。”
“是。”
“啧啧,真是风水轮流转啊,当初南相官拜两朝,南后垂帘执政,那是何等的风光……”
“谁能想到呢,如今南家没落,南后被废畏罪自尽,身后只得这一口破棺材,还要被弃尸荒野,真真是造化弄人哟。”
“哎,”说话的小太监生着一张圆脸,叹了口气,将抬棺材的粗滚子往肩膀里头又挪了挪,朝另一个小太监道,“说来也古怪得很,前些年,皇上的身子分明是一日不如一日,上个月林御医还吩咐要准备身后事,可谁知……”
“这些事哪里是你我该过问的!在这皇宫里头,晓得的越少越好——”另一个尖脸小太监嗔道,“都二更天了,你我手脚麻利些,天亮前还得赶回宫呢。”
“嗯。”
“咚——”
蓦地,一阵诡异的声响忽作,四下里寂静之极,更教这声响益发地瘆人。
“……”走在后头抬棺材的圆脸小太监心头“咯噔”一声,他抹了抹额角的汗水,朝四方望了望,吞了口口水,声音发颤着道,“你、你听见了么?”
“啥?”尖脸小太监回过头,面上带着一丝不耐,“我说,你就莫疑神疑鬼了,这天底下哪儿来的……”
“咚咚咚——”
这一回,那声响更为清晰了些,亦更为骇人,方才还一脸不耐烦的小太监此时也是吓得面色发青,背上的衣衫被冷汗尽数浸湿,经夹着雪的风一吹,不禁冷得一个哆嗦。
二人相视一眼,立时便将抬着的棺材扔到了地上。
“……难道、难道是……”圆脸小太监浑身微微地抖着,颤颤巍巍地伸出手,指了指那口破棺。
“莫、莫要自己吓自己……”
“咚咚咚——”“吱嘎、吱嘎——”
“啊——诈尸啊!”
两声凄厉的尖叫响起,两人吓得面色铁青,跌跌撞撞地朝着来的方向死命地跑了回去。
棺材的盖子微微动了动,终于是朝着一旁被掀了开,落到了地上,发出一声闷响。
一只白皙纤长的手,缓缓地伸出,扶上了棺材的沿,紧接着,里头的人便挣扎着缓缓坐了起了身子。
心口处不住地传来一阵阵莫名的钝痛,她抬起手,捂住心口,徐徐睁开了眼。
“……”尚有一丝迷离的狭长双眼朝四下里打望了一番,她只觉一阵莫名,便眨了眨眼,又朝四下里望了望,这一回,她算是看得请了,看得忒清了。
“这是……”她怔了怔,顿觉整个人瞬间都不好了——她重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