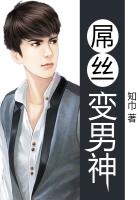落日熔金暮云合璧,血红的夕阳即将隐没在地平线下。五月中旬天气已经渐渐炎热,白天精神萎靡的狗狗们傍晚时分欢扑跳跃,兴奋不已。一只白色小狗原地转圈,追逐着自己的尾巴,脖上系的铃铛叮叮脆响。
已经进了小区了,白冉霞手搭着方向盘,头部跟着音乐的节奏轻轻摇摆。忽然感觉撞上了什么东西,白冉霞激灵回神出了一身冷汗,她急忙关了音乐把车停在路边,手忙脚乱又撞倒了一只垃圾桶。
她深深吸气下车查看,原来只是一只普通的小狗,身下一滩血迹,看来是活不了了,她长舒了一口气。又像是想起什么,她围着车转了一圈,眉头渐渐拧成一个疙瘩。另外几只狗停止嬉闹,在小白狗身旁嗅个不停,发出阵阵哀声,白冉霞听在耳中心烦意乱,仿佛被扔在了锅里温火慢炖。她厌恶地瞥了一眼,开车离开了。一只狗而已,她无所谓地想着。
白冉霞家住三楼,五层旧楼没有电梯,楼道里是触摸灯,连续摸了几下才慢悠悠地亮了起来,一闪一闪仿佛恐怖片的桥段。不知为何白冉霞脑子里满是刚才撞死的那只狗,张着扭曲变形的嘴,鲜血在身下流淌凝固。
空气里似乎弥漫着若隐若无的血腥味,随着呼吸游进鼻孔。她四下打量一番满是惑色,使劲抽动几下鼻子,晚饭时的菜香和楼道里的古怪潮味一起钻进鼻孔,唯独少了刚才的气味。难道是因为刚才撞到狗造成得错觉么,她没有在意。
终于爬到三楼,她伸了伸发酸的腿,掏出钥匙打开房门。扑面而来一股浓重的烟酒味,她打开灯无所谓地看了一眼,一脚踢开酒瓶,随手把包扔在桌上,一低身靠在了沙发上。
昏昏沉沉中做了一个梦,仿佛那只被撞死的小狗眼睛泛着红光,正死死地盯着她,她有些害怕向后退了一步。狗嘴里猛地发出一阵低吼,白毛须臾变得鲜红,脖上的铃铛发出急促的响声,她啊的一声坐了起来。
一只白色的东西映在她的眼中,四条腿一根尾巴,白色的皮毛上鲜血混着灰尘已经凝固,嘴巴扭曲暴张,眼睛鼓出眼眶没有半分生机,分明是她撞死的那只狗。
白冉霞惊愕失色,张着嘴说不出话来,耳边有铃铛声叮叮脆响,她打个冷颤,疑在梦中。
张正宁有些疑惑地推了白冉霞一把,不想被其刺耳的尖叫吓了一跳。“这只狗是你捡回来的?”白冉霞指着狗,怒不可遏地瞪着张正宁。
“怎,怎么了,被车轧死了,我看怪可惜就捡回来了。”张正宁捏着铃铛,有些结巴地说道。白冉霞平复一下心情,满脸讥笑:“你不是要吃了它吧?”张正宁理所当然地点点头。
白冉霞盯着握刀剥皮的张正宁,张嘴吐了个烟圈。烧水洗涮,油锅爆香,狗肉翻炒成一盘美味。那盘菜,叫做意外险……张正宁回头看了一眼白冉霞,迎上她的目光不由打了个冷颤,他尴尬一笑,把做好的狗肉端上桌子。白冉霞尝了几口,如果没有走错路的话,会是一个不错的厨师。
“都准备好了吧?”
“准备好了,一个小时以后。”张正宁吃着狗肉,含糊不清地回答着。
月黑风高夜,杀人放火时。张正宁没有胆子杀人,自然也不会放火。晚上九点十分流光溢彩,他压低帽沿在金碧辉煌的酒店附近踱步,此行只有一个目的,碰瓷。
“喝酒开车的人,可最怕交警了。”在一次尾随假装残疾行乞的骗子,抢钱未遂反被扁得鼻塌唇青后,扣着指甲的白冉霞漫不经心的一句话,如电光般在张正宁心中闪过。
张正宁啐了一下口水,恨恨地瞥一眼酒店,心中愤愤不平。他暗想你们美酒佳肴吃得痛快,老子却在这喝西北风,一会定要狠狠地宰一笔。这般胡思乱想,表情越发狰狞了。
不知道哪里飘来一股淡淡的臭味,熏得他有些烦躁,连续换了几个地方都摆脱不掉。酒店的客人走了一批又一批,始终没有碰瓷的机会,张正宁也有些着急了。正在这时,忽然看见不远处有人打了一个奇怪的手势,张正宁笑了。
看,勤劳的人总会有收获,只要努力就会心想事成。他哼着歌跟在一个红胖子身后,目送他上车,车灯亮了,发动机响了,张正宁疾走几步扑到车上,然后翻倒在地。
先前打手势的人是他收的小弟,两人是碰瓷时候认识的。都说同行是冤家,不过张正宁和此人却是臭味相投,相见恨晚,颇有惺惺相惜之感。最让张正宁惊奇的是,这个叫赖五的年轻人居然也抢过钱,还被假装残疾的行乞者揍得鼻青脸肿,张正宁当即认赖五为小弟,两人立志要在碰瓷界混出一片天地。
两人分工明确,赖五锁定目标,张正宁上前碰瓷,钱款四六开。遇到棘手的猎物两人就一起动手,也不至于被打成猪头,那个扁过他们的假乞丐前两天就被狠狠修理了一顿。
?红胖子有些惊恐地分析眼前的情景:一个不知道哪里来的家伙自己撞了过来,身下红呼呼一大片。自己刚刚下车查看,结果就被另一人塞进车里,倒地的人也迅速起身钻了进来。
番茄酱的气味里似乎夹杂着些许腐烂的臭味,劈头盖脸地钻进鼻孔。红胖子有些发懵,打了个酒嗝,试探地问了一句:“碰瓷?”赖五不耐烦地瞪了他一眼。红胖子心领神会,翻遍了裤兜、钱包,自觉地把所有财物都交了出来。
赖五抱着肩膀满脸痞相,张正宁与他相视一笑,如此为民除害的壮举,收一点辛苦费岂不是理所应当?
张正宁抓起钱塞进口袋,忽然又闻到那股奇怪的味道,像是有死掉的动物腐烂生蛆,令人作呕的气味在狭小的车内肆无忌惮地弥漫,熏得三人一阵窒息。张正宁惊骇地发现,那气味似乎是从自己嘴里散发出来的,耳边隐隐有铃铛声音清脆悦耳,似乎在哪里听过。
赖五竖眼横眉,重重地拍了红胖子的肩膀一下,怒道:“你车上什么东西这么臭?”说着狠狠推了他一把,狐疑地四下打量着。
张正宁心中一惊,急忙也装作疑惑的样子回头张望,一个黑色的布袋跃入眼中。他一把扯了出来,随手拉开了拉锁,带着一道道黑色条纹的棕黄色毛皮映呈眼前,旁边有还有几根白白的东西。
赖五一声惊呼,这一瞬间张正宁只感觉到天旋地转,那是窒息的感觉。
张正宁这个人年轻的时候打小孩骂哑巴,白天游手好闲晚上拦路抢劫,偷狗贩犬无恶不做,十足的地痞流氓。浑浑噩噩混到而立之年,正欲改过自新不想遇到白冉霞,又被她推进万丈深渊,只是他从来没有后悔过,此刻更是哈哈大笑了起来。从未这么清晰地感受到过心跳,仿佛血液要奔流出体外。
张正宁觉得他比发现新大陆的哥伦布还兴奋,他笑得涨红了脸,因为他手里拿的是,虎皮和象牙啊!
张正宁笑得很狰狞,眼睛泛着红光,红胖子和他对视一眼,不由打了个冷颤,心里一发慌瞬间变成了白胖子。空气凝固了几分钟,张正宁似乎下定了什么决心,他慢慢收敛了笑容。把刚才白胖子交出的钱掏了出来,一把拍到座位上,凶狠吼道:“买你这个包,没问题吧?”
白胖子擦了一把汗,连忙叠头。赖五有些迟疑的目光落在张正宁的脸上,张正宁斜睨了白胖子一眼,面露不屑之色。富贵险中求,赖五把心一横,和张正宁迅速消失在夜色中。
遇弱则强,这就叫黑吃黑。
白胖子怔怔地看着二人消失的方向,露出古怪的神情。良久后,他的面色恢复了正常,头脑很清醒,手还有些抖不过没关系,他很相信自己的驾驶技术。回家睡觉,他这么想着。
只是这个晚上注定不会平静,因为他,撞人了。不甘、懊悔、恐惧以及愤怒化成一道凄厉的嚎叫响彻夜空。
白冉霞今晚有些心神不定,张正宁顶风作案不知道会不会有事,她有些懊恼地揪了揪头发。早就该买一份大额保险,然后只要在合适的时机制造一场“意外”就够了。像张正宁这样众叛亲离的人,出了事也不会有亲友追查,何况她对此颇为自信,因为她的前夫就是死于一场“意外”。
每当夜深人静想到前夫时,白冉霞总会有一丝莫名的忐忑。或许做了亏心事都会寝食难安,她时常会觉得有一双看不见的眼睛盯着她,然后会在最不经意的时刻,给自己致命一击。
最近被盯着的感觉越来越频繁了,白冉霞晃着头颅,努力把这种念头抛出脑外。被贪婪吞噬良知的人永远不会愧疚,她低头盘算着,脸上露出既嘲讽又歹毒的神色,张正宁,杀了你也算是为民除害呢!灯光下白冉霞的影子,扭曲如饕餮。
算算时间张正宁也应该回来了,白冉霞走到窗前探头张望。目光所及处,稀稀落落还有几扇窗户透着光亮,路灯下拥挤停靠的汽车如棺材一般排列在寂静无声的小区,白冉霞正要转身,忽然愣住了。
不知何时出现的狗群蹲坐在地,仰头和她对视,一只两只三只……正中间的是只白色小狗,脖子上似乎挂着什么东西,依稀可见是一个铃铛。白冉霞像是想起什么,盯着那只铃铛,骤然睁大了眼睛。梦中凶猛厉狗脖上挂的铃铛和张正宁手里那只不断重叠,合二为一。
只是在那之前自己根本没瞧见过,那只铃铛又怎么会出现在梦中?
白冉霞惊惧地看着那条狗,惊觉像极了她撞死得那只。突然,一股寒意袭遍全身,楼下凭空出现一道身影,伸手抱起了那条狗。
被盯住的感觉前所未有得强烈,剧烈的恐惧如翻滚的骏波虎浪,白冉霞踉跄摇晃,惊骇失声。她不可置信地向后退了几步,忽然又鼓足勇气,惊疑不定地靠近窗口,凝目向楼下望去。
真的是他,白冉霞脸色瞬间惨白,脑中嗡嗡轰响。楼下的那道身影张开嘴像是仰头大笑,身体渐渐变淡,群狗哄然奔散。
白冉霞如遭重击,跌坐在地上彷徨失措,无数个纷纭杂沓的念头在脑中炸裂,最终化成三个字循环往复:见鬼了。
她跌跌撞撞地洗了一把脸,迈着发软的脚步坐到沙发上,又起身接了一杯水。喝了一口有些烫,她股战而栗地捧着水杯刚要坐下,忽然听见咚咚咚的脚步声由远而近,似乎停在了门口。
白冉霞哆哆嗦嗦站到门前,对着猫眼看了过去。满脸鲜血的男子嘴唇微动,看口型似是在说别来无恙。
房门剧烈颤抖起来,似是有什么穷凶极恶的东西即将闯入,是他,他来了!
白冉霞一声尖叫,倒退数步,扬手把水杯扔了出去,张正宁刚打开门还来不及反应,就被飞过来的水杯砸个正着,热水泼到脸上,烫得他哎呀大叫。
夜里十一点,夫妻二人鬼哭神嚎,声振屋瓦,对面的邻居忍无可忍,睡眼惺忪地推门怒吼:“你们有病啊?”两人的声音戛然而止,张正宁快步闪进屋内。打着哈欠的邻居被鼓起风中的恶臭熏得一阵干呕,他低声咒骂连忙关门,细微的脚步声和隐约的铃铛声响消失在黑暗深处。
“你干什么呢?”张正宁擦了一把脸,面露愠色。白冉霞双眼右瞥,随口敷衍:“没事吧,我以为有贼呢。”顿了一秒,白冉霞斟酌发问:“你回来的时候,有没有看到什么奇怪的人?”张正宁一愣,惊讶不已:“真的来贼了?”
白冉霞无力地摆摆手,突然闻到一阵熏天臭气,她捂着嘴扑到卫生间呕吐一阵,直起腰伸手擦了一下眼角,嘴里也有一股奇怪的味道,就像是吞咽了一块腐肉。她回头看了张正宁一眼,仿佛看见他对着狗肉大块朵颐,白冉霞胃里一阵翻滚,一张嘴又吐了起来。
张正宁嘴角抽搐堪堪要吐,手一紧攥到了带回来的布袋,一时吐意全无。他拉开拉锁,抖出一大一小两张虎皮顾盼自雄,白冉霞猛然一僵,忽地眯起了双眼。
已经过了最佳睡眠时间,两人各怀鬼胎无心入睡。张正宁神情亢奋地来回踱步,被烫得还有些发红的脸上挂着情不自禁的喜意,抬头纹堆得老高,一眼看去直如厉鬼。
白冉霞靠在沙发上假寐,心头风回电激,都说计划没有变化快,看来果真如此。十几分钟之前自己还谋划如何害死张正宁,结果前夫的鬼影出现彻底打消了她的念头,她可不想被两只鬼纠缠。正想就这样一拍两散,不想张正宁居然带回了虎皮和象牙,这可始料未及了。
白冉霞心头狂喜,脸上却不动声色,天一破晓就找机会偷偷带走虎皮,逃得越远越好,从此东南雀飞各求富贵,张正宁,你就自求多福吧。
白冉霞打定主意,不觉露出冷笑,回过神来又闻到熏人的腐臭,随着张正宁走来走去,似乎有若隐若无的铃铛声忽远忽近。她屏住呼吸心脏狂跳,窗外冰冷的目光盯得她寒毛卓竖,血淋淋的人脸与她隔窗相望。她双手互握掌心湿潮,快一点天亮吧。
黑夜逐渐被光明驱散,被盯梢的感觉在天边泛白的时候如汤沃雪,迅速消失无踪。白冉霞咂咂嘴,似乎没什么异味,看来是吐净了,她长舒一口气。
张正宁想必是吃得多,不吐则已,一吐起来便惊天动地,一直折腾到早上七点,终于不动了。他硕大的将军肚如被猛兽啃食,一夜之间竟然消失不见。
白冉霞匆匆收拾了几件衣服,拎起装着两张虎皮的布袋刚要离开,忽然,张正宁放在桌上的手机嗡嗡振动起来,白冉霞一个激灵,忙把电池扣出扔在一旁,屏幕上赖五两字消失不见。
蹑手蹑脚地走到门口,白冉霞轻轻拧开房门,闪身出去再慢慢关上,以从没有过的速度冲到楼下,把包摔到副驾驶座位上,系好安全带迅速发动引擎。车前车后围着一群狗狂吠不已,白冉霞心中虽急又不敢冲撞,好在出了小区狗群狗一哄而散,她一脚油门绝尘而去,像是甩开了万丈阴霾。
昨晚铤而走险抢了东西,赖五心中忐忑一夜未眠,今早打电话给张正宁,想商量一下如何处理,不知为何被挂断了,再打过去已经关机。赖五有些发慌,急忙赶到张正宁家,扬起手大力拍打起来。过了好一会,屋内才响起摩擦地面的脚步声,张正宁打着哈欠开了门,赖五这才放宽心,又忍不住低声埋怨:“三哥还睡呀,虎皮呢?”
张正宁腹内剧痛,头昏脑胀强打精神,里外屋找了几圈,喃喃道:“对呀,虎皮呢?”赖五竖起了眼睛,一把揪住张正宁,怒然大喝:“别装糊涂,你老婆呢!”张正宁拍了拍脑袋,自言自语:“咦,我老婆呢?”
赖五大怒,暗道张正宁要独吞,一拳把他打翻在地。张正宁不可置信地看着赖五,想要还击偏偏手脚发软,只好尽力把他推出房门,赖五死死抓着他,两人扭在一起,脚下一空齐齐跌下楼梯。
听到邻居又制造扰人的声响,对面的男子怒不可解,他气鼓鼓地正要冲其怒喝,一开门就见到两人扭打着摔落下去,楼道外面都听到了一声霹雳也似的吼叫:“杀人啦!”
医院里有一人吊着腿,躺在病床上唉声叹气。前几天莫名其妙被两个人打了一顿伤还没好,一时腿脚不便,昨晚又让车撞了,那司机杀猪似的大叫现在想起来还心有余悸。晚上监控模糊,也不知道能不能抓到对方,他看着缠满绷带的右腿欲哭无泪,看来以后“做生意”足够以假乱真了。眼见病房外又急急推过两个人,他总觉得有点似曾相识。
近日公安局接连收到几起匿名举报,内容大同小异,皆称有两人专门在酒店附近碰瓷敲诈,连续调查几日,今早接到举报称疑似发现嫌疑人,警方调取监控确感可疑,寻找到事主不想顺带破了一起肇事逃逸案。
一个胖子无力地瘫坐在审讯室的座椅上,不禁怆然涕下。昨天晚上他在离家不远的酒店和朋友喝了酒,已经不是第一次酒驾早就习以为常,按理说绝无出事的道理,不想倒霉遇到两人碰瓷的,好不容易摆脱这两个人,车还没开到家就撞了人,还在心存侥幸,没想到警察那么快就找上门去,吓得他立马就招了。
胖子抽了一下鼻涕,哽咽道:“民警同志这真不怪我,都是那两个人害的。”对面两个警察无语地看着他,其中一个警察伸手拍桌打断他的哭诉,皱眉讯问:“你是说那两个人先抢了你的钱,又用你的钱买了你的包?”胖子点点头。警察顿了顿,问道:“包里是什么?”
“虎皮和象牙。”
“什么,虎皮?”警察的声音瞬间提高了八度。“不是真虎皮,是仿品,本来打算用作装饰的。”胖子垂头丧气地解释道。
白冉霞手指轻敲,焦急地等着绿灯,不经意一瞥,从车内后视镜上看到有人抱着一条白狗,正阴森森地望着她。有声音在耳边幽幽轻叹:“你相信有鬼么?”
路边执勤的交警看到白冉霞车前沾血,似有撞击得痕迹,联想到昨夜的肇事逃逸,立刻上前敲敲车窗。前狼后虎,白冉霞情绪失控,尖叫一声抓起布袋,推开车门夺路而逃。后背好像被人推了一下,白冉霞跄了一个趔趄,刺耳的刹车声响过,一只黑色的袋子翻滚着飞上了天。
十字路口乱成一团,不一会就里三层外三层围了好多人。嘈杂的人声中仿佛有道飘忽的声音:“看,我们也是为民除害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