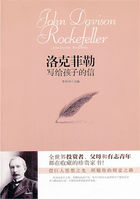赵遣鹿的眼睛深沉,黑黝黝的却缺乏光泽,像一汪波澜不兴的幽潭,一片静寂,却有着孩童般的纯净。
江楼月起身点了灯,殿中明亮起来。一盏又一盏,所有的灯都点亮了。
她在他的眼中,恍惚是当初花烛在畔的太子妃,身上的红衣有着嫁衣的鲜艳。
“清楚多了,可见是灵丹妙药。”赵遣鹿道。
“没有这么快,不过是殿中如此亮,你能明显地感觉到。”江楼月道。
“是么?”赵遣鹿轻吐出二字。过了好一会儿,他又道:“怪不得眼睛感觉有些热。”
江楼月立时放下手中的灯,疾步走到他面前,弯腰问道:“有多热?”
赵遣鹿道:“就像我服下的药液的温度。”
江楼月眼睛不由瞪得大了点,口微张,一时没有说话。
“怎么了?”他问道。
她拉来凳子坐在他面前,“诊脉。”
赵遣鹿挽了袖子伸手,倒是一点不担心的模样。
江楼月立即为他把脉,神情从初时的有些凝重,到疑惑,最后放心下来。她收回手,笑道:“四十年的赤头艽,没有白费。你可以好好地睡一觉了。”
“我的眼睛,很快就能看见?跟以前一样?”赵遣鹿道,有些按捺不住的欣喜。
“对,很快,跟以前一样。”江楼月也有点喜不自禁,这半年里她就没怎么闲过,总算能把他的眼睛治好了。
“你歇着吧。”她道。
顿了顿,赵遣鹿道:“那你……”
“我就坐在这里呗。”江楼月道。
赵遣鹿露出微笑,起身取了一件披风给她,“别着凉。”然后他便去歇了,尽管殿中灯火通明,他却很快就睡熟了。
江楼月手撑着腮,轻阖着眼。
冬夜不算漫长。
赵遣鹿发出一声低低的呓语,醒了过来。
天还没大亮,但殿中的灯火照了一夜,此刻仍亮着。
他没有睁开眼睛,仔细地听着殿中的动静,感觉她还在。
江楼月一夜没睡,把呵欠忍了下来。他的呼吸变化时,她就知道他醒了。脚步轻动,她来到了床前。
赵遣鹿缓缓地张开了眼帘,好似初生见到了第一缕光,眼前的一切从一片模糊渐渐清晰,这个过程只有几个呼吸,他却觉得像是过去了一整年。
“怎么样?”江楼月蹲在床前,微笑着问道,眼底有着难以察觉的几许期待。
赵遣鹿张了张口,一时没说出话来。他看着帐顶,随即转头看向她。她的脸上,还是那熟悉的浅笑,熟悉的眼眉。
“是不是跟以前一样?”她笑问道。
“是。”你还跟以前一样。
“这就好了。今天不用上朝,你可以多睡会儿,我也要回去睡觉了。让木远把这个好消息告诉陈大夫,免得他担心。”说完,她便站起身回自己的寝宫去了。
阴影中一道迅捷的影子闪过。
赵遣鹿浅淡地笑了笑,她的话对木远来说,跟自己的话是一样。
此刻殿中真的只剩了他一人。江楼月的背影消失在殿外,他没有去看,眼中却深邃不见底,心揪地低喃道:“你教我如何还能放手?”
星月元年正月十七,赵遣鹿正在御书房批阅奏折,时不时地抬眼看看总管太监手中展开的一幅幅画像。
“皇上,您看看这一幅画得如何?”总管太监恭敬地呈上一幅画像。
赵遣鹿眉眼微抬,目光落在画上便凝住了,放下手中的朱笔,将画接了过去,嘴角似有笑意。他只道:“赏。”
总管太监笑着在一旁候着,还得等着皇上说出如何赏才好。
“白银万两。”赵遣鹿淡吐出四字。
“是,陛下。”总管太监立时应下,躬身退了出去,抬眼看时,赵遣鹿还在看着那幅画像。总管太监心道,这位皇后娘娘,是个能享福的命。这画像他也看过,端的画得颇具神韵,尤其是那眉眼与笑容的明媚,回眸一笑,真真如天仙一般。
总管太监甫一出了御书房,迎面见着江楼月来了,赶紧恭敬地行礼:“奴才参见皇后娘娘。”
江楼月抬手让他起来,“皇上在里面?”
“回娘娘的话,陛下在里面。”
“你忙你的去吧。”江楼月道。
“是,娘娘,奴才告退。”他看着江楼月进了御书房,脸上露出笑容,皇上若是开心,自然少不了他的好处。
赵遣鹿见进来的是江楼月,立时笑道:“来了。”
江楼月一进来就见他手里拿着个卷轴,随口道:“看什么呢,这么入神。”
他自然却动作非常迅速地将画卷了起来,放在案上,道:“反正是你不感兴趣的。”
江楼月扫了那卷轴一眼,便转开了注意力。
“何事?”赵遣鹿温柔地问道。
江楼月挠了挠脖子,嘀咕道:“这皇后的衣裳穿着就是不舒服。”她这是为了掩饰自己的不好意思,每次她都是有事才找他。
赵遣鹿顿时笑了,“何时这样的事就能拘着你了不成?你爱穿什么便穿什么,连我都不敢说个不字,更何况是别人。”
江楼月低首轻咬了咬唇,下定了决心,抬头看着他道:“你还欠我一件事,你可还记得?”
“先说来听听好了。”赵遣鹿平淡地道,脸上的笑容不变。
他的眼前,已经不再是偶尔才能见到的轮廓。
“我治好你的病,你放我走。”江楼月没有多犹豫,径直将此言道出。
赵遣鹿征战时曾患过近一个月的眼疾,新帝登基时是一个瞎子,眼前全然漆黑一片,什么都看不见的感受,不是第一次,更不是第二次。
“我也有一个条件,你若是答应,我就答应。”赵遣鹿道。
江楼月道:“你且说来听听。”
“为我取了燃蛮。”赵遣鹿道。
“要燃蛮为属国?”江楼月道。
“我要的不是属国,而是灭国。”赵遣鹿道,话语里不带一丝冷意,连看着她时脸上温柔的笑容都没有变。
江楼月退了出去。
赵遣鹿吩咐道:“来人。”宫人立即上前去。
“把殿内的熏香都撤了。”他说着,心中的那一抹烦躁之意,难以挥却。
“是。”两名宫人应下,就开始端起香炉往外走。
“慢着。”赵遣鹿却又道。
宫人躬身在原地候着,手中还端着香炉。
赵遣鹿道:“放下吧,退下。”他平静地说完,缓缓阖上了眼睛。现在双眼已无碍,只是不能太费眼,每几个时辰总得休息一下。但此刻,他觉得自己需要静一静的,不止是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