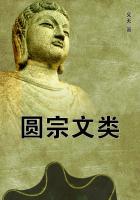我的学校岁月啊!我的生活中从童年到青年间的默默滑动啊――那是我生命看不见、觉
察不到的进展!当我回头看看生活的流水时――现在那已变成荒蔓丛生的干涸的水渠了――
让我想想,还有没有什么痕迹可使我记起它当年怎么奔流的呢?
一会儿,我就坐在教堂里了。每个星期天的早上,我们先在学校里全体集合,再一起去
那儿。泥土的气息,阴沉的空气,脱离红尘的感觉,透过黑白两色的拱形穿堂和侧堂传出的
风琴声,这一切都变成一些翅膀,把我托在一个迷迷糊糊的梦上,使我在那些日子间飞来飞
去。
我不再是学校中最末等的一个学生了。几个月里,我就超过了好几名。不过,我觉得那
第一名的学生是个卓绝的人物,离我很远。他高高在上,令人望了为之晕眩而无法企及。爱
妮丝说“不对”,我说“对”,并告诉她,那个了不起的人物已掌握了很渊博的学问,她却
认为就连我这么一个前途无望的人到时候也能达到他的高度。他并不像斯梯福兹那样是我个
人的朋友和大家的保护人,但我崇敬他。我很想知道,离开斯特朗博士学校时的他会是什么
样的人,人类怎样才能不让他得到一个地位。
可那突然出现在我面前的是谁?这是我爱的谢福德小姐。
谢福德小姐是尼丁格尔太太学校的住读生。我崇拜谢福德小姐。她是一个小姑娘,穿着
短外套,圆圆的脸蛋,浅黄的卷发。尼丁格尔太太学校的女孩们也来教堂做礼拜。我不能看
我的书了,因为我必须看谢福德小姐。唱诗班唱诗时,我只听见谢福德小姐的声音。做礼拜
时谢福德小姐的名字一直在我心头――我把她列入王室家族里。回家后,在我自己的卧室
里,有时我被一阵阵爱情冲动着叫道:“哦,谢福德小姐!”
有一段时间,我对谢福德小姐的感情没把握,可是,后来由于命运之神的仁慈,我们在
舞蹈学校里相遇。我才得以谢福德小姐为舞伴。我触到她的手套那瞬间,便感到一阵颤栗一
直上升到我短外套的右边衣袖,一直从我头发间冒出。我从没对谢福德小姐说出一句热情
话,可我们相互理解。谢福德小姐和我是天生的一对。
我真不明白,为什么我偷偷把十二个巴西核桃送给谢福德小姐作礼物呢?它们并不表示
爱情,也无法包成个模样,就是放在门缝里也难轧开,就算轧开也油腻腻的。可我觉得这东
西就是于谢福德小姐相宜;我还送给谢福德小姐又松又软喷喷香的饼开,还有数不清的桔
子。有一次,我在衣帽间里吻了谢福德小姐,真是**!第二天,我听到传说:谢福德小姐
因走路时趾尖向内而受尼丁格尔太太的责备,我是多么痛苦和愤慨啊!
谢福德小姐溶入了我的一生和梦想,我又怎么能和她断绝关系呢?我想不出来。可是,
谢福德小姐和我之间开始有了冷漠。我听到一些躲躲闪闪的闲言,说是谢福德小姐亲口说过
她希望我不要那样直瞪瞪地盯着她,还说她更喜欢琼斯――更喜欢琼斯!那个一无所长的学
生!我和谢福德小姐的隔陔越来越大。终于,一天,正好碰上尼丁格尔太太学校放学,谢福
德小姐经过我时做了个怪样儿,还对她的同伴们那么笑。一切都成为过去了。整个生命的热
情――似乎是整个的没什么两样――已经到此为止;谢福德小姐从早晨的礼拜中退下了,她
再也不是王室中一员。
我在学校里地位高了起来,没人再来打扰我。那时,我对尼丁格尔太太学校的少女们一
点也不讲情面,就算她们的人多出一倍,漂亮二十倍,我谁也看不上。我觉得舞蹈学校让人
生厌,也为那些女孩不能自己跳而纳闷,她们为什么不把我们放开呢。我在拉丁诗方面有所
造诣,对鞋带不屑留心了。斯特朗博士向大家称我为有前途的青年学者。狄克先生很是高
兴,姨奶奶也经下一班邮车给我寄来一个几尼。
一个青年屠夫的影子出现了,像《麦可白斯》里戴着帽盔的怪物那样。这青年屠夫是
谁?他令坎特伯雷的少年们害怕。有一种迷信的说法广为流传,那就是他那特异的力量来自
搽头发的牛腰油,所以他能和成年人抗衡。这青年屠夫脸宽宽的,脖子像公牛的那么壮,腮
帮粗糙发红,心智不太清楚,舌头老滚动着骂人。他这舌头的主要功能是谤骂斯特朗博士学
校的学生。他公开说,任这些学生要求怎么样决斗,他都应战。他点名道姓说对学生中有些
人(也包括我),他可以把一支手绑在背后,只用另一只手便能击败。他袭击年纪小的学
生,乘他们不防打他们的后脑勺,并在街上当大家面跟在我身后向我挑衅。为了这些种种理
由,我决定和这屠夫决斗。
这是一个夏夜,我依约在一个墙角的洼地草丛中和屠夫相遇。我带有一群从我们学生中
选出的勇士,屠夫带了两个另外的屠夫、一个年轻的酒店店主和一个扫烟囱的工人。条件讲
定了,屠夫和我相对而立。不一会儿,屠夫在我左眉上点燃了一万支蜡烛。又过了一会儿,
我不知道墙在哪儿,而我又在哪儿,也不知道别人在哪儿了。我俩不断打成一团,我竟不能
分辨哪是我,哪是屠夫,我们抱成一团在草地上滚过来又滚过去。有时,我看见流着血而镇
定无事的屠夫;有时我什么也看不见,只是坐在我助手的膝上喘气;有时我发了疯似地向屠
夫进攻,把我的指关节在他脸上碰破却也一点没让他惊慌。终于我醒了过来,头晕糊糊的,
好像从一场昏睡中醒来;我看到屠夫走出去,接受着另两个屠夫和扫烟囱工人及酒店店主的
祝贺。他一面走,一面穿上外套,看到这我相信胜方是他了。
我被送回家的那模样很凄惨。人们在我眼睛上放上牛肉片,又用醋和白兰地揉擦;我的
嘴也肿了一大块。一连三、四天里,我都待在家里,眼睛上戴了个绿眼罩,难看极了。要不
是爱妮丝像姊妹那么对待我,安慰我,读书给我听,而使时间轻松愉快地过去,我准会很烦
很闷的。我一直对爱妮丝百分之百地信任,我把有关屠夫的一切,以及他对我的中伤都讲给
她听了,她认为我只有和屠夫决斗才对,可是想到我和他的那场决斗,她就不寒而栗。
不知不觉,岁月流逝,班长不再是亚当了,他也好久不任班长了。亚当离开学校已那么
久,他回来看望斯特朗博士时,除了我已没什么人认识他了。亚当马上就要进入法律界作辩
护律师,戴上假发了。我发现,他比我想象中的更谦谦有加,外表也不那么招摇,这一点叫
我很惊奇。他还不曾轰动世界,这世界仿佛就是没有他也能照样转下去――就我所知如此。
一段空白,诗歌和历史的战士们那漫长无尽的队列大摇大摆走过的一段空白――后来怎
么样呢?我当了班长。我往下看位居我下面的学生,带着屈尊俯就的意思。他们中有些学生
使我想起我当年刚来的情形,我对他们尤为亲切。当初那个小不点好像根本就不是我。我回
忆起他时就好像是回忆起人生路途上遗落在后面的什么东西――好像是回忆起我从其旁边经
过的什么东西而不是我――就像回忆起别人一样。
我在威克费尔德先生家第一天里见到的那个小女孩,她又在哪儿?我再也没看见她。取
而代之的是那幅肖像的翻版,这翻版在家里上下走动(不再是一个孩子的化身了)。爱妮
丝,我亲爱的妹妹――我在心里这么称呼她――我的顾问和朋友,对于一切受到她那种详和
善良和克己精神影响的人来说又是幸运女神,完完全全成人了。
我的个头和外貌变化了,我积累的学识也变化了,我还有什么别的变化呢?我挂了一个
带金链的金表,小手指上戴了个戒指,穿了一件长后摆的外衣,还用了不少发油(这东西和
戒指配在一起,真难看极了)。我又恋爱了吗?是的,我崇拜的是拉金斯家最年长的那位小
姐。
最年长的拉金斯小姐并不是一个小姑娘。她成年了,高挑个头,肤色黑黑,眼睛黑黑。
最年长的拉金斯小姐并不是一个稚气十足的小妞妞了,因为就连最小的拉金斯小姐也不是
了,而最年长的必然还要大三、四岁。也许,最年长的拉金斯小姐都快三十岁了。我对她的
热情超出了常情。
最年长的拉金斯小姐和一些军官很熟识。这事让人挺不好受。我看见那些军官在街上和
她交谈。我看到,那些军官一看到她的小帽和她妹妹的小帽(她对于小软帽有种显然的偏
爱)从人行道上过来,便穿过街道去见她。她有说有笑,好像对这感到很称心。我花了大量
时间来回徘徊就为了能见她一面。如果一天我能向她鞠躬一次(由于认识拉金斯先生,我也
认识了她,所以能向她鞠躬),我就欣喜万分。我常有幸向她鞠躬。在赛马期间举行夜间舞
会的时候,我知道最年长的拉金斯小姐会和军官们在舞会上共舞。如果世上有公道,我所感
受的痛苦就应该得到一种补偿。
热情烧坏了我的胃口,热情使我走马灯似地戴新丝巾,如果不穿上我最好的衣,不一次
次擦干净我的鞋,我就没法安宁。只有这样一来,我才似乎比较能配得上拉金斯小姐。一切
属于她的东西,或一切和她有关的东西,我都觉得珍贵。拉金斯先生是个粗鲁不堪的老汉,
吊着双下巴,有一只不能动的眼嵌在脑瓜里,在我看来却很有趣。看不到他的女儿,我就到
他通常会去的地方,对他说“拉金斯先生,你好吗?年轻的拉金斯小姐们和一家人都好
吗?”这样似乎太露骨,我不禁脸红了。
我常想到我的年龄。我才十七岁,说十七岁委实太年轻了,和拉金斯小姐不班配,那有
什么关系?再说,我不久就会是二十一岁的人了。虽然亲眼见那些军官走进去,或听到他们
在最年长的拉金斯小姐正弹着竖琴的客厅里的动静,这些都令我伤心,但我仍然常在拉金斯
先生的住宅外踱来踱去。甚至有那么两或三次,那一家人都入睡后,我还心灰意懒、神情恍
惚地围着那房子转悠,想弄清哪间屋是那最年长的拉金斯小姐的香闺(现在我相信,我把拉
金斯先生的卧室错认作她的了);一心巴望那里会失火,聚在那里的人会吓得不能动弹,于
是我就带着一张梯子冲过人群,把梯子靠在她窗子上,把她抱着救出来,再回去取她留在那
儿的其它东西,就这样丧生于火海中。我在爱情方面一般来说不自私,所以想到只要能在拉
金斯小姐面前像个人物也就死而无憾了。
大概就是这样,但不是常这样。有时,我眼前升起了光明的幻景。当我穿戴打扮好(这
是要花两个小时的一件事)去拉金斯家赴大型舞会时(这是要用三个星期去等待的),我用
乐观的想象来满足我的幻想。我想象我鼓足了勇气去向拉金斯小姐求婚。我想象拉金斯小姐
把头伏在我肩头说:“哦,科波菲尔先生,我能相信我的耳朵吗?”我想象拉金斯先生第二
天一早等着我,对我说:“我亲爱的科波菲尔,我女儿已经都告诉我了。年轻点没什么妨
碍,这里是两万镑。祝你们幸福!”我想象姨奶奶发了慈悲而为我们祝福;狄克先生和斯特
朗博士都来参加婚礼。我相信――我的意思是:当我回忆这一切时我相信――我是一个很理
智的人,也不张狂,可我就是一直这么想象着。
我来到那有魅力的房子,屋里有灯光、谈话、音乐、鲜花、军官(看见他们我就伤
心),还有最年长的拉金斯小姐――一团美丽眩目的火焰。她穿着蓝色的长裙,头插蓝色的
花――蓝色的勿忘我――似乎她真需要戴勿忘我那样!这是我第一次被邀出席的真正成年人
的舞会,我感到有点不自在,因为我好像不属于任何圈子,大家对我都无话可谈,只有拉金
斯先生问起我那些同学们,而他也不必这么做,我并不是去那里出洋相。我站在门口,直盯
着我心中的女神以饱眼福。过了一些时候,她走了过来――她就是最年长的拉金斯小姐呀!
――兴致勃勃地问我可想跳舞。
我鞠了一躬,结结巴巴地说:“和你跳,拉金斯小姐。”
“不和别人跳吗?”她又问道。
“我不愿意和别人跳。”
拉金斯小姐笑了,脸也红了(我觉得她脸是红了),便说:
“那就等下一只曲子吧,我很高兴。”
“时间到了。”我想,这一定是华尔兹,“我去请拉金斯小姐时,她犹犹豫豫地说道,
“你会跳华尔兹吗?如果你不会,贝利上尉――”
可我会跳华尔兹(并且跳得相当好),于是我把拉金斯小姐带开了。我很郑重严肃地把
拉金斯小姐从贝利上尉身边带开。无疑,贝利上尉很沮丧,可和我有什么相干。我也沮丧过
呀。我和最年长的拉金斯小姐跳起了华尔兹!我不知道我身处何地,置身于何样人间,也不
知时间的流逝。我只知道,我带着一个蓝色天使游来游去,我如痴如醉,幸福万分。我带她
游呀,直到后来我发现我自己和她一起坐在一个小房间的沙发上休息。她夸我纽扣孔里插的
一朵花(是粉红的山茶花,价值半克朗)。我把花给她,并说:
“我要为它讨一个昂贵的价格,拉金斯小姐。”
“真的?是什么呢?”拉金斯小姐问道。
“你的一朵花,我会像守财奴珍惜金子那样珍惜它。”
“你是个胆大的孩子,”拉金斯小姐说,“给你吧。”
她把花给我时并不显得不快;我把花放在嘴上后再放进我怀里。拉金斯小姐笑着把手伸
进我胳膊里说:“嘿,现在把我送回贝利上尉那儿去吧。”
我正在玩味这愉快的华尔兹和相会时,她挽着一个已过中年的男子来到我这儿,这男子
长得一点也不帅,整晚都在玩牌。拉金斯小姐说:
“哦!这就是我那大胆的朋友!切斯尔先生想认识你,科波菲尔先生。”
我马上感觉得到他是这一家的朋友,便觉得好不得意。
“我很欣赏你的鉴赏力,先生,”切斯尔先生说道,“你的鉴赏力令人佩服。我想,你
对霍蒲这种酿酒的植物不怎么感兴趣,可我却种了很多霍蒲;如果你愿意到我们那一带――
就是阿希福德一带――看看我们的那地方,我们一定也高兴,你愿住多久就住多久。
我热诚地感谢他,和他握手。我觉得我是在一个幸福的梦里。我又一次和最年长的拉金
斯小姐跳起了华尔兹――她说我跳得真棒!我回家时心里真说不出有多快活,整夜我都在想
象:我一直挽着我亲爱的蓝衣女神跳华尔兹。以后的一连几天里,我都沉浸在幸福的回忆
中;可是我却没能在街上碰到她,造访她家时也没见到她。我只有用那朵已干枯了的花――
那神圣的信物――来安慰自己失望的心。
“特洛伍德,”一天晚饭后,爱妮丝说道,“你猜谁明天结婚?是你崇拜的一个人呢。”
“我想总不会是你吧,爱妮丝?”
“不是我!”她正在低头抄乐谱,这时抬起脸来高兴地说。
“你听见他说什么吗,爸爸?是最年长的拉金斯小姐呢。”
“嫁――嫁给贝利上尉?”我用最后剩下的力气问道。
“不,不是嫁给什么上尉。是嫁给切斯尔先生,一个种霍蒲的人。”
约有一两个星期我都非常沮丧,我取下戒指,穿上最次的衣,不再用发油,一个劲对着
前拉金斯小姐已枯萎的花叹气。那时,我对这种生活也厌倦了,又逢屠夫再次挑衅,我就扔
掉那朵花去和屠夫决斗,结果我打败了他。
今天看来,这件事,加上我再次戴上戒指,还有再次有节制的用发油,都是我步入17
岁时留下的脚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