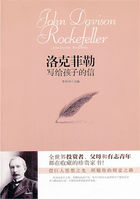韩子高看到李玄霄与宋明哲二人面色缓和许多,没有了刚才开门见面时的苍白无力,约莫是二人已经缓过气来,正了正衣襟,伸出二指,轻敲桌面,脸色一变,一本正经的说道:
“昨日我福隆帮安插在百毒教内的眼线送来一封密报,所以在楼心月屠戮血蝎门赶回长安城之时,才能被我福隆帮做了个截胡的买卖,礼部宝玺就落入我手中。那场争斗之中,楼心月本就被我用见不得光的手段所伤,落下个可大可小的病根,再加上在我授意下余下的二百锦衣与那百毒教四大长老且战且退,耍了一整日的捉迷藏游戏。因此才导致百毒教内部空虚高手不足,明哲与玄霄能够在楼心月手中捡回一条命来也不足为奇。现在礼部宝玺就在我手中,明哲走的时候记得带上,也算是物归原主了。”
面色终于恢复一丝红润的宋明哲笑着点点头,没有说话。
这么多年的兄弟友谊在面上摆着,韩子高上上下下对宋氏家族的临意照拂,已经不是一句感谢就足够偿还两情的。
“接下来,我想说一些重要的事情。”
说着,韩子高的眼角有意无意的扫了一眼李代。
身为皇子的李弘文立马会意,对着黏在韩子高身边的明珠公主李婉宁,温声说道:“婉宁,你不是早说要去陈记买些宫里难见的吃食吗?”
心思伶俐的李婉宁哪能听不出李弘文话中的含沙射影,瞪了一眼自己的亲哥哥,冷哼道:
“想赶我走就直说嘛,拐弯抹角的有意思吗!”
韩子高伸出手轻轻拍了拍李婉宁的手背,轻声说道:“到时莫要只顾着吃忘了时辰,误了回宫的时间被你娘亲发现就不好了。对了,记得给我带些焦油麻花,我也想吃了。”
李婉宁眯眼笑道:“知道啦!”
走过李弘文身旁时李婉宁还不忘在他头顶重重的“哼”了一声,对着李兄玄霄说了一句“小玄子记得有空找我去玩”,便撒欢一般的打开房门雀跃而出。
门外两名锦衣汉子立即分出一名,紧随其后。
关上房门之后,李玄霄皱眉望向风雅纯儒的韩子高,低声说道:“你的腿到底是怎么回事!”
韩子高眼神古井不波的盯着桌上釉红玉嘴茶壶,语气平静的说道:
“十年前,学府遣散咱们那批士子后,我就携家带口赶赴长安,期许着考个功名好为离逝的师兄们说些话。只不过在路过二梁山时被劫掠上山,我的父亲、哥哥直接就被做成人肉包子。那时我还小,再加上身子孱弱也不甚引人注目,后来娘亲用自己的身体保下我的性命。在二梁山上苟延残喘的活了一年,博取他们的信任后,有一天我趁他们不备带着娘亲偷跑出山,却还是被他们发现追上,也就落下了个残疾的毛病。”
李玄霄看着韩子高平静的神情,仿佛这段凄惨的往事没有发生在他身上,而只是一段道听途说的故事一般随口说出,心中如刀绞般难受。
一个人的内心要强大到如何境地才能心平气和将辛酸往事一一道出?
而韩子高无疑是心志坚毅之辈中的佼佼者。
“后来正巧碰上从太桑成回京的福隆帮弟子,只不过当时那几名弟子地位不高,也只是因为有一颗菩萨心肠,仗着福隆帮的威名从山匪刀下就下我母子二人,本着井水不犯河水的念头也就没有与二梁山的人起冲突。”
说着,韩子高闭上双眼,合身躺倒在轮椅之上,平静地说道;
“到了长安城后,我有幸受到老帮主的青眼相加,没过两年,就做上了福隆帮客卿的位置。”
说着,他双手扣紧轮椅扶手,整个清逸的身体竟然开始莫名颤抖起来,他竭力压抑住心中情绪,继续说道:
“后来,我带着五名锦衣,于隆冬大雪时分登上二梁山,再下山时,山顶的积雪就都已经融化了,就像是秃了顶的老男人。”
缓缓睁开眼,他仿佛看到那幅画面一般,双目失神,伸出手向前探起,喃喃说道:
“二梁山上下八十七名山匪,我一个一个的点了足足八十七盏天灯,滚淌血水融化积雪后又被冻成冰棱,在日头底下熠熠生辉,就好像冻结实了的红色湖面,我韩子高毕生难忘那等美景......”
李玄霄心中暗叹了一口气,没有说话。
一旁的宋明哲与李弘文也都是面色悲伤,低着头,沉默不语。
良久无声也无言。
……
不知过了多久,韩子高回过神来,看着三个相对无言的人,深吸一口气,吐出胸中复杂的情绪后,轻咳一声说道:“这次把你们叫过来,主要是因为二先生从东池学府寄来三封密信。”
闻言,三人俱是抬头,挺了挺腰板,等待韩子高说下文。
“二先生寄来的三封密信,每一封都仅有二字。”
顿了顿,他继续说道:
“第一封密信上有‘夺玺’二字,收到这封密信后,我发动福隆帮所有眼线得知近日礼部宝玺被盗之事,还没来得及跟明哲细说便带人赶赴血蝎门,后来的事情大家也都知道了。血蝎门盗了宝玺,百毒教抢了宝玺,我福隆帮黄雀在后最终渔翁得利。”
一直沉默不语的李代低头皱眉道:
“问题是,血蝎门为何胆敢偷盗礼部宝玺,要知道宝玺之中就属礼部宝玺最为无权无势,而且使用过程冗杂程序繁多,血蝎门要礼部宝玺有何用处?”
李玄霄继续说出心中的疑惑,面对四人之中唯一一个饱读诗书神机妙算的人,他也一点没有隐藏心思,
“而且平日素来相安无事的百毒教为何会无缘无故的将血蝎门灭门?难不成百毒教也对礼部宝玺有了觊觎之心?”
韩子高没有直接回答,而是从小处入手大处着眼,“万流入海,皆有根源。所有事情的起因就是争来夺去的礼部宝玺,如果我们不知道他们盗取礼部宝玺的目的是什么,不妨转换思维,礼部宝玺在最近的时间里最大的用处是什么?”
三人的目光齐齐投向皇子李弘文,四人之中韩子高属于江湖帮派,与官府朝廷牛头不对马嘴,平日相见也都是横眉竖眼相看两相厌。
宋明哲的父亲虽说是堂堂礼部侍郎,可他自小便对政治手腕不感兴趣,要不然也不会在进入东池学府后没有选择权谋之辩的“帝范堂”而是选择了以剑入道的“御剑堂”,也算是不了解其中奥妙。
李玄霄更不用说了,在长安的时候年纪尚幼,虽说平日里与那些权贵子弟勾肩搭背互道兄弟,可那也仅仅是在赌坊勾栏之中的酒肉之友,根本够不到相互交心的地步。
最后就只剩下这位挂着四品兵部左散侍头衔的皇子李弘文了。
李弘文皱着眉头思忖道:“礼部宝玺本身就只是礼部发布檄文时的加盖之物,本身并没有多大权力。若说最近有什么大事需要礼部宝玺出现的话......”
突然,他目光一凝,大惊失色道:
“国祭大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