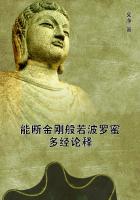黄昏,黑压压的乌云像赛跑似的从东边天空飞奔过来,密布在头顶上空,大队保管室外边的几棵大树随着狂风不停地摇晃着。风送信来,大雨就要来临了。这时,大队长用喇叭喊起来了:“请贫下中农同志注意!请贫下中农同志注意!根据气象台的紧急通知,今晚我地区有一场暴雨,同时河谷地区有六到七级左右的大风。希望同志们做好避风防洪的工作……”
来了好几个社员帮有才伯他们把种粮收进保管室后,就各自回家去了。有才伯和杨双全又把保管室周围仔细地检查了一遍,把有可能漏雨的地方都用晒席遮严了。然后,和杨双全在晒场捡撒在地上的粮食。
“唉……”杨双全长长地叹了口气说:“这个活,真麻烦。”
“是呀!世上没有不麻烦的事。”有才伯爱惜地捡起一粒粒粮食,并嘱咐旁边的杨双全说:“双全,仔细点,把每一颗种子都捡起来。”
“今年粮食这么多,撒掉几粒有啥要紧的。”杨双全低着头,漫不经心地捡着,翘着嘴巴嘟嚷着。
“有啥要紧?你对保管粮食的责任心太差了,双全!”有才伯收敛起脸上的笑容,语重心长地说:“双全,你要知道,在旧社会里,我们贫下中农为几棵粮食,有的还丢掉了性命。”
“……”杨双全还是无动于衷地捡着地上的稻子。
有才伯伸出青筋突暴的右手,把手背上足有两寸多长的三条伤痕摆到杨双全面前说:“双全,你看我手背上是什么?”
“伤痕。”杨双全用眼角瞟了一眼,爱理不理地说着。
“你猜,这伤痕是怎么来的?”
“我不知道。”
“不知道,就听我说把。”
有才伯咬牙切齿地说:“这三条伤痕是地主刮地王用腰刀砍的。”
“刮地王砍的?”一提到刮地王,杨双全就想起了他那去世的父亲,他吃惊地抬起头,出神地望着有才伯。
“是的。”有才伯收回右手,继续捡着地上的粮食,他满腔仇恨地又讲起了这三条疤痕的来由:“……刮地王和狗腿子都走了,只见昏死过去的妻子和口鼻都流着鲜血的孩子,谷子也撒满了岩洞。他摸了摸孩子的胸口,已经没了心跳……”
有才伯讲到这里,已经讲不下去了。他用衣袖擦了擦眼泪,又悲痛地说:“双全那!在解放前,穷人为了吃几粒粮食,不知被夺走了多少条生命!解放后,毛主席他老人家才把我们从苦海里解救出来,穷人翻身做主了,要不然,我那杨德智也早就见阎王啰。”
有才伯越说越激动,“粮食是个宝呀,一个保管员不爱惜粮食,撒掉几粒粮食,有啥要紧的,人人都这样想,我国有七亿多人,那一共要撒掉多少?我们做了国家的主人,不算这笔帐不行啦!每一颗粮食都是集体的财产呀。说远了你不知道,就拿前两年大伙食团来说吧,你是见道它的重要性的。”
杨双全这时觉得很惭愧,不好意思地抬头望了望有才伯,又低着头说:“有才伯,你的话我全明白了,从今以后,我一定爱惜每一粒粮食。”
“明白了就好!明白了就好!”有才伯高兴地笑着,过了一会儿他又说:“搞这项工作不但要安心,爱惜每一粒粮食,而且在刮风下雨时,还不能放心大胆地睡大觉,更不能麻痹大意,要严防敌人的破坏和捣乱。”有才伯和杨双全把晒场上的粮食捡完后,又把保管室周围察看了一遍才回家吃饭。
天黑了,乌云越来越厚,雷声在不停的响着,闪电一道一道划破长空。说来也奇怪,已经农历十月了,还电闪雷鸣,这是少有的。有才伯回到家里,春玉婶已经弄好晚饭,他吃完晚饭,像往常一样,抽着叶子烟搓粽绳。因为保管室里大部分的箩绳都要换了,他自己都不知道搓了多少个晚上了。
“德智他爹,队里的母猪快要下小猪了,这几天,天气变化又快,我今天晚上要去照顾母猪,不在家里歇息。”贤惠的春玉婶四十来岁,比有才伯小整整二十岁,不知道的还以为他们是父女呢!夫妻间年龄虽然相差大,但感情却很好。
“你安排了就是。”有才伯笑着回答。
有才伯的家坐落在指头山(十指山)半山上的黑竹湾里,房屋四周布满了枝干黑得发亮的翠竹林。相邻的几十里村庄凡是需要做烟杆、帐杆、钓鱼竿的人,都喜欢到这里来找。他家分得三间瓦房,猪棬房在一边。杨有才虽已年过花甲,但精神却很好。他除了保管室的工作外,队里需要担抬的他还要揽一分,他自从成立了农业合作化以来,一直担任着保管工作。他认真负责。干部群众都很信任他。凡遇刮风下雨,他都跑下山去坐守在那里,害怕漏雨把粮食霉烂了。有一天,他从山下回家时,发现一个标有‘椅子湾大队’字样的箩筐烂了口,甩在了坡上,他一声不响把它捡回家,用自己的竹子把箩筐修补好放回保管室的农具室。这些正好被甩箩筐的那个青年全看见后告诉了大家。社员们都称他是集体的‘红管家’。
“咔嚓——,轰隆——”震天动地的霹雷击在屋顶上空给狂风助威,接着,零星的大雨点打在瓦片上,嘀嗒嘀嗒的响。杨有才放下手中还没搓完的棕索子,打开大门,一股狂风扑进屋吹灭了油灯,屋里立刻变得漆黑一团。他站在门口,借瞬间的闪电光看到外面的树被吹弯了腰,雨点也不停地飘向阶沿。
“糟糕!保管室的房子怎么样了,我得去看看。”他立即回屋,把马灯点亮,从墙上取下蓑衣斗笠,披戴在身上,提着马灯就往外冲。
有才伯刚跨出大门,猛兽似的狂风接连刮断了好几根竹子。他刚走出院坝不远,就从身后传来了一声巨响,猪也不停地叫了起来,他借闪电光回头看了眼,是猪稝塌了。但有才伯一心想着保管室,就没有回去,仍然提着马灯径直向山下村南的保管室走去…….
有才伯到保管室的时候,只剩手中的马灯了。这时,杨双全也顶风冒雨地照着手电筒来了。他们赶紧打开门,将保管室内都检查了一遍,并没有发现漏雨的地方,才到保管室内空地歇息,这一老一少互相望着泥人般的身体,不觉都笑了起来。有才伯从荷包里拿出叶子烟,准备吸一节熏熏脑袋,可叶子烟全被雨打湿了。这时,外面又刮起了狂风,只听哗啦一声,几块碎瓦片从房顶上掉下来,好险啊!擦过杨双全的身子落在了地上。他们用手电筒照了一下,雨注直向粮仓里泻来。他们马上用席子把粮屯盖了两层,有才伯沉着地吩咐道:“双全,快搭楼梯!上房子补漏去!”
有才伯心急之下抱了一捆谷草,从杨双全搭好的梯子爬上保管室的屋顶。屋顶有好几处都在漏雨,有才伯把谷草铺在漏雨处,但刚一松手,谷草就被风吹走了。他见谷草不能解决问题,就大声地向下喊道:“双全,赶快拿床晒席上来!”
杨双全急忙从保管农具的屋里扛出一床晒席,吃力的递上去。有才伯费劲打开晒席铺在屋脊两边,盖住漏洞。他还没缓过气来,又一阵狂风,把晒席也卷走了,他也差点被卷下房子。“双全!再把晒席递上来。”
狂风刮得杨双全睁不开眼,他把掉下来的席子吃力地重新卷好,扛起晒席扶着楼梯爬上房顶,帮助有才伯把晒席铺好,并把晒席两头的绳子栓在屋檐上。狂风暴雨放肆了一阵,也许是感觉累了,就渐渐停了下来。有才伯蹲在房子上,用袖子擦了擦脸上的汗水和雨水说:“双全,我在这里守着,你下房子去,叫社员们赶快来,趁着这时候风小,把房子上的瓦重新盖好。”
“好!”杨双全梭下房子后,有才伯在房子上觉得浑身冷得颤抖起来,两腿关节也痛起来,他咬紧牙关,想坚守在房上。
“唿……嗚……”狂风又咆哮起来了,暴雨也来了,屋顶后边忽然捆晒席的绳子断了,席片被狂风卷起来,有才伯见事不妙,马上爬过屋脊用自己的身体死死地压住晒席,他迎着狂风暴雨,咬紧牙关自言自语道:“风再大,雨再猛,也吓不倒我杨有才!”
狂风暴雨无情地摧残着有才伯,他的牙咬得更紧了,头沉重得快要抬不起了,‘轰隆……’又一次惊雷击响了,他把头抬得更高,望着锅底一样黑的天空。他抓住屋檐压住晒席,信心百倍地念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争取胜利。”
“唿……嗚嗚……”狡猾的狂风这时改变了方向,偷偷从房子前面袭击过来,他马上支撑着身体,向房顶前面漫漫地爬去,刚爬到脊背上,咔嚓一声前面的绳子也断了,他被晒席卷住了身体,向保管室后面滚下去。
杨双全跑到生产队长黄平的院子叫人,他把情况简单述说后,黄平马上通知了一些民兵和社员与杨双全一起奔向保管室,他们赶到保管室外边,用手电筒照了照房顶上,晒席没了,有才伯也不见了,杨双全大声地喊起来:“有才伯!有才伯!……”
“……”没有有才伯的回应,杨双全神经立刻紧张起来。
“有才伯!”“有才伯!”
“有才伯在保管室后边。”这时张宝山沉重地回答。大家纷纷向保管室后面跑去,只见张宝山抱着昏迷的有才伯坐在地上。
“有才伯怎么样了?”“有才伯怎么了?”众人惊慌地问。
“有才伯从房顶上摔下来,昏迷了。”张宝山着急地告诉大家。
张宝山在下午会议结束后,他没过回家,他到杨志勇家里,又把如何修抽水站的事研究了一翻,狂风暴雨时,他才从杨志勇家里出来,直奔保管室来。他知道像这样的天,有才伯一定在保管室忙着。来这里也好协助做一些遮风避雨的事,随便也商量些事情,刚走到保管室大门口,就听见屋后边‘啪’的一声,接着就听见细细的‘哎哟’声,张宝山跑到屋后边用手电筒一照,有才伯的前额被摔破了两寸长的口子,伤口处像嘴巴一样地张着,露着白骨头,血不停地流着,张宝山立即把他抱在怀里,正在不之所措时,杨双全带着群众赶回来了。
“有才伯!有才伯!”杨双全急得流下了眼泪,他蹲下身子,用手电筒照着有才伯,摇着他的肩膀,在场的社员也跟着喊着。
“大家都不要闹,让有才伯清净地躺一会嘛!”张宝山叫杨双全扶着有才伯的上半身,自己从地上爬起来,用毛巾轻轻地擦着有才伯脸上的泥浆和血,并撕下自己的衣服给有才伯包扎伤口,嘴里吩咐着卢腊梅到办公室叫救护车。
杨志勇、刘大民带领群众抢修保管室的漏处忙开了:有照亮的,捆绑竹条的,搬瓦的,盖瓦的,大家七嘴八舌,手忙脚乱的行动起来了。黄平的大女儿黄素珍抱来两床棉被和几套衣服,张宝山他们把有才伯抬进屋里不漏雨的地方,给有才伯换上干衣服,这时,张宝山发现有才伯的右腿也骨折了。
卢腊梅跑到大队办公室,办公室的大门却紧紧地闭着,她用拳头敲着门喊道:“杨会计!杨会计!”
“深更半夜的,你找我有什么事嘛?”杨连永不高兴地说着。
“有才伯受伤了,我要给医院打电话,联系救护车。”卢腊梅急切地解释着说。
“好!我马上起来。”杨连永高兴极了:这个死对头终于遭报应了。他悄悄地把安在墙上的电话开关关了,然后才把油灯点燃,开门假装关心地问:“卢书记,有才伯是在哪个地方受伤的?”
“保管室。”卢腊梅没多说话,走进办公室拿起话筒乌鲁鲁地摇起来,“喂!喂!……”
“……”听筒里还是没有回声,他向旁边的杨连永问:“怎么搞的?电话打不通。”
“我也不知道。天刚黑时,公社打来电话说,要防风防洪时都还是好的。”杨连永揉着两只眼睛说。
卢腊梅很有经验地查看着室内的电话线,发现问题出在开关上,他瞟了杨连永一眼,拉上开关,再摇起电话来。
杨连永说:“哎呀!是刚才打雷时我把电话线关了!”
卢腊梅没有理睬他,电话打通了,她对着话筒说道:“喂!你是公社邮电所的小李吗?……请你帮我接通县医院!……你好!你是县医院吗?……我是龙安公社椅子湾大队的,我们大队杨有才今晚上为抢修保管室,受了重伤,眼前危险,请你们开救护车来接一下,……怎么?救护车下雨天来不了?又还不在家?……啊……”卢腊梅惋惜地放下电话。
县人民医院的救护车在一个小时前,已经开到红星公社去接一个危在旦夕的患腹膜炎的产妇去了。卢腊梅跑回保管室,把情况告诉了张宝山。杨连永也冒着雨到保管室来看热闹,他嬉笑着说:“张书记,赶快想法子把有才伯送进医院,他伤的这么重。”
“你说得对,我知道!”张宝山思考了一下说:“卢腊梅,快去叫刘大民把拖拉机开来!”
“不行啦,我们这土公路雨天没法开车!我们就用阀杆抬送吧。”在场的几个男社员说。
“对!只好用阀杆抬送。”杨金、杨应还有几个男社员就立即去准备护送有才伯去医院所需的东西。不到一刻钟,一切准备好后就用阀杆把有才伯抬走了。张宝山把卢腊梅和杨志勇叫到身边,把应该做的和该防备的工作商量了一下,叫卢腊梅到有才伯家里去告诉春玉婶,并代表党支部对她进行安慰,他说完就追有才伯他们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