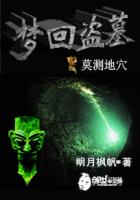终于到了半夜,整个镇子都陷入黑暗里,只有几个路灯像鬼火一样闪着幽幽的蓝光,吴水才已经饿得前胸贴后背,两眼放出鬼火一样的蓝光。吴水才走进菜地里,心里饿得慌,手却不乱,他先扯了几个黄瓜,一块地里扯一个,这样不显眼。几个黄瓜吃下肚,感觉全变成了水,不顶饿,就去了苕地,抠红苕吃。抠了几个红苕,也懒得洗泥,顺手扯下几片苕叶子,擦去泥土,一顿大吃。
第二天一早,吴水才就去派出所门口,继续等赵所长。从天麻麻亮等到太阳当空,赵所长才骑着摩托车回来了。
吴水才知道指望派出所找牛,对赵所长要特别地客气,他先是点头哈腰地叫了声赵所长,接着拿出烟来,散给赵所长吃。可是赵所长根本不理他,他放好摩托车,也不接吴水才的烟,却叫他等着,自己进了屋里。吴水才很听话,站在外面等,又等了个把钟,赵所长捧着一杯茶走了出来,看着吴水才说,你叫么事名字?
吴水才觍着脸说,我叫吴水才,半坡村的,我昨天就来了,我的牛被人偷了。
赵所长喝了口刚泡的浓茶,不看吴水才,却看着路对面的粑摊,喊一声:何脑壳,端两个粑过来。何脑壳应一声,现做了两个粑,用黄纸包着,跑着送了过来。赵所长也不接,转身进去了。何脑壳跟着进去,一会儿空着两手出来,走过吴水才面前,对他使了个眼色。
吴水才赶紧进了派出所,看见赵所长坐在柜台里,正捧着粑在吃。吴水才早就把肠子饿木了,舍不得花钱买粑吃,一直忍着。赵所长吃他的粑,吴水才装作看不见,可是粑的香味儿不管你看不看得见,到处跑,跑到肚子里了,肚子就造反,劲头大得很,搞得吴水才拼命吞口水。
赵所长终于把粑吃完了,用包粑的黄纸擦了擦手,像投球一样把纸扔到角落里,然后拉开抽屉,摸出一个本子和一支笔。
“说吧,报么事案?”
“我的牛被人偷了。”
“我知道你的牛被人偷了,么候儿的事?”
“昨天晚上被偷的,不对,应该是前天晚上,半夜,半夜狗叫得很厉害”。
“么事牛?”
“黄牛。”
“么事颜色?”
“黄色。”
“有么事特征?”
“左边屁股上有朵花,像打碗花。”
“你家的黄牛还金贵,屁股上都长花了。”
吴水才嘿嘿笑,笑了一半就止住了。一天没吃东西,笑得肚子痛。
赵所长说,好了,我已经登记了,你回家等着,等找到了牛我就叫人通知你。
二
吴水才在家里等了十天,没等到赵所长的任何消息。他觉得十天的日子真长,像十年。他每天去牛栏看看,坐在门坎上,盯着空洞洞的牛栏发呆。那把吃剩的草还在那儿,他盯着发黄的草看,他只要看下去,打碗花就会出来,就会伸长舌头把草往嘴里卷去,吴水才甚至能听见牛嚼草的声音,这时候他就会激动地站起来,打碗花就走了,黄黄的牛草还在地上躺着,一根没少。王大娘说吴水才是想打碗花想昏了头,想花了眼。吴水才不这样看,他觉得是打碗花在向他托梦,要他去救它。吴水才离开牛栏刚出来,遇上冬生,他挑着空粪桶从菜地回来。
冬生说,派出所还没信啊?吴水才说,有个屁,我都等了十天了。冬生说,你等十年牛也回不来,你得去找,派出所不管你就找镇里,镇里不管你就找县里,县里不管你就找市里,市里不管你就找省里,省里不管你就找中央。
吴水才一听慌了,说,我还去北京啊,那得多少钱做路费?冬生说,又没让你先去北京,也许你找到县里就把牛找回来了。
吴水才心想这还差不多,县城不太远,就算没有车坐,走个两天也走得到。他心里起了些温暖的感觉,有些感谢冬生,看着冬生挑着粪桶远去的背影,却没有说出来。这些天他可是看了不少白眼,他丢了牛,倒像做了么事见不得人一样,很多人都躲着他。李书记、刘村长、苕四儿,见了他就躲,就像见了瘟神一样。当然这件事也不能尽怪大家,吴水才这些天有些发神经。他天天去看那个空牛栏,有时还对着地上的草说话。大家见了面,打个招呼,问候了吴水才,顺嘴问候一下他的黄牛,找到没有?顺便说说牛的好处,力大呀,草也吃得多,深耕的时候还真少不了它,犁插得多深它都拉得动。这下不得了,吴水才拉住了话头就开始讲他的黄牛,他细女的打碗花。说起来,打碗花跟茶花是同年同月的呢,前后就隔了个两天,像约好了一齐来到这世上。王大娘少奶,茶花吃不饱,天天扯着嗓子叫,硬是把喉咙叫破了。没办法呀,王大娘就挤牛奶喂她,她是跟打碗花吃一样的奶水长大的。茶花几岁就给打碗花驮着满畈里走,她在牛背上睡觉,咯咯地笑,她等于是给打碗花带大的呀。吴水才不提起,大家还真不记得这牛已经十七八岁了,正当年啦,大家就附和几句,感叹几声。叹牛的命,也叹人的命。吴水才话更多了,打碗花就喜欢听茶花笑,茶花一笑起来,它也跟着笑,你们不知道,你们看不出来,我就知道打碗花会笑,它总是在茶花笑的时候跟着她笑。吴水才在说打碗花的时候,完全把它当成了家里的成员,心里充满感情,那感情绝对不比对儿子伯和差。伯和八岁的时候丢过一回,王大娘急得跳脚,他一点也不急。
大家这才觉得吴水才有些不对劲,他讲起牛来就发神经。不能跟他讲牛的事。不讲他都没完没了,要是讲开了,他还不扯到山穷水尽?
最怕见吴水才的是青松。青松天天去具水河拉沙子,要路过镇上,吴水才就天天找青松,让他去打听,青松哪能听他的?去问过一次,结果给赵所长骂了一顿。赵所长说,吴水才糊涂,你青松也不清醒啊?派出所就一个人,哪里有空去给他找牛?你还真以为是《秋菊打官司》,李公安不能给秋菊说法,就去替人家找牛?那是电影。
已经有两三天没人理他了,冬生见了面不仅打了招呼,还替他出主意,可见冬生是个仁义的人。回到家里,吴水才就对王大娘说,冬生人不错,菜地边上那块斜坡地,冬生要种南瓜就让他种吧。王大娘还没表态,吴水才又让王大娘给他烙饼。再找两套换洗衣服,还有,把那床破棉絮也拿出来。王大娘说,你要去哪里?吴水才说,我要去镇里,找派出所,找镇长,如果他们不理我,我就去县里,去省里,去北京。吴水才把冬生的话重复了一遍,好像这话是他自己说的一样,好像他真的要这么做一样。竟然有些扬扬得意理直气壮的气概,有些像戏里唱的那个荆轲,风萧萧兮易水寒。吴水才犹自得意着,王大娘却吓傻了,站在那里不动,这去的地方越来越大,越来越远,一个熟人都没有,自己的男人还背着个烂棉絮,这跟电视里那些上访的人一样了,那些人都是受了天大的冤屈,自己才丢了一头牛,为了一头牛,把自己搞到那么远的地方去,这不是道理。可是在吴水才面前,王大娘从来没有讲道理的时候,看到王大娘在那里发呆,吴水才就火了:娘卖瘟的,你像个木头一样,你还晓不晓得动啊?王大娘赶紧把对男人的担心甩到一边去,走进厨房里烙饼。
吴水才背着烂棉絮到了派出所门口,发现两扇大铁门关得严严实实的,外面的推拉门也拉上了,还挂着一把防盗锁。派出所锁得像银行一样,这让吴水才觉得不正常,他站在门口看了一会儿,就走过马路,走到卖粑的摊子前。他像个熟人似的,笑着对人家打招呼。卖粑的早把他忘了,有些生硬地看着他,停了半晌,指着粑说,要吗?吴水才明白人家不记得他了,就收起干涩的笑,说,我是来派出所报案的,十天前来过,我的牛被偷了。卖粑的似乎有了记忆,啊了一声,说,偷牛?报案?好像是见过你,还没找到?吴水才又挤出一点笑,说,没找到,找到了我就不来了。男人看了看派出所的大门,又看了看吴水才,没有笑,干瘪瘪地说,你来得不是时候。吴水才笑笑,承认来得不是时候,到了吃饭时间,赵所长又去喝喜酒去了。男人说,要是喝喜酒就好了,喝完了就回来了,这回不是喝喜酒,赵所长到县里去了。县里出了大事,棉纺厂的老职工把棉纺厂围了个水泄不通,全县的警力都集中到了县里,维持秩序。
吴水才傻了眼,他背着烂棉絮,调转身,看着派出所两道铁门,目光像一把利剪,要把铁门剪断。可是就算剪开了铁门,他还是见不到赵所长。吴水才可怜巴巴地看着卖粑的男人,低三下四地问,赵所长今天肯定不回来了?男人说,应该不会回来,你看铁门都锁成这样了。吴水才又问,那明天呢?男人说,明天可说不定,得看县里的事处理完了没有。吴水才又问,那后天呢?男人不耐烦了,说,你问我,我问谁去?我又不是公安局长。不耐烦地挥手赶,站一边去,别影响我做生意。吴水才听话地站到一边。站了一会儿,觉得累了,就把烂棉絮放下,找了个干净的地方蹲着。蹲累了,找了块砖头,坐下了。目光有些游离,一会儿看派出所,一会儿看粑摊。中午的生意不错,人来人往,少说卖了三十个粑,吴水才在心里掐算了一下,一个粑赚五毛钱,三五一十五块,这个生意做得。男人闲下来了,从裤袋里摸出烟,抽出一根,点着火,吸了一口,转头看吴水才,吴水才赶紧递上一个笑容。男人却把头扭开了。吴水才知道要买他一个粑才能跟他套话,就从口袋里摸出毛票,凑齐了一块,又拿出两毛,走到男人面前,说,照顾你一下,买个粑。男人有些不屑地看了看吴水才手里的毛票,发现毛票污迹斑斑,沾满了汗水,还少了两毛,就说,一块钱一个。吴水才说,上次你卖我八毛钱一个呢。男人说,是吗?少收了你两毛钱啊,爱要不要。吴水才知道这两毛钱省不了,还指着这个粑套人家的话呢。他把毛票塞进裤袋里,重新摸了一块硬币出来,递给男人。男人收了钱,用一张黄纸把粑包起来,递给吴水才。吴水才吃着粑,看了男人一眼,又看一眼,说,赵所长不回来,我又不能回去,这可真是一件难事啊。男人扫了吴水才一眼,说,你还真以为赵所长能帮你找牛啊?他不过就虚应你一声。吴水才停止咀嚼,有些吃惊地看着男人,说,赵所长答应我了,我都看着他登记了,他还能说话不算数?男人说,赵所长说话几时算过数?吴水才说,赵所长说话不算数,那谁说话算数?周镇长说话算不算数?
男人突然不做声了,还不耐烦地对吴水才挥了挥手,然后就开始收摊子。男人挑着担子走了,他走过吴水才身边时有意地绕了几步。那几步把跟吴水才的距离绕远了,也把人心绕远了。吴水才刚才还把他当半个熟人呢,现在看来陌生得很。
吴水才把烂棉絮都背出来了,不可能就这样背回去,除非他手里牵了一头牛。吴水才要实践他跟王大娘说的话,他必须去找周镇长。
吴水才一到镇政府门口,周镇长就从里面出来了,后面跟着一群人。本来吴水才不认识周镇长,但刚好有人叫周镇长,那人说,周镇长,四中的车来了。周镇长说,好,小张你让司机等一下,周静下来我们就走。吴水才明白他找到周镇长了,周镇长还准备外出,他一出去就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吴水才就有些急,慌慌张张往周镇长面前赶。秘书小张正往外走,看到吴水才背着个烂棉絮往里疾走,他是个聪明人,一把扯住吴水才,问:干什么?吴水才急速行动的步伐被遏止,看着小张说,我找周镇长。小张扯着的手加了力,说,有什么事?吴水才说,我的牛被人偷了。小张这回不只加了力,还往外拉扯,边拉边说,这事找派出所,找周镇长没用。吴水才说,派出所不管,要找周镇长。
别看镇政府没有派出所那样的铁门,小张就是铁门,而且要比派出所的铁门好用得多。周镇长要送女儿去汉口上大学,这是周镇长的大事,怎么能让一头牛给耽误了呢?吴水才尽管是个庄稼把式,但力气却没有小张大,眼看着就被小张拉出了周镇长的视线。吴水才急了,对着周镇长就大喊:周镇长,周镇长。
门口这么大的动静周镇长一直听不见,这会儿不能再听不见了,就往门口看着,说,小张,什么事?小张说,没事,一点小事。小张抓着吴水才的手突然用了十分的力,吴水才觉得腕骨一麻,好像连筋带骨给掐断了,吴水才还没来得及叫唤,耳边响起一个声音,那声音低沉却有金属的质感,像一根铁丝一样刺进了耳鼓。小张说,周镇长有事外出,你的事我来处理。这时,周镇长和一个女学生被一群人簇拥着走出了大门。吴水才眼睁睁地看着周镇长上了小车,小车一溜烟开走了,吴水才感觉他的两个眼珠也给小车生生带走了。小车走了很远,根本就看不见了,那些人还在挥手。
小张终于松开了吴水才,吴水才看了看自己的手腕,感觉它回到了自己身上。小张也在看自己的手,他看看自己的手,再看看吴水才,然后急急忙忙往厕所跑。吴水才以为小张尿急,可是小张并没有进茅厕,他跑到水龙头跟前,在手上打肥皂,冲水,又打肥皂,又冲水。吴水才看明白了,小张是嫌抓过他的手脏。一会儿小张回来了,走到离吴水才三米远的地方,立住,说,你是哪个村的?吴水才说,半坡村的。小张说,找过派出所了?吴水才说,找过了。小张说,那就回去等消息吧。吴水才说,我已经等了十天了。小张说,等十天算什么?又不是一天两天能找到的。吴水才说,我听人说,派出所根本就没去找牛。小张说,派出所又不是开给你一家的,还能天天去给你找牛?吴水才说,赵所长没有天天找,他一天也没找。小张说,你怎么知道赵所长没找,他找了还要向你汇报?吴水才说,我就知道赵所长没有去找。小张说,你还挺自以为是啊,你叫什么名字?吴水才报上大名。小张听了呵呵一笑:水才,舍财,你叫这么个名字,不丢牛才怪呢?吴水才说,你不给我找牛就算了,还拿我的名字开玩笑,我儿子说了,在广东话里,水就是财,从我的名字看,我是要发财的。小张笑得更厉害了,他笑了一阵就说,好啊,你就等着发财吧。小张说完就向前面的楼房走去,一级一级地上台阶。吴水才赶紧跟了上去。小张就停下,扭过身看着他。吴水才在干巴巴的脸上挤出一个笑容,说,小张,你说过,要处理我的事。小张说,我是要处理你的事,但你没有必要上去,你就在下面等着。
吴水才看了看脚下的楼梯,看了看大院,明白有些地方他能去,有些地方他不能去,就转身走回大院里,走到院西一棵梓树下面,等着。吴水才眼瞅着太阳从当空向西落去,大院里的阳光像一块布,给人一剪刀一剪刀地剪没了。这期间他把王大娘烙的饼拿出来,吃了一个。王大娘烙的饼有些老,噎得吴水才直翻白眼,吴水才一开始还忍着,后来就在心里骂王大娘的祖宗十八代。好在王大娘离得远,要是在脚边,他肯定一脚踢了过去,踢她一个四仰八叉。娘卖瘟的臭婆娘,明明知道没水喝,还把饼烙得这么硬,存心不让老子吃。
吴水才把又硬又老的烙饼吃了两块,还没等到小张下来,却等来了刘村长。刘村长站在大院正中,一眼瞅见了坐在梓树下的吴水才。他风风火火地走过来,一把扯起吴水才,说,狗日的,丢人丢到镇政府来了,跟我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