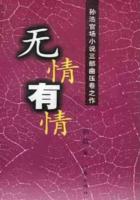吃过早饭,男犯们在场院上放风。裘双喜和傅明德嘀咕了一通后,把小痦子叫到跟前。鲁震山坐在不远处的一个石滚子上看着三个人。
傅明德问:“老实说,你到底是什么人?”
傅明德又问:“你进来之前到底是干什么的?”
裘双喜掂了掂手里的一块尖石头:“你不说实话,我要了你的狗命!”
小痦子蔑视地打量着两人,懒懒地说:“有种你就杀了我吧,我早不想活了。”
裘双喜举起石头:“我看你真是不想活了!”
鲁震山咳嗽了一声,裘双喜一扭头,侯仲文居然不知何时站在了旁边。
裘双喜忙将石头藏到身后,傅明德笑笑:“报告政府,我们就是随便聊聊……”
侯仲文看着裘双喜,突然伸手从裘双喜背在身后的手上夺过那块尖石头:“我看你才是不想活了!”说完,把石头扔到一旁。
小痦子哭丧着脸说:“报告政府,姓裘的一天到晚欺负我,还想要我的命!政府可要为我做主啊。”
“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侯仲文盯看了小痦子一眼,走开了。
侯仲文早就注意上小痦子了。早晨男犯们排队打饭的时候,一个男犯手里拿着三个馒头与小痦子一错身,一个馒头便落到了小痦子手里,男犯并没发觉。小痦子刚要将馒头往嘴里送,一只手一把扯住小痦子的胳膊。小痦子一回头,面前站着的正是侯仲文。
小痦子赔着笑脸,递上馒头:“大队长,我错了……”
侯仲文打量着小痦子,突然扯开小痦子的衣扣,盯着小痦子的肩头看了看:“你以前……不是小偷!”
小痦子点头哈腰:“对,对,我就偷过那一回,以前我都是好人……”
侯仲文逼视着小痦子:“进来之前,你是干什么的?”
“打鱼,摸虾,拉车,卖小工,扛大个,只要能挣钱,啥活我都干。”
“你当过兵吧?”
“就是没当过兵。”
侯仲文指着小痦子的左肩:“这肩膀上的茧子呢?”
“这……这是扛大个磨的。”
“是扛枪磨的!”
“我长这么大,从来就没摸过枪,我一看见枪就害怕……”
侯仲文突然抽出手枪,“啪”的一声,拍到小痦子手上。小痦子吓得一趔趄,枪掉在地上,他忙又捡起来,毕恭毕敬地还给侯仲文。
小痦子也是憷了侯仲文,一天两次这么盯着自己,他的心里也有点发毛:“鲁大哥,这姓侯的怎么就专盯上我了?”
“那是你小子心虚。他对谁都是一副捉摸不透的表情。”鲁震山目光游移地四下看着,与傅明德的眼神对了个正着。傅明德像过了电一般,忙转过头去。
从进了江滨北校场监狱开始,傅明德便注意到了鲁震山看自己的眼神,他的眼神像是随时都在探寻自己心里的秘密。在知道这个人居然打过台儿庄之后,傅明德更是感到心虚得厉害。和这样的人囚于一室,他不能躲开这个七尺汉子的躯体,只能躲开他犀利的眼神。
小痦子早就看出傅明德怕鲁震山,所以他就转弯抹角、想方设法地讨好鲁震山。鲁震山身上的军人豪气,似乎也让他从骨子里就把保护显得弱小的小痦子当成了分内的事情。
小痦子问鲁震山:“傅坛主老躲着你,是不是就因为你说他去过台儿庄?”
“他一直说没去过。别看他留起了大胡子……我觉得,他就是我认识的一个督战官。”
小痦子好奇地问:“督战官是多大的官?”
“我们迟师长是中将,对他都毕恭毕敬的,他不是官职高,就是来头大。”
“他不承认,你没证据,这事不好办哪。要是弄错了,你非但立不了功减不了刑,政府没准还要治你个诬陷罪哪。”
“我觉得你这话是向着他说的。”鲁震山盯着小痦子。
“哪呀,我这不是为你好吗?我知道你想早点减刑出去,可一旦说错了,再来个罪加一等,那不太倒霉啦!”
鲁震山琢磨着小痦子的话,他想不明白小痦子是在帮自己还是在帮傅明德。
回到临时监舍,傅明德还是没有放过小痦子:“有大队长的亲自关照,感觉如何呀?”
小痦子不想理傅明德,刚要躲开,却吃了裘双喜一拳头:“妈的,这些日子把你宠坏了!傅坛主问话你还敢不回了!”
小痦子举了举手铐,没好气地说:“这个都戴上了,你说我能感觉怎么样?”
傅明德态度好了些:“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没跟侯大队长交代明白,他才抓着你不放?”
“交代什么?我倒想把咱们和总指挥商量逃跑的事交代出去,争取立个功!”
裘双喜举手要打小痦子,小痦子忙喊鲁震山:“鲁大哥!”
倚在墙根的鲁震山像是睡着了,一直闭着眼。小痦子忙窜到他身边。
刘前进和彭浩昨天晚上就内鬼的事扯到下半夜两点多,非但没有理出个头绪,反倒脑子更乱了。一大早,两人又把文捷喊了来。刘前进开诚布公地说:“哪个人有啥疑点,涉及谁,咱们三个敞开说。文捷,你先谈谈周圆吧。”
文捷想了想:“周圆倒是有机会利用电台与外界联络,但她不负责编码和译电,不知道电报的内容。老龙口事件之后,支队长也考查过她,没发现什么问题。再说,她也没参加老龙口粮站的布防会议。所以说,内鬼可能另有其人,而且是能接触布防机密的人。”
刘前进看着彭浩:“我和老侯上了山,你带张连长他们在寨口布防,这两件事怎么会走漏了呢?”
彭浩说:“如果内鬼稍加留心的话,这两件事都不难知道。”
刘前进说:“我问过老班长,关假货郎之前,已经对他全身上下搜了个遍,他身上不可能藏有锯子之类的工具。”
彭浩说:“假货郎锯断窗上的栅栏,应该也是内鬼给他提供的工具。”
文捷说:“写这个密信的人,放走假货郎的人……还有后来,可能让假货郎传信给唐、宁那些匪徒,让他们赶紧撤走的,会不会是同一个人……”
刘前进连连点头:“有道理。假货郎的事,老龙口的事,还有卧云寺的事,这几件事要连起来考虑。接触老龙口布防方案的人群是重点怀疑对象,我们要重新进行排查。排查的范围要扩大,不要只查地方来的干部,部队来的干部也要查。”
文捷欲言又止的态度让刘前进看到了:“你想说什么?”
文捷看一眼彭浩:“我想说……排查,也包括支队领导吗?”
刘前进说:“怎么会提这个问题?”
文捷说:“布防方案,是你和政委两个人商定的……”
彭浩、刘前进神情各异。
关晓渝在知道刘前进和侯仲文回来的当天晚上,就想去看看侯仲文。可看到周圆急三火四去见刘前进的样子,她虽然忍住了,心里却对周圆羡慕得不行。不过,第二天下午她还是找了个借口见到了侯仲文。两人在寨口的山坡上慢慢走着,很是惬意。
侯仲文说:“跟支队长走这一趟,我可真是见识到了什么是共产党人的勇敢机智。”
“你也不差呀,我听周圆说,你当时可勇敢了。”
“跟支队长比,我可没有他的身手,老啦,不行了!”
“你才多大啊?就敢说老了。”
“在咱们一支队,除了老班长,就属我的年龄大了。”
“年龄大,我可以称你为兄长,叫你老大哥啊。”关晓渝仰脸看着侯仲文。侯仲文觉得有些不自然。
关晓渝说:“有件事,你答应过我还没做呢……”
“什么事?”
“你自己说过的,忘了?”
侯仲文想了一会儿,一拍脑袋:“噢,是吹笛子的事吧?”
“你还记得啊……”
“有机会一定兑现……”
“现在就有机会—”关晓渝从怀里抽出笛子,“我可早就给你准备好了。”
侯仲文愣了下,接过笛子看了看,横在嘴上,几个单音过后,一曲柔曼又略带感伤的旋律随即吹出。关晓渝打着节拍轻轻唱起来:“一条小路,曲曲弯弯细又长……”
侯仲文边吹边看着关晓渝,两人不时用眼神交流着……
一曲吹完,两个人都沉默着,关晓渝低着头,脸上泛出片片红晕。
侯仲文轻声问:“你的笛子……是跟你父亲学的吧?”
关晓渝很觉惊诧:“你怎么知道?”
“看你的眼神我就知道,你父亲一定经常在你面前吹笛子……”
关晓渝看着侯仲文,良久。
侯仲文轻轻地拉起关晓渝的手,往前走去:“你父母……”
“都不在了。”
“怎么……”
“他们都是地下党员,在重庆一次群众集会上被国民党特务杀害了。”
侯仲文叹了口气,两人默默走着。走了一段路,侯仲文说:“晓渝,今后,我会像父亲那样照顾你的。”
关晓渝抬起头:“不……我不希望你做我的父辈……”
“我,我先走了。”侯仲文有些慌乱,刚迈出一只脚,关晓渝突然一把抱住侯仲文的腰,脸贴在这个男人宽阔的后背上。
过了一会儿,侯仲文悄声说:“冷静点,晓渝,有人来了。”
关晓渝不情愿地松开他,转身跑去……
寨子外边的一大片油菜花,在过午的阳光下,腾起一大片梦幻般的、令人心向往之的灿烂。
湖中清波荡漾。一叶扁舟靠在木板房附近,木板房的窗里有幽幽的光透出。一支鱼竿从窗里伸出,垂在湖中。
宁嘉禾手持渔竿坐在窗前,眼睛盯着湖中。
唐静茵坐在旁边,望着波光粼粼的湖面:“瓦扎头人不把你当回事,刘前进他们就要押着人过鸡冠岭了,你还有这种闲情逸致。”
宁嘉禾仍专注地看着渔竿前的浮漂,像是没有听见唐静茵的话。
“他们就要过鸡冠岭了,我怕瓦扎头人顶不住。咱们得想想办法。”
“办法该想当然要想,不过,不让他们过鸡冠岭不太容易啊。好在去新锦屏的路还远着哪,还是要从长计议。”
“你—”唐静茵有些恼火,“也太长刘前进的威风了吧。我唐静茵也不是吃素的!”
宁嘉禾扫了唐静茵一眼,又继续看着渔竿上的浮漂:“我给你讲讲劳改部队的事,你听了,没有坏处,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嘛。你千万不可小瞧了他们那几个人,刘前进虽是一介武夫,可这个人还真是十分了得。”
“你又危言耸听!蹲了一回共党的班房,他就把你的胆子摘走了?”
宁嘉禾一摔渔竿:“放肆!”
一阵静默。
起风了,湖水拍岸,涛声传来。
宁嘉禾关上窗户,苦口婆心地说:“静茵,你这样轻敌是要吃大亏的!你根本就不了解你的对手是些什么样的人!”
唐静茵起身,气呼呼冲出了屋子,宁嘉禾无奈地摇了摇头。
现在,一直萦绕在周圆心里的两件事总让她坐卧不安,一件是她太想知道甄世成到底是不是自己的“上线”。另一件是她和刘前进的感情现在几乎停滞不前了。刘前进对自己的忽冷忽热,让她难以判断对方是不是真的喜欢自己。按照最早的设计,她是受命要用美色迷惑住刘前进继而才有所动作的。所以在许多场合她才故意做出颇为大胆的举动,想让刘前进早点“中招”。可不知不觉中,她竟然真的慢慢喜欢上了这个动不动就对自己粗门大嗓的男人来了。很多时候,她也弄不清自己究竟是在执行所谓的命令还是为了自己的“私情”才去接受刘前进的。眼下的刘前进显然不能有太多精力跟自己谈情说爱,她便通过种种渠道想了解更多有关刘前进的“前世今生”。借着来找老班长领军需品的机会,她央求老班长多讲讲刘前进:“我想给支队长写篇文章,他过去的事也想了解一下。”
老班长高兴了:“那可是好多年前的事了。支队长一参军就在我的班上。那时候,他才这么高……”老班长比画了一下,“一个娃娃兵。不过,别看那时候他人小,也淘,可鬼精得很,在部队上谁都喜欢,正派、机智、仗义、勇敢……这些好话儿,放在他身上都不过分。”说起刘前进在战斗中的故事,老班长更是滔滔不绝,周圆也听得情醉神迷。
“前进年纪轻轻就当上了团长……同志们都敬重他,喜欢他。对了,那个程部长,更是喜欢得不得了!”
“对呀,我也喜欢支队长!”周圆脱口而出。
老班长愣了一下:“你喜欢……支队长?”
周圆突然显出些紧张来。
“周干事,你今年多大了?”
“我……不小了,过了年就22了……”
老班长沉吟着。
“老班长……有什么问题吗?我可是认真的!”
关晓渝推门进来:“什么事啊小周,叫你这么认真?老班长,支队长让我喊你去他那儿开个会。马上。”
周圆站起来,看看关晓渝,又看看老班长,有些慌乱地跑去。
会还没开,刚从外面买粮回来的甄世成在向刘前进汇报情况:“……通司(即“翻译”)带着我们跑遍了方圆几十里,一粒粮食也没弄到。”
刘前进问:“那个瓦扎头人同意为我们筹粮的,怎么会说变就变了?”
“彝人们说,别说没粮,就是有,他们也不敢卖。”
刘前进思忖有顷:“现有的粮食还能维持多久?”
“省着点吃,顶多够两天的。”
刘前进琢磨着:“敌人打粮站那回,主要就是想声东击西救出宁嘉禾,烧掉的粮食怎么会那么多呢?”
甄世成说:“那火一着起来,还能少烧了?那粮食多干燥呀。”
刘前进点点头,从窗户里看到文捷和侯仲文进了院子,就站起身,说:“一会儿这个会你也参加一下,粮食的事,你最有发言权。”
会上,最先发言的是刘前进:“鸡冠岭瓦扎那边,有了些变故。唐、宁匪帮正对他们施压,逼走了瓦扎的彝兵,换上了他们的人,号称鸡冠岭成了他们游击军的地盘。”
侯仲文一听火了:“这个瓦扎怎么能言而无信!支队长,我再跑一趟官寨,去当面问问他!”
刘前进朝侯仲文抬了下手:“没有用!现在谁去官寨都解决不了问题。再说,瓦扎这时候还不知道在不在鸡冠岭哪。”
彭浩说:“我和支队长研究了一下,唐静茵、宁嘉禾说服不了瓦扎和他们同流合污,又调动不了大小官寨的人马,只能靠他们自己极其有限的那帮残匪蹦跶蹦跶。不过,他们不熟悉岭上岭下的地形地貌,虽然放出话来说什么要占住鸡冠岭,打我们的阻击,但是,他们未必真敢倾其所有跟我们决一死战。”
刘前进站起来:“就算姓唐的匪婆子发了疯,可那个宁嘉禾对我们的实力还是知道一点的。再说,他们十分清楚,解放军在大西南的剿匪斗争正愁不能把他们弄到一起聚而歼之哪,他们会轻易把他们那点儿人、那点枪都拢到鸡冠岭上吗?”
众人点头。
刘前进接着说:“还有,我们也得准备打一家伙。我这一路上可是被这些坏蛋东一下西一下撩得满肚子火气,正想好好撒一撒—当然,要打也要有准备地去打,请机动部队过来,一起打!一举剿灭他们!”
侯仲文舒了口气:“按支队长和彭政委说的,唐静茵、宁嘉禾他们就是虚张声势而已了。”
刘前进说:“老侯,我倒不希望他们只是个‘而已’,我们要准备打仗。可是打仗得让战士们吃饱饭啊!现在,缺粮是个大问题。”刘前进的目光落在老班长和甄世成身上。
“我们……一直在想办法哪。”甄世成看看老班长。
“光想不行啊,得有结果。”彭浩说,“照目前的情况来看,全支队的伙食标准还要再减一减,不过,这不是个办法。”
“不能再减了。”刘前进说,“这几天的伙食标准已经减了不少,再减,还怎么打仗,战斗力也要有保证啊!”
“现在粮食有限,伙食标准不降也不大可能。”侯仲文小心翼翼地说。
甄世成说:“那当然。我倒是不想降,可这粮得有啊……”
“什么叫‘那当然’!你还有理了?”刘前进瞪着甄世成,话里有了火药味。“一缺粮你就降伙食标准,那我要你这个后勤科长干什么?”
“甄科长,话是这么说,办法你还得想。这边哪,我们也想了个办法。支队长不同意再降伙食标准也是有考虑的。”彭浩拿出一封信,“这是给地方政府写的信,请他们尽快支援粮食;同时,把鸡冠岭的事也跟他们通报了一下,需要兵力的话,还得请他们助我们一臂之力。”
刘前进说:“如果大家同意这个办法,就得赶快派个人去,同时把粮食带回来。”
“打个电报不就行了吗?何必还得派人去送?”文捷不解。
“咱们的发报机坏了,一直没修好。行了,散会吧。”刘前进起身。
“那叫谁去呢?”彭浩问。
刘前进斟酌了下:“小李去吧。没人能比这个闷葫芦更踏实了。”
“支队长,发报机坏了可得赶快想办法,那可是咱们的鼻子、耳朵和眼睛呀。”文捷焦急地说。
“我知道,正想办法呢。”刘前进出了屋子。
“彭政委,这事得快点解决呀。”文捷又嘱咐彭浩。
彭浩顿了下,说:“行,我催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