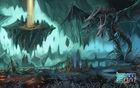入了秋,草原上白昼日减,虽已过了辰时,别云峰前仍是漆黑一片,只有那天际微微有些泛白,起了雾,有些风,挂着露珠的青草地上,一双双铁足踏碎了秋日清晨的宁静。
一声号角从那弥漫着的白雾中传出,肃杀而悲怆,接着便是一阵鼓点,起先只是是缓慢的敲击,点点滴滴有些断续,接着鼓声就变得愈发急促起来,犹如一碗黄豆落入滚烫的油锅。
细密的鼓点伴随着浓雾中透出的整齐的脚步声,一切都开始变得紧张起来,战事将启,北风寒,天空中飞过一只晚归的寒鸦伴着它凄厉的嘶鸣。
忽然,天亮了,天边那朦胧的地平线上正缓缓升起一轮红日,将那些云霞染得通红,朝阳如血,天下殇。
一阵寒风吹过,云开雾散,露出了梁军的军阵,一座三丈高台映入眼帘,那人一身戎装,着坚甲,披红袍,英姿飒爽,正是擂鼓号令全军的陈盼盼,只见她面前一支牛皮鼓,身后半盏金钲,头上扎着的红巾在风中飘舞,手中鼓槌不停击打着鼓面,清脆而又雄浑的鼓声向着远方传去。
十五万北凉府兵组成了一座大阵,似一副开合的棋局,一半黑,一半白,相互交织却又泾渭分明,向着远处那片弥漫着血雾的突厥大营缓慢前行。
太阳已经完全越过了山岗,武成峰身上披着的是那件略显陈旧的金甲,骑着的是匹高头大马,身后千骑护卫,整齐排列在高台之下。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眼中的杀意渐盛,一颔首,一道令旗便向台上递去,只听得“咚咚咚”三声鼓起,十五万大军齐声呐喊,响彻天地。
梁军的军阵早已排列整齐,军势强横,而对面那处大营中仍是悄无声息,一如既往。
“那些突厥番子不会是逃了吧。”陆先生领黑衣军在前,主持着阵势的开合,只见他盘膝坐在那辆双辕大车上,头戴斗笠,却没了以往的那些云淡风轻,举目眺望着远处那没有半分动静的血雾,喃喃说道:“若那血屠城真的跑了,可就真的有意思了。”
“将军,要冲一番试试么?”身旁,一位裨将上前问道。
“不许,一切都按那高台军令行事,还有和你说了多上次了,别叫我将军,在下只是乡野间的一位修行者,无官无职,叫我陆先生就好。”不让喊将军,却要叫先生,陆先生这几句话看似平凡,却无处不透着骄傲霸气,然而他却好像没有察觉到这点一般,只是摇了下脑袋眼睛依旧盯着前方,没有半分松懈。
那裨将低头退下,脸上生起一丝讥笑,心中暗道:“不让我叫你将军,却要我喊先生,这是把战场当学堂么,难怪人们常说,修行者脾气古怪,如今看来这果然不假。”
裨将的笑容自然逃不过陆先生的眼睛,他自然不会跟这人解释些什么,只是觉得当年父母给自己取的这个名字实在太过招摇,心中不由得多了几分别样的情绪。
时间拖得久了些,梁军的杀气则被压抑的更久,作为这次战役中的主力部队,他们早就听闻了玉门关被围的消息,却只能和敌军对峙在别云峰下,虽说那杀意被北凉府兵那严明的纪律性压制下来,但昨日从关内传来的大捷的消息终于还是引燃了这积压已久的战意,士兵需要用杀戮来宣泄,一如宝刀渴望着鲜血。
“北凉府兵精,再这么拖下去恐怕于我军不利”阿史那颉利与血屠城并肩站在土坡上,突厥大营中,那些狼骑已披挂整齐,却迟迟没有进攻,自然是因为血屠城的命令。
“只要能胜,这些士兵的死活又与我何干,战场上死得人越多,我便越强大,这血雾大阵便更加难破,时间拖久些,我便能立于不败之地。”
“死的人与你无关,却是我突厥的子民,自然也将成为我的子民。”阿史那颉利脸有愠色,却没有把话说破,只是在心中暗自说道,望着对面梁军的阵势,忽然觉得有些奇特,心中便生出些许不安来,于是问道:“梁军这是什么阵仗,国师大人可曾见过。”
血屠城似乎没有看到颉利脸上的那丝怒意,抬起头随意望了一眼,目光便再也无法从那黑白分明的军阵中移开,眼中精光闪动,这是他第一次正视敌手,却发现几日不见,这敌手已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对手,平静之中生出些许兴奋,苍白的脸上笑得残忍,双唇微张,露出洁白的牙齿以及那鲜红的舌头。
原本想这次敌人不过是些未曾破境的大修行者,没曾想尽然就这样与那人的阵意相遇,那座在少年时得到的血碑自有真意,其中记载的阵法更是惊险雄奇,虽说论武学血屠城不敢自称天下无敌,但若是论阵法他却有争夺者当世第一的勇气,直到许多年前,那位棋圣在南面破境。
“棋山棋圣黑白子,黑白棋法天下一,他的阵法,分阴阳,一乾坤,奇时如羚羊挂角踪迹难寻,正时如滔滔大河气势磅礴,今日一见,果然不凡。”血屠城望着那阵法,如同在观赏一件艺术品。
“国师可有破阵的手段?”见血屠城如此评价,阿史那颉利的心便一沉,有些不安的问道。
“他之所以能稳居第一,是因为他和我未曾较量过”血屠城的脸上写着轻蔑,心中却有些不安,突破修行者境界的人物于天地心生感应,除非黑白子的境界远高于他,不然他便能有所感应,然而他却没有察觉。
如此种种,只能说明一件事,主阵的并非黑白子,而是另有其人,从那排兵布阵中的些许瑕疵中不难看出,这阵法大概是那棋圣的门徒所设,若是如此,那黑白子亲自布的阵法又该是何等声势,血屠城不敢去想,亦不愿去想。
“时间差不多了”血屠城一边说一边盘膝坐下,闭上眼说道:“我主阵时你为我护法。”
突厥大营上的血雾开始随着血屠城席地坐下而开始慢慢收敛,单薄的雾气一点点凝聚在了那些突厥狼骑身上,露出了那多日不见的营地。
大营周围的那些木栏早已被拆除,营帐也都已消失不见,只剩下那些狼骑,黑压压的一片层层叠叠看不见尽头。
狼骑摆出的阵仗有些奇特,非丁非甲乾不合坤不一,既没有奇门遁甲的玄奇也没有寻常军阵的肃杀,只是将那些身上泛着血光的狼骑杂乱地排列着,但若仔细看去似乎有点真意。
“终于露了面,却没想是这般模样。”武成峰身旁一名家将轻声说道。
“这阵法有些不一般,血屠城并非虚名之辈,摆出这般乱阵必有深意。”
“将军,你就下令吧,今天终于可以和突厥番子好好干上一丈了。”
武成峰没有说话,只听得高台上传来三点鼓声,接着便是一阵号角长鸣,心道:“还是娘子与我心有灵犀。”
随着雄浑的鼓声远远传开,黑白大阵开始运转,排在前排的黑衣步卒向两侧分开,露出后面身披白袍的骑兵。
高台上,陈盼盼并没有看透突厥人摆出阵法中的玄机,但好在这已是在战场,既然看不破那便杀破,于是便指挥骑兵突击,去杀破这血阵的虚实,这个想法与台下武成峰的思路不谋而合,想到自己竟如一莽汉般没有一点风度,陈盼盼脸微微一红,暗道自从嫁了这么个粗人,自己的品味倒是降了不少。
在梁军开始突击的同时,突厥人亦发起了冲锋,骑手浑身泛着血光,胯下坐骑戴着巨狼头骨制成的头盔,显得格外狰狞恐怖。
伴随着细密的鼓点,两军人马撞在了一起,交锋处泛起阵阵血浪,如倾泻的暴雨,那红色的血光似乎并没有给突厥狼骑什么增幅,只是每当有骑手身死坠马之际,那些血光都会变得明亮几分。
黑白棋法甚是玄奇,黑棋是静主开合,需要陆先生坐镇牛斗位,而白旗不定主进退,那冲虚位更是时刻而变,所以这阵法对于“那个人”并没有太多的限制,他只需身负那有些奇怪的石子,便能牢牢把握着战局的走势。
“那个人”混于乱军之中已有了段时间,他不骑马不披甲,一身青衫速度却快的惊人,手中绿光时现,每道绿光都能带走一个突厥狼骑的性命。
渐渐,两军阵前堆起了一座尸山,双方都拼出了真火,杀意与戾气在战场上空凝聚,血光更盛。
“噗”的一声,“那个人”手下再添一缕亡魂,血溅到了他的脸上流过他的唇角,他舔了舔,有些腥,有些臭,有些酸,有些甜,心中猛地生出几番躁意,似乎有一种对对鲜血与杀戮的渴望正在蔓延。
突然,怀中那块石子发出了一丝凉意,直袭天台灵明,“那跟人”便惊醒过来,看着四周,只见几个梁军明明已把那突厥狼骑斩于马下,却仍要纵马踏上几个来回,将那尸体踩成肉泥,另一边,一个失了战马的突厥人一枪将梁军从马上掀了下来,却仍然要再补上一枪将那战马也刺个通透,两军战士似乎都已入了魔障。
若要破障,便得放下屠刀,而在这两军阵前又有谁能做到。
血屠城这血阵竟然是两败俱伤的打发,这让“那个人”有些始料未及,正在焦虑之时,却听得风中传来了陈盼盼的声音。
那声音清脆嘹亮用的是凉州边塞的曲调,之所以说是曲调,是因为她在唱曲。
从未有人在战场上唱过曲,一来这战场太过嘈杂歌声难以入耳,二来这的确有些不合时宜,但陈盼盼的曲调却入了每个将士的心魂,因为这曲声如春风化雨却又铿锵有力。
她唱的是《破阵曲》解的是众人心中的戾气。
“长弓引箭控不发,甲光照面枪如林,一片鼓声连角起,四下犬马起唏嘘,君可见,天山脚下,何处有那枯骨裹红衣。
萧萧北风冻旗柱,大漠黄沙日生烟,可汗点兵攻朔漠,金戈铁马卫戍边,且听我,别云峰前,一曲长歌把敌破阵前。
举目望山,巍巍昆仑,壮我将士胆。碧海狼烟,大好山河,岂容他人陷。
好男儿,自当提携玉龙,雕龙文卷,屠狗功名,岂是平生真意。
大丈夫,应该上阵杀敌,入凌烟阁,做万人敌,方得青云之志。”
曲罢梁军将士眼前皆是一明,心中戾气顿减,士气却又旺盛了几分,而在远处的山坡上,血屠城缓缓睁开了眼,嘴角上扬,变作一条弧线。
“有些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