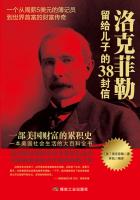每天吃过晚饭后,杏儿总是先把妈妈拉到沙发上,再把爸爸也请过来。杏儿就坐在妈妈和爸爸的中间,咯咯地笑着。
然后,游戏开始——妈妈和爸爸中的一个人用手从后面捂住杏儿的眼睛,让她猜是谁。
杏儿每次都能猜对,因为这个游戏做了无数次,杏儿能感觉到妈妈和爸爸双手的不同。
游戏开始,一只手从后面捂住了杏儿的眼睛。妈妈说:“好了,杏儿,猜吧。”杏儿咯咯地笑着,说:“是爸爸。”
妈妈笑着问:“你怎么知道是爸爸?”
杏儿说:“爸爸的手有劲儿。”
妈妈说:“那当然了,爸爸天天在井下挖煤,就像杏儿在院子里挖小洞洞一样,手没劲儿能行吗?”
第二天,游戏又开始了,一只手又从后面捂住了杏儿的眼睛。
妈妈说:“好了,杏儿,猜吧。”
杏儿照例咯咯地笑着,说:“是爸爸。”
妈妈问:“你怎么知道是爸爸?”
杏儿说:“爸爸的手凉。”
妈妈说:“那当然了,爸爸整天在井下,那儿本来就很潮湿。今天井下又有一处小塌方,渗出了好多好多的水,就像杏儿前几天挖的小洞洞被水泡塌了一样。爸爸把情况反映给了矿主,就是那个管着你爸爸的人,可他说没什么大事,照常开工。就这样,爸爸在水里泡了好几个小时,手能不凉吗?”
第三天,游戏照常开始,又是一只手从后面捂住了杏儿的眼睛。
还是妈妈说:“好了,杏儿,猜吧。”
这回,杏儿没有笑,反而撅着小嘴小声地说:“是爸爸。”
妈妈问:“怎么了,杏儿,为什么不高兴?你不是最喜欢玩这个游戏的吗?”
杏儿抬起头,眨着那双漂亮的眼睛看着妈妈,委屈地说:“爸爸,爸爸又没气了,他的手又软了。”
顿了顿,杏儿慢吞吞地接着说:“妈妈,我不玩了,人家的爸爸都不用充气,为什么我的爸爸老是要充气呀……”杏儿边说边指着放在沙发上那个能充气的塑料“爸爸”呜呜地哭了起来。
杏儿一哭,妈妈的眼圈也红了。但是,她没有掉出眼泪,因为她的眼泪早在3年前就都流光了:她永远也忘不了那个让她一辈子都刻骨铭心的夜晚,忘不了丈夫在冰冷的水里浸泡了五天五夜的身体,忘不了那个黑心的矿主……那段时间,她整天以泪洗面,也曾经想到要陪丈夫一起走。但是,当她看着身边整天咯咯笑的杏儿,还是毅然抹干眼角的泪水,从心底里告诉自己要坚强……杏儿一天天长大,整天缠着她问这问那,也非要跟别的小朋友一样和妈妈爸爸一起玩猜猜看的游戏。这着实让她犯了难,看着挂在墙上已经有些发黄的丈夫的遗像,她再次把泪水咽到了肚子里。
冥思苦想,她终于想出了一个主意——第二天,她家的沙发上就多了一个能充气的塑料假人。
此后,她和塑料假人一起跟杏儿玩游戏,杏儿别提多高兴了,手舞足蹈地说自己也有爸爸了,也能跟爸爸一起玩游戏了……
“妈妈,为什么我的爸爸老是要充气?”杏儿摇着妈妈的手天真地问道。
妈妈打了一个激灵,杏儿的话把她从回忆中唤回来。她看了看身边满脸委屈的杏儿,蹲下来,用微颤的双手小心翼翼地擦去杏儿脸上的泪痕,然后,轻轻地抚摸着杏儿的头,像是自言自语地说着:“杏儿,好孩子,别哭了,爸爸肯定是累坏了……”
可是,杏儿根本不听,还是不依不饶地哭闹着。
妈妈实在没办法,因为她确实不知道该如何回答杏儿的问题。
这时,她突然瞥到身边的一个气球,于是,妈妈急忙说:“杏儿,别哭了,我能让爸爸飞起来!
杏儿止住哭,眨着一双红红的眼睛好奇地问:“真的吗,爸爸真能飞起来?”
妈妈点了点头,说:“好孩子,快睡觉,等明天你睡醒了就能看到。”
杏儿半信半疑地点着头,睡觉去了。
第二天,杏儿醒得很早,刚睁开眼,就问妈妈:“妈妈,爸爸飞起来了吗?”
妈妈朝杏儿笑着,然后,用手指着屋顶。杏儿顺着妈妈手指的方向看去:“咦?爸爸真的正在屋顶上摇头晃脑地飞着。”
杏儿终于又咯咯地笑了,高兴地嚷着:“哦,小朋友的爸爸都不能飞,只有我的爸爸能飞,爸爸飞得好高呀……”
一旁的妈妈看着开心的杏儿,摇了摇头,无奈地苦笑着,因为只有她知道“爸爸”能飞的秘密:昨晚等杏儿睡熟后,她走街串巷好不容易找了个卖气球的人,给塑料假人充了2元钱的氢气……
拥有一个会飞的爸爸很了不起!虽然他不能为孩子遮风挡雨、消除病症,但是他却给孩子带来了最坚实的心理后盾。一个父亲肩负着很多责任,除了为孩子树立起一座山,还要为孩子指出前进的方向。而“父亲”两个字,本身就是一种能让孩子安全与幸福的字眼儿。父爱,就是厚重的踏实,温暖的陪伴。
父亲头上的草末
父亲头顶草末到学校找我时的身影在我心灵深处,令我永远无法忘怀。
父亲是个农民,识不得几个字,一辈子靠耕田种地为生,从未出过远门,甚至连去县城的次数都极为有限。他和母亲在家乡那“旱了收蚂蚱,涝了收蛤蟆”的盐碱地上辛苦地劳作着,用心血和汗水养育着我们兄弟五个。哥哥姐姐们长大成家后一个个远走他乡,读高中的我便成了父母心中最大的希望。
1994年,我不负众望,考进了黑龙江大学,成为我们村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走出去的大学生。可是,我上大学的第二年,久病缠身的母亲便离开了我们。看着四壁空空的家和不时登门的债主,父亲郑重地对我说:“孩子,安心上你的学,别瞎寻思家里的事儿,我就是砸锅卖铁也要把你供完。”
回到学校,我省去了早餐,每天午晚两餐也只吃两个馒头和五毛一份的咸菜,掰着手指头计算着怎么省钱。可就在我省吃俭用挨过了大半个学期后,一场大病突然降临到我的头上。半个月后,虽然在同学们的精心照顾和全力帮助下我恢复了健康,可大家垫付的医药费加上借来的钱却压得我喘不过气来。在试过了一切可以想到的办法寻求帮助无效后,我第一次流着泪水给父亲寄出了要钱的信。
两周后的中午,我下课刚刚回到宿舍,门一响,一个衣着寒酸的人推门走了进来。
“爸?”来人竟是父亲,我顿时愣在了那儿。
“哎呀,你们学校可真大,找你真不容易。咋样?病全好了吗?”父亲说着摘下了头上戴的狗皮帽子。我清楚地看到,父亲的头上竟然沾满了草末。
父亲仔仔细细地看着我,最后放心地点了点头:“好,好了就好。”说着解开棉袄,把手伸进怀里,掏出了一个已辨不出颜色的手绢包。
“这一段凑钱不太容易,晚了些。这是3000元,快还给你那些同学吧。”父亲说着,眼里流露出一种异样的神色。
3000元?我不由得一愣:“哪儿来的这么多钱?”
父亲干咳了一声:“还能是哪儿来的?借呗,贷呗。啥也没人命金贵呀!孩子,咱家的情况你也知道,这钱你可要节在(方言,节省的意思)着花呀!”
我捧着这带着父亲体温的3000元,含着泪点了点头,说:“爸,你放心吧。”
父亲简单地吃过了我从食堂打回的午饭后准备回家。走到门口,他犹豫了一下转过身来:“孩子,从省城到咱家挺远的,来回坐车也得花不少钱,过年……你就别回家了。”
我心一震,皱着眉点了点头,把父亲送出校门便匆匆赶去上课。不知为什么,那一夜我没有睡着。
转眼间到了寒假,在同寝弟兄的坚持下,我登上了回家的客车。从省城到县城,又倒车颠簸了近百里,掌灯时分,我才来到了家门口。
推开家门,我愣了:新刷的雪白的墙壁,一应俱全的家具,高档的电器……住在这里的人告诉我,在我生病那段期间,父亲已经把这房子卖给她了。
“什么?”仿佛一声惊雷,我差点儿没坐到地上,“卖……卖给你了?那……那我爸……我爸呢?”
“他给别人看草垛去了,就住在20里外的野草甸子上。”
我不知道是怎么从“家”里走出来的,一出门,泪水一下涌了出来。我发疯般哭喊着,向着村外的野草甸子上奔去。
也不知跑了多长时间,山一样的草垛立在眼前。在草垛边上,一个半露于地面、上面盖满了草的地窨(yin)子静静地卧在凄冷的月光下。掀起棉布门帘,苍老的父亲正一个人孤单单地守在地锅前,锅底红红的火焰映照着他头上数不清的草末。
“爸——”我哭着叫出了声,一下子跪倒在父亲的面前。
父亲一愣,看清是我,急忙把我拉了起来:“快起来,回来了也好,吃饭了没有?”
那一夜,父亲只字未提卖房的事儿,只是絮絮叨叨地说了一宿的母亲,而我则整整淌了一宿的眼泪。
刚过十五,我便告别父亲准备回学校。父亲抖着手从怀里掏出那个手绢,打开,里面十块、五块、两块、一块的零钱,加起来竟然有一百块:“孩子,这是他们给我的看草垛的钱,你拿去。”
我的眼泪围着眼圈直转:“爸,上回那钱还有呢,这个你留着吧。”
父亲一瞪眼:“净瞎说,那钱还了账,估计早没了。我在家里好对付,你在学校处处都要用钱。爹只能给你这些了。拿着,孩子,就差半年了,不管咋样都要把书念完。”
我的眼泪刷地流了下来,点着头接过了钱:“爸,你多保重,我走了。”趁父亲没注意,我把一部分钱塞在了褥子底下,转身爬出了地窨子。
在自己勤工俭学和朋友们的帮助下,我终于完成了最后一个学期的学业。毕业后,我没有任何犹豫,回到了生我养我的家乡。
如今,父亲和回到家乡的哥哥一家生活在一起,我也时常回家看望父亲。父亲常常对我说:“不用回来得那么勤。我身体好好的,又有你哥嫂照顾,你好好上你的班就行了。”
我经常含笑点头答应,可事后依然常回家看看。每当静下来时,父亲那沾满草末的形象便出现在我的眼前。我清楚,父亲的行动和身影已经深深地刻进了我的脑海,必将影响我的一生……
父亲头上的草末,就像那段贫穷的岁月,我们无法省略,也不能无视它的存在。好在,无论贫穷还是富有,我们和父亲都在努力。房子没了还能挣回来——只要亲情在,人定能胜天。父母的大爱如此深重,相信会激励每一个有心的儿女努力前行。
父亲的爱里有片海
我从海边回到“金海岸”小屋的时候,已经是下午5点多钟。我是从海边回来的最后一拨人,其实昨天我就可以回来的,要不是为了多拍几张“海韵”图片,回去让我的还没见过海的学生们开开眼,我才不会在这海边多待一会儿呢。从前天开始,广播、电视、报纸等各媒体就发布消息,大后天将会有台风登陆。昨天就有大部分游玩的人返回了市区,今天只剩下少量游人,而且所有剩下的游人都手忙脚乱地在“金海岸”小屋收拾着行李,准备马上离开。
“金海岸”小屋是个前后左右上下六面都用厚铁皮包成的小屋子,只在朝海的那面开了个小门。这也许是经历风暴者对小屋的最佳设计吧。小屋里有些简单的生活设施,可以供人们将就着用。这小屋挺有特色,前天我还专门为它拍了几张特写照片呢。这小屋离海边最近,到海边游玩的人们常在这儿歇会儿脚。说它最近,其实走到海边也是要一个多小时的。
天,总是阴沉着脸,像随时要发怒似的。要不是“金海岸”的小老板响着一台收音机,这“金海岸”早就没有了一丝活力。要在旅游旺季,“金海岸”屋里屋外人山人海,比繁华的市区也毫不逊色。
“这铁板做成的‘金海岸’也不是金海岸了,大家快收拾东西去市中心,躲进结实的宾馆里去吧。”那小老板不停地大声叫着。
人们各顾各收拾着东西,少有人说话。我的东西很少,早已收拾停当。忽然,我看见两个人,估计是父子二人,父亲有40岁的样子,儿子不过10来岁。父子俩一动不动,孩子无力地倚在大人身边。父亲提着个纸袋子,好像只有条毛巾和一个瓶子。可是,他们一点也不惊慌,仿佛明天就要到来的台风与他们毫无关系。
“父子俩吧?”我走过去,搭了搭腔,那父亲模样的人点了点头,算是回答。
“收拾收拾,我们一起走吧。”我是耐不住寂寞的一个人,又说。
父子俩没有作声,40岁的父亲对我笑了笑,却没有回答。我想他们是对我有一种戒备心理吧。
“您说,明天真的有台风?”一会儿,那位父亲盯着我问。我重重地点了点头。他的脸上爬上了失望的神色。
还有一个多小时公共汽车才来接我们回市区,人们都拿出准备好的食物来对付早已咕咕叫的肚子。我也拿出了我的食物,一只全鸡,一袋饼干,两罐啤酒。
“一起吃吧。”我对他们两人说。
“不了。吃过了。”那父亲说,说着扬了扬他那纸袋子里的瓶子。是一瓶榨菜,吃得还有一小半。
我开始吃鸡腿,那父亲转过头去看远处的人们,儿子的喉结却开始上下动着,吞咽唾沫。我这才仔细地看了看孩子,瘦,瘦得皮包骨头一样,偎在父亲身旁,远看倒像是只猴子。我知道孩子肯定是饿了,撕下一只鸡腿,递给了孩子。父亲忙转过脸来对我说了声谢谢,我又递过一只鸡翅给那父亲,父亲这才不好意思地接在手里。等到儿子吃完了鸡腿,父亲又将鸡翅递给儿子。儿子没有说话,接过鸡翅往父亲嘴里送。父亲舔了下,算是吃了一口,儿子这才放心地去吃。
我忙又递给孩子父亲几块饼干,说:“吃吧,不吃身体会垮掉的。”父亲这才把饼干放进嘴里,满怀感激地看着我,开口了,又问:“您说,明天真的会有台风?”
“是呀,从前天开始,广播、电视和报纸就在说,你不知道?”我说。父亲不再做声了,脸上失望的阴云更浓了。
“你不想返回去了?”我问。
父亲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还怎么能回去呀?”他的眼角,有几颗清泪溢出。
“怎么了?”
“孩子最喜欢海,孩子要看海呀。”他拭去了眼角的泪。生怕我看见似的。
“这有什么问题,以后还可以来的。”我安慰说。
“您不知道,”父亲对我说,“这孩子今年16岁了,看上去只有10岁吧?他就是10岁那年检查出来得了白血病的,已经6年了。前两年我和他妈妈还可以四处借钱为他化疗,维持孩子的生命。可是,一个乡下人,又有多大的来路呢,该借的地方都借了,再也借不到钱了,只能让孩子就这样拖着。前年,他妈妈说出去打工挣钱为他治疗,可到现在却没有了下落。孩子就这样跟着我,我和他都知道,我们在一起的时日不会很长了。孩子就对我说,爸,我想去看看大海。父子的心是相连的。我感觉,孩子也就是这两天会离开我了,我卖掉家里的最后一点东西,凑了点路费,坐火车来到这座城市,又到了这海边小屋子,眼看就能看到海,满足孩子的心愿了,可是,可是……”父亲哭了起来,低沉的声音。
“不管怎么样,还是先返回去再说吧。”我劝道。
“不,我一定要让孩子看到海。”父亲坚定地说。
接游客的汽车来了,游人们争着上了汽车。我忙着去拉父子俩。父亲口里连声说着谢谢,却紧紧搂着儿子,一动不动。但是我不得不走了。我递给那父亲300元钱后,在汽车开动的刹那我也上了汽车。因为我想也许还有一班车,他们还能坐那班车返回。到了市区,我问起司机,司机说这就是最后一班车了。我后悔了,真该强迫父子俩上车返回的。但又想起父亲脸上的神情,我想那也是徒劳。给了300元钱,似乎心安理得了些,但那300元钱对于他们又有什么用呢?
当晚,我在宾馆的房间里坐卧不安,看着电视,我唯有祈祷:明天的风暴迟些来吧。
然而,水火总是无情的。第二天,风暴如期而至,听着房间外呼啸的风声,夹杂着树木的倒地声。我心里冷得厉害,总是惦着那父子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