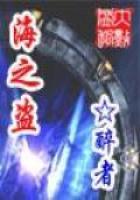香港又一次回到了人们视线的中心。
很多不怀好意的人心里明白,这个城市将很快成为舆论的是非地。他们盼望太阳西去,盼望天黑、盼望新的一天。哲人曾说岁月匆匆,人们应该把握当下。然而,他们这些人今天可不这样想,因为,他们等的就是好戏开场。这其中不乏有社会名流、政客。对于名流总得借此显摆自己的学术素养,得发表些真知灼见的见解。而政客嘛,特别是在野党,他们已经准备好对执政党的批评。如果政府不干预这件事情,他们会说执政党软弱无能、一无是处。如果政府干预这件事,那么他们会说这是对民主、自由的破坏。总之,在香港,在野党与执政党之间公开的找对方的茬亦然习以为常,以博取香港市民的支持。
教授被安排在港科大贵宾接待室休息,过了一会,服务生端上了午餐,一盅西红柿炖牛腩,一碗红烧肉,一盘香油拌苦瓜,还上了一盘清炒三丝,一小碗米饭,服务生将一果盘摆在了饭桌的最右边,最后服务生倒了一杯红酒,离开走出了房间。教授看着窗外的大海,心想这真是喝红酒的好时光。他看见一轮船从远处缓缓驶来,后面跟着一个快艇,快艇一加速,一闪而过。
时下,他想起了去年夏天在美国加尼福尼亚海滩冲浪的情景,他邀请了他的黑女佣一家,女主人叫艾米娜,而男主人叫卡利维,他们有一个十三岁的儿子,就在家附近的中学读书。他们在那里玩了整整一天,晚上,他们听着海浪拍打海滩的声音,在帐篷里喝着红酒。小卡利维在节能白织灯下,读了一会小说,又吃了些火鸡肉,独自在自己的帐篷里睡着了。艾米娜起身去换了件白色的长裙,赤脚在沙滩为他们独舞,她笨拙的扭着屁股,用力的摇晃身体。兴许是由于酒精的作用,她浮夸的作出几乎荒淫的表情,一对**房不停在胸前晃来晃去。卡利维与教授在帐篷里笑到不行,卡利维指着艾米娜,用中文问教授带不带劲,教授苦笑的点了点头。他们又喝了几杯,在夏夜星空下的凉风中微醺睡去。凌晨时分,酒精慢慢失去了原有的效力,教授听见隔壁的帐篷里传来艾米娜哇哇的呼叫声,另外有一个男人喘着粗气,不停的怒吼着。几分钟后,它们就被一波又一波涌来的潮汐声给彻底淹没了......
教授看着窗外,看着轮船驶过后空旷的海面,自己乐了起来。他想,在卡利维眼里艾米娜一定是一块可口的黑巧克力。此刻,他不得不再次回想起,艾米娜用不太流利的中文冲他叫‘老爷’的下午,那是她来教授美国家的第二个年头的周六,当时的艾米娜正在家附近的中文培训学校学中文,算起来她已经连续学了三年中文。她早晨早早地做好早餐摆放在餐桌上,在干净的玻璃杯上倒满热牛奶,给园子里的花浇水,给一群鸟伙伴换水换食,最后给它们倒去头一天的鸟粪。然后她穿过门前的草地,打开木栅栏门,赶去听早上9点钟的中文课。中文学校是一位美国华人夫妇所开,原本是CD人。不知道为何,美国这个国家突然出现了中文热,势头一点不比当年中国人必须学英语来的差劲。
几天前,艾米娜不知道在哪里弄来一本描写中国上世纪初的当代小说。其中有丫鬟叫男主人的老爷的对白,艾米娜看后牢记于心。周六下午,她早早的做好了晚餐,就去书房叫教授吃晚饭。
“老爷,老爷,吃饭了”
教授坐在中国制的摇椅上,看着书。点了点头,突然感觉不太对味,这之前,艾米娜有时候说“教授,吃饭了”,有时候会说“开饭了”,虽然发音不准确,但是总算能听明白意思。对于今天,教授硬是听成了“老也,老也,吃饭了”
于是教授下楼,他们就开始像两个孩子一般在“老爷”与“老也”之间纠缠不清,最终,艾米娜气急败坏冲进自己的卧室,找来一支上课作笔记的原子笔,重重的在笔记本上写了两个大大的汉子,然后又匆忙地拿给教授看。教授看着歪歪斜斜两大字,苦笑不得,又哈哈大笑起来。
教授此刻独自一人靠着凳子上哈哈笑了起来,他拾起果盘里一颗葡萄放入嘴里,一阵酸甜。
他隐约听见自己的肚子在咕咕作响,于是他用筷子将周围几个盘子的菜都夹了遍,喝了几口红酒,又吃了几小口米饭。唯独没有碰那碗红烧肉,有几次,他已经将红肉夹了起来,然后,又慢慢放下了,内心一阵天人交战。
“吃吧,吃吧,不就是一块红肉”
“不行,脂肪对肌肉百害无益”
“看起来,这红肉也没有什么油脂了”
“贪吃虫,多吃苦瓜吧”
教授想起了多年来,健身教练一直要求他尽量不要吃肥肉的忠告。可是,突然,他想起了接来下还有一场,甚至两场、三场硬仗要打。于是,如同顽皮的孩子,他直起身来,将六块红肉全部吃了下去,不仅如此,他又将其它盘子、盅子里的菜吃了个精光,完后,他又喝光了杯子里所有的红酒,除了米饭剩下不少外,其它算是一扫而光。至于果盘里的水果嘛,有两根香蕉、切好的一个四等分苹果,还有酸甜的葡萄,他扫了一眼,选择了放弃。
他清楚,对比上午的演讲,明天的记者会才是艰苦时刻,甚至在某一秒,他在心里询问自己是否取消记者会呢。他想,这又到了该补充、储备能量的时候了。
而大厅内,珊妮待人群都走光了以后,这才慢慢步出大厅,本来她想找一找男人婆,结果男人婆没有一个人影,仿佛人间蒸发一般。突然,在走廊前面,她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跟在一个男人的身后。于是珊妮一阵小跑,尾随而去。她,看见他们一前一后走进了校长办公室。
门虚掩着。
“那么,你说,你为何这样做”
对方默不作声。
“你这样做,你知道别人会怎么看”
对方仍不默不作声,看起来采取的是软抵抗。
男人无可奈何的坐在校长椅子上,“你说话啊”
“我看这事情,不偷不抢不违法,顶多就是帮助同学”对方终于第一次发声。
“你真是轻描淡写,不知轻重”
“违法吗”对方开始主动回击。
“是,不违法”男人在校长椅子上站了起来,面对窗外的海边。“可是它可耻”男人板着脸,转过半边脸重重地说。在男人看来一个人如果拥属、占用本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起码是不道德的、是可耻的。
她流下眼泪,她告诉他,如果自己的母亲还在世,他不会这样教训她。她觉得眼前这个男人,她的父亲是小题大作,他的父亲第一次在道德上给她判了死刑。
房间内,一个男人,重重的瘫软在沙发上。门外,珊妮看见一个身影跑了出来。
“男人婆”她惊呼道,然后又紧紧把自己的嘴巴给堵上了。
珊妮在刚打开的房门就要关上的一瞬间,看见校长不停的用手紧紧抱着自己大脑,泪花湿润了双眼,好像想起了最悲痛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