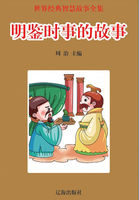在采集山果的季节里,人们最易得到的莫过于山里红。山道旁,沟塘边,随处可见。
诱人的酸甜连成一片红霞,成熟的羞红会使你忘记它那带刺的语言……东北人对它都有个印象,吃的人也很多,可谁把它当做水果,甚至没人知道它在植物界里的学名,只能沿用那山民对它不加修饰的概括--山里红。
小时候,因为生活在城里,虽能在街口付两分钱享用一碗儿那迷人的酸甜,却从未见过它的母体。
片片红果,铺天盖地。把身上的小口袋装得鼓鼓的,跨出梦乡,依然只是两分钱一碗的残红……说来也巧,我和几个儿时的伙伴真的插队到了山区,偏偏又是在收获的季节。
淳厚的山里人,短粗的手掌落在我们那挎过书包的肩头。一句句幼稚的提问,淹没在一阵阵善意的嘲笑里。于是,大捧大捧的山里红已堆放在我们的行李边,煤油灯跳动着光亮,故事在吱吱的旱烟锅里燃烧。山村的第一夜,便把我们埋到了“山里红”的梦中--清晨,挎着竹篮的山妹便成了我们几个的排头。山路上,那红底白花的身影似跳动的音符,掩映在绿色的苍茫里。而我们则被拉成了省略号,点缀在坎坷中。
果香冲淡了我们的疲惫,串串层层的红果实使我们相信了故事的真实。丰盈的树下,拥起了迫不及待的手臂。“哎哟!”颤动的枝条告知了我们应互相尊重。
那是一个难忘的时节,丰硕的山果满足了我们儿时的憧憬,也把我们沉醉在现实中……第二年的春天,山里红的树身不知躲到哪儿去了。绿海茫茫,降低了我们那本来就不很明确的分辨率。后悔第一次的接触,只忘情于私欲里而没能留意那母体的丰姿。
热情的山妹满足了我们的好奇,这大概就是我们第一次见到的山里红的母亲。鲜绿的枝叶,托起轻泛细碎的小白花,在微风里抖着清香。丑陋的树干,植根在贫瘠的岩缝间,榆柳桑槐的排挤,并没有憔悴它的姿容,枝上的针刺,体现着它与自然抗争的能力。
光阴荏苒,离开山村已经20多年了,然而,每到秋天,我还是忘不了买上几斤山里红来咀嚼那酸甜微香的童年,和那远山的呼唤……在清柔的月光下,说吧,说吧,轻柔的风会把你无人知晓的爱悄悄地捎到我的心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