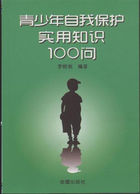我不是在看守所里见到的耿信阳,而是在一个风景区里的疗养中心见到的。当然那个地方表面看起来是个疗养中心,但实际上招待的却是和耿信阳一样的人,我想周晓婷大概也来过这儿吧。
那个在我印象里儒雅且意气风发的人已荡然无存,两鬓斑白、面颊消瘦,但精神还不错,只是从前那样有神的眼睛已经收敛了所有的精芒,余剩平静。就在我来看他之前,我手机上收到了一条当地推送的新闻,标题是《耿信阳正在接受调查,其第二任妻子因涉案太深已自杀》。人常说“盖棺定论”,看来盖了棺也未必定论,只是想想我妈身前和身后的污名也实在是让我无话可讲。
我坐在耿信阳面前胡思乱想发呆是因为我实在不知道要从何说起。他终于还是先开口了,他说:“岑波的日子定了吧?”我以为他会先问耿赫的情况,唯独没有想到他会问岑波,我愣了一下点点头。耿信阳好像松了一口气,平淡地说:“岑波,始终是你的定时炸弹,他走了对你、对他都是好事。你身边的牛鬼蛇神都被清扫干净以后,就好好生活。”
我有种莫名其妙的感觉,但耿信阳却温和一笑,说:“经历了那么多,你把自己养得很好,你妈会放心的。”我还是淡淡地打断了他的话:“耿赫脱离生命危险了,剩下的要看他自己的求生意志,另外我给你请了律师。”听到律师二字我看到他眼神里闪出一丝异样,接着他沉思了一会儿说:“律师也只是走个程序,该担的事情还得担着,所以不用浪费太多的精力,只要这个律师和我接触过以后能条理清晰的表述事实就行,其他的不重要。我手上沾的不过是铜臭气,没沾过血,所以未来不过是没了自由,更何况我也不冤,咎由自取而已。”
听着他平静地安排接下去的事情,我竟然生出了一种刮目相看的感觉。我以为再见他的时候,他会落魄,会精神不济甚至会因为害怕露出胆怯,那样我会发泄一下多年心里憋屈的情绪,至少要鄙视一下,哪怕是用眼神。但我的算盘落空了,他就那样安静的和我说话:”很庆幸你妈对你的不闻不问,时至今日才没有拖累你,也许她早就料到了今天。以后,耿赫需要托付给你了,对他、对你我都不是一个尽责的父亲和继父,我心里能装下的只有你妈和我的野心,到头来也不过是一场春秋大梦。”
那天大概是耿信阳有生以来跟我说话最多的一次,平平静静、普普通通的对话,没什么情绪波澜,没什么起伏,真的很像一对多年未见的父女徐徐而谈。
我忽然记起我妈在日记中曾经这样写道:我对他一直都有很深刻的印象,他一身的英气总让我想到正义凛然,他对我浅笑,让我觉得他是在戏弄我,但偶尔也总有心痒痒的感觉,我想我必须远离他。但耿信阳还是飞蛾扑火般的走向我,我再次失去了理智。我一再试探他的底线,试探这个为了我不停地让步、牺牲的人到底有多爱我,事实证明他的确可以无条件的爱我。甚至容忍我只是变态的想作弄他,甚至容忍我一再地把他推上绝路,其实我何苦要这么做呢,我只是不甘心,不甘心就这样死去,我单纯的想拉一个心甘情愿为我垫背的,很不巧耿信阳就是那个心甘情愿的。
那一刻我想的是:吴惠珍的确很变态。
我终于没忍住,问耿信阳遇到我妈后悔吗?他认真思考了一会儿,回答我:“说不后悔是假的。第一次见到你妈的时候我就应该把她放在心上,但我却抵不住权利的诱惑。如果我能等到你妈大学毕业,现在我们也儿孙满堂了,也就不会有什么赵顶天,岑大胜,自然也不会有赵沐阳、岑波、耿赫,还有你;如果不是我执着于仕途,也不会有那么多的因果关系,也不会误了我们害了你们。“
门突然被打开,有人进来了,我知道这表示我们会面的时间到了。他说:”你回去吧,我的事情律师跟进就行,你好好解决你自己的事。耿赫如果醒不过来,你就把他送到康复院去,所需要的费用我会让赵沐阳想办法,你处理好岑波的后事也算你和你妈与岑家俩清了。“
耿信阳站起来的时候,我才忽然发现他佝偻着腰,我诧异地看着他,他说:“没事,腰坐久了会直不起来,老毛病了。”我点点头说了句保重,耿信阳回头对我说:“事情了了以后,你找个喜欢的人,嫁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