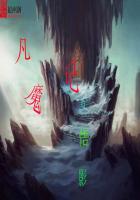龙远东道:“军师之议,诚然甚佳。然则以我所见,敌军极其擅长游击,并不以一城一地之得失为意。他们打得过就会打,打不过就会走。等我们停下来,他们又来骚扰。而我们追击,又不免陷入他的口袋。大胜固然未必常有,而小胜也是相当难得。更或许一年到头,我们跟在他们屁股后面打了几百个圈圈,不仅什么战果也没捞到,还平白损失无数兄弟。”
张佩冷笑道:“依你说来,我们岂非必败无疑?莫非你被五行宗伏击了一次,就怕了他们?敌人所依仗者,不过是七十级魂师比我们多而已。倘若我军组织三千名精锐刺客,十人为一组,分撒出去,专以刺杀敌人高级军官为己任,一年下来,总能杀死掉千把个,到时候,敌强我弱之局面,必然改观!”
禾大力拍桌道:“说得好!龙铁铲,我发现你胆子是越来越小了!仗还没开打,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的。行不行,总要试过才知道吧?老张这个刺杀的主意委实不错,我第一个报名当刺客!”
龙远东不以为意,淡淡一笑。
刺杀,的确是一种风险与机遇并存的活动。侥幸一次成功,便可能带来难以估量的好处。如果你一心一意只是想刺杀一两个人,持续冒险之下,或许当真可以办到,哪怕目标有十个、八个,那也无妨。但是倘若你想要在壁垒森严的万军丛中,一口气刺杀一两千名七十级以上的高手,却无异于痴人说梦!
如果刺杀如此有用,世间的仗又怎么打得起来?
再说,为了刺杀敌人一个,却需自损一百,甚至更多,投入回报完全不成比例,即便最后成功了,又有何意义?
所以刺杀这种事情,只可能发生在少部分关键人物身上。不成功则已,一成功,就能改变战局!
这些道理显而易见,稍微想想就能明白,龙远东有理由相信,张佩与禾大力一样,都是说的一时气话。
禾小朵压了压手,道:“各抒己见,何必动怒?这刺杀之策,可容后再议。”
在禾小朵主持下,众将又先后提了十几个大同小异的计策。
比如有人建议,与沦陷区的府军里应外合,兵贵神速,出其不意,将敌人分割包围,然后放大吃小,打几个歼灭战,再以点及面,逐步求取全面胜利;
也有人说,调一支优势兵力,直插舒州、海州府军中间地带,打通两州府之间的通路,将三地连成一线,然后相互声援,张网结阵,就近一个县一个县地清剿收复,扎扎实实巩固根基,慢慢扩大战果,最后创造条件,分部和敌人决战;
更有人提议,秘密派遣细作潜入敌人内部,离间九宫阁与五行宗两大势力的关系,以便从中收取渔翁之利,等等。
但不管什么计策出来,总有人找到其中的弊端和破绽。要么是异想天开,实际非人力所能办到;要么是剑走偏锋,冒险突进,胜负全靠运气;要么是保守求稳,一味强调蓄势待发,伤不了敌人的元气。
总之大家想得越深,主意出得越多,越感到形势棘手,不容乐观。
众人商议良久,未有善策,士气渐沮,都闷声不语。
一直在旁认真倾听的云天甲忽然道:“讨论了这么久,大家似乎对剿敌的前景颇觉灰心。但以我之见,只要我们应对得法,敌人必败无疑。”
“哦?此话怎讲?”禾小朵精神一振,追问道。
“理由有三:
第一,天下大势,在于民心。民心所向,即为大势所趋。民心思安,则乱不能久;民心思和,则战不能续。
虽然现在民众生活维艰,苟延残喘,但他们只要能够有口饭吃,勉强活得下去,便都不愿意抛家舍业,铤而走险,犯上作乱。尽管我朝政治素有积弊,官吏陋习太多,毕竟还有挽救的余地,而这恰恰就是我们的取胜之机。只要我们能够妥善安抚好民众,广施德政,敌人就翻不了天。”
禾小朵欣然赞道:“云帅所言,甚合我意!”
其余将领有点头同意的,也有些颇不以为然。尤其像文砚心、李高澹等人,浸淫政治越久,越知道变革时政的难处。
空谈谁都会,具体落实起来,谈何容易!
不过,禾小朵既然表了态,他们老于城府,自然不会当面拆台。
云天甲继续道:“第二,敌人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强大。我们知道,敌军的特点是擅长游击战、伏击战,作战灵活,神出鬼没,这既是他们的优点,也是他们的弱点。
就我所知,敌军虽然举旗造反,却并没有深入人心的统一宗旨,每到一个地方,首先就是杀官放火,抢钱抢粮,有时候明明占了县城,把钱、粮、人都搬空后,又退入山林之中;也并没有长远的规划,打起仗来,毫无方向和目的,哪里弱就往哪里打,打到哪里算哪里。
因此,他们在打攻坚战和阵地战的时候,往往缺乏必胜的信念,一遇挫折,就军心动摇,四散撤退,另找出路。敌人造反至今,除湖州一地外,其余各州的府城依然掌握在我们手中,便是明证。
他们就像一个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壮汉,喜爱随心所欲,不愿迎难而上,这种人表面上看去力大无穷,其实甚好对付。”
禾小朵喜道:“说得好!”
文砚心若有所思,右手抚须,微微点头。
“第三,我们的军力虽然不强,但也并没有我们以为的那么不堪。
首先,我们的真实兵力,并不比敌军少,相反还要多很多。因为并非只有那三万多的机动兵力才可以投入战斗。如果将中部五府的府军、郡兵、县卒、乡勇都加起来,又再算上沦陷区各州府的兵力,这就已经超过六十万众。其外我们还可以招募佣兵、驯兽师、炼器师、矿工、山民、猎户等等民间力量为我所用。这又起码可以凑出五万人。
其次,我们各个部队,尤其是三大驻军,长期卡在三阶巅峰、六阶巅峰大关的魂师不在少数,如果我们能够提供充足丹药辅助冲关,又给予合理的集训,用不了几个月,他们就能更上层楼。在兵员数量不变的情况下,所有单兵的战斗力整体往上提一个台阶,那么军队的战斗力亦将有质的飞跃。
最后,五大边关之中,除了与中明帝国接壤的怀远关外,其余四关的兵力完全可以自由调动。所以,我们现有的机动兵力,不是三万,而是五万!”
李高澹道:“云前帅所言,在下有两点不明。
第一,冲关丹药,向来奇缺,可以说有价无市。一则血晶石、血灵石出产本来就少,二则优秀的炼丹师更是稀有。如果我们能弄到充足的冲关丹药,早就分发下去了,何至于让将士们长久卡在三阶巅峰、六阶巅峰不能突破?
第二,边关军扼守国门要冲,乃国家根本之所系,非同小可,自古以来,从未听闻有抽调边关军剿匪的先例,所谓的‘边关军可以自由调动’,不知从何谈起?”
云天甲微微一笑,道:“冲关丹药一事,我已经有了解决的眉目,快则三月,慢则半年,我必让前线战士人人都可以分到相应的丹药。”
李高澹惊道:“此事当真?”
“绝无虚言!”云天甲胸有成竹。
李高澹本来还想挤兑他立军令状,又想他是前线主帅,如果弄不到丹药,便打不赢仗,到头来终究免不了一死,立不立军令状都一个样。当下冷然一笑,不再言语。
云天甲顿了一顿,道:“之所以说边关军可自由调动,是因为与东木国接壤的四个边关,根本不用守。”
代忠惑然道:“边关不守,外军趁虚而入,岂不糟糕?”
其余众将也都露出不解的表情,范晔、柳逸尘、李高澹三人幸灾乐祸,嘿然而笑。
云天甲道:“东部四关可以不守,理由有四。
第一,东木国的主要发展方向在海外,没有动机来打我们。
第二,东木国乃我土浩帝国之铁杆盟友,在边境上对我们几乎不做防备,连国关都不常设。他既然没防备我们,对我们自然也没有什么野心。
第三,退一步讲,万一东木国来打我们,以我们东部四关的兵力,恐怕也挡不太住。既然挡不住,还有什么守的必要?而且,东木国军队一旦进入我境,首当其冲的也是五行宗、九宫阁的匪军,而我们完全有时间来调兵遣将,从容应对。
第四,我们不守国关,那么匪军在我们步步进逼之下,便有可能向东木国流窜,到时候需要头痛的不是我们,而是东木国。所以他们不但不会来进攻我们,反而会来帮我们。只要我们派出特使,告知东木国国主,必然可以说服他们调遣精兵强将,替我们守关。如此一来,我们就等于一举多了几万、十几万的强援,敌我兵力对比,将彻底逆转。”
李高澹哼道:“说得简单。人心叵测,东木国到底是会趁火打劫,还是会雪中送炭,谁也打不了包票。不要搞到后来,我们前门驱狼,后门进虎,那可就麻烦大了。”
柳逸尘附和道:“云前帅所言,句句在理。但是国关大防,绝对不可掉以轻心。我看撤守国关之事,还是从长计议。”
李、柳二人开了头,文砚心、范晔、张佩、船一帆等人,也纷纷表示了各种各样的忧虑和担心。
禾小朵见满厅上下,一片嗡嗡,心中不忿,解下腰上佩剑,决然道:“非常之时,行非常之事!我即命云天甲为前帅,一切军事大权,当尽归帅府。此佩剑乃我信物,今日交予云天甲执掌。自今而后,军机大事,全凭云天甲一言而决,不必公议。有不服从者,执此剑,行先斩后奏之权!”
众将悚然一惊。
如此恩宠,令人既羡且妒。
云天甲心中亦是一凛:“公主竟然对我如此信任!”半跪于地,双手接过镶金嵌玉的华美短剑,郑重道:“末将定然不负公主所托,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转身对众将道:“剿敌之事,我心中已有方略。三日之后,请大家移驾前帅府,领取作战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