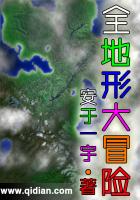天色近晚,夕阳已经仿佛挂在了西面山顶那棵最高的天杨树的枝头,流天和陈弋龙已经回到了走马村。在与回家途中遇到的大伯大婶们寒暄之后,流天打开了自家石屋的木门,映入眼帘的依旧是空无一人的屋子和冷锅冷灶。流天转身关上木门,径直走向了旁边不远处陈家的石屋,很自然地开门进了里屋,却见一个穿青衣的男人正在石灶边准备晚饭。男人那本来略显冷漠的眼神似乎也有了一丝回转,他看着流天说道:“回来了,来加把柴火。”流天一边说道:“好的,风叔”,一边直接坐到了灶前烧起火来。这一切都显得那么地自然,仿佛本就该如此一般。
吃过晚饭,流天收拾起了桌碗,而这个叫陈风的男人则坐到了堂屋,摆弄起了一小段木头。
陈风来到走马村已经有九年了。这个石屋本来的主人陈二在几年前声称到郡府去做工,然后就再没回来过,而陈风则一直住在这里,靠着不错的木工手艺过活着。流天从小便常到这个略显木讷的男人家里玩耍,晚了便吃完饭再回家。刘半天回家晚了见不到流天也不用担心,因为他很快便会见到自己儿子从陈风家的石屋里走回家,几年来始终如此。
刘半天今天下午到了距郡府较近的几个村子里去收购了一些粮种,当然回来的路上又喝了一点小酒,回来得稍晚了一些。回到自家石屋后,叫了两声流天也没人回应,刘半天则径直到自己的木床上躺下睡了。过来良久,流天才回到家,见到了床上已经睡着的父亲。他走到床前,给刘半天拉了拉泛黄的棉被,没有回到自己的小屋,却是提着小木凳走到了屋外的空地上坐着发起呆来。
流天今年已经九岁过半了,本应该是充满稚气、无忧无虑才对,可是流天却发现,自己总有着不同于其他小孩的想法。他的“想法”很不合常理,因为他自己深深地明白,自己比同龄的孩童要老成太多!自己做事情总是能够思前想后,甚至权衡利弊,可这本不该是一个不满十岁的小孩子应该有的吧!透过村民的眼神和只言片语,流天知道自己其实是刘半天捡来的,可自己怎么就这般与众不同呢,难道自己和这些平日里生活在一起的人们不是一个族类?流天总是在暗自回避这这个很可能是正确的问题。
流天记得在自己六岁的时候,刘半天咬着牙花了一大笔银两请了一个在郡府学堂教过书的先生来教授自己识数写字,自己只花了几天便知晓了所有的课业。可是自己却不想让别人都知道自己是个异类,硬是装作不成器的呆童,气走了那个满脸皱纹的老头子。自己的记忆力超出常人,能记得刚会走路时候开始的所有事情,而且从没有生过病。这所有的一切并没有让流天觉得欣喜,反而让他苦恼无比,因为他并不想要与周围的人显得那么格格不入。
流天望了望身后的石屋,轻叹了一声,不禁想起了那个老学究曾提过的一句典故:“凡超群者,任重也,道远也!”
“我可能就算是超群者吧,可我并不想要这样啊。我现在每天都过得很快乐,我很喜欢周围的人们,也不想要改变这一切。可是……”
“管它那么多呢!我现在就这个年龄,就要做现在应该做的事情!什么狗屁任重道远,我就要去抓蝉烤鱼,明天我还要去烤一条大蛇呢!”流天恶狠狠地想着,似乎突然变得轻松无比。
良久之后,流天回到了自己的小屋。他躺在了木床上,却是翻覆着难以入睡眠。
今晚的月亮圆如玉盘,皎白的月光透过了小窗,照到了流天的小屋里。流天看到了那个挂在墙上的小花篮。月光洒落在花篮上,在凹凸不平的墙面上映出了弯曲的黑影。他起身摘下了花篮,捧着花篮躺了下来,却不禁想起了那个外表木讷的风叔。
风叔曾问过流天:“你记恨你的亲生父母吗?”
那个看似木讷的男人却似乎早就看穿了流天的心思。
“我不知道!若是见到他们,我不知道自己会怎么样的!”流天自言自语道,与以前自己回答这个问题是一样的答案。
捧着花篮的流天徐徐睡去,似乎在睡梦中与这花篮又融为了一体,正如当初自己在天河之中漂流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