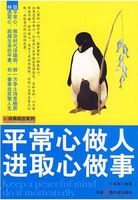春天总是很短暂,一眨眼的功夫就过去了。
灿烂金黄的天空下浮凸着前方楼房的轮廓,太阳能的电池板反射出刺目的白光。外面看上去一片迷蒙,空气中飘散着梧桐飞絮。
母亲从大红塑料盆里取出扭成筋骨的衣服,抖开来挂上衣架,水珠沿着衣襟滴滴沥沥。她的动作不利索,直起腰时停顿了一下。她几乎不使用身侧那台洗衣机,它看上去还是全新的。在燥热的驱使下,母亲脱掉了外面罩的枣红色单衣,扔在洗衣机的盖子上。她里面胡乱穿着的娅凝淘汰下来的色彩鲜丽的T恤衫。这和她的衰老面容很不搭配。当她再度俯身想拾起一件衣服时,那上面按上了猫儿的爪子,牢抓不放。母亲另一只拿着衣架的手,朝猫儿打上去,猫儿的爪子勾住了衣服,拉扯了几下才跑开。
母亲咧嘴笑着。
娅凝躺在客厅的躺椅上,带着欣赏的态度望向阳台这番现实的姿影。
夏天又到了。离艳华逝世过去两个多月了。
上个月的一个黄道吉日,小叶在粉红小洋楼举办婚宴。那真是个不可思议的晚上。
会议厅的四个顶角安装了音箱。主桌前的话筒因为来来往往的碰撞,不时发出刺耳的噪音。
小叶身着旗袍玲珑有致,抹了很浓的粉底,盘了个圆圆的发髻。她的周身焕发着夺目的美丽和风韵,好像杂志封面的女郎。与新娘相比,娅凝很少在婚礼上见到相称的新郎,小叶的男友却打破常规,玉树临风地周旋在几张桌间,洒然招呼旧同事和曾经闹过不愉快的领导。像所有走出小镇而蒸蒸日上的有为青年那样,与其说是不自觉的炫耀,不如说是人在向上跃迁后所自然拥有的宽容和包涵。
娅凝这桌的同事小声嘀咕婚礼过于简单随意。他们不知道,小叶在市区会办一场隆重的。这个简单的婚礼场面上还是热热闹闹,闹新人的缛节层层不漏。
被喜洋洋的气氛环绕的娅凝蓦然想起自己的婚礼,感到那比小学时代还要离得遥远了。
她抿着啤酒,吃了几口凉菜。然后就悬起筷子呆,眼神迷茫。嘈杂的喧哗烘托着娅凝的孤寂。耳畔混乱的人声,似乎在说隔壁桌有单身男士,问他们这里有没有待嫁的女士。娅凝慌忙垂下头。婚宴上的起哄很平常,娅凝却憎恶把单身的身份拿到稠人广众**人取乐。而她本能的笨拙反应,已经让观者暗自发笑了。
天花板上拉成十字的彩带摇摇晃晃,中间挂着红色的花球好似个蜂窝。
端菜的服务员不得不双手举起碟子躲让猛然起立闹酒的醉客,她们一如既往表情冷漠。小叶手拉新郎,正给领导敬酒,领导肆无忌惮地开着玩笑,内心的反感妨碍了小叶的笑容,她的笑沉淀在嘴边,非常僵硬。她那白里透红的脸颊上,沾了一颗小亮片。
两人的头发上也洒满了亮片。看着这象征着喜庆的标志物,娅凝的高兴中藏着失落。下个礼拜就见不到小叶了。上班还有什么意思呢?她近来发现,有些经历是因为明天要拿去跟小叶分享,才会变得有趣。小叶聆听的表情总促使她大说特说一番海明,不惜添油加醋。
这是朋友的价值啊。
而她始终没有跟小叶提艳华。没有跟小叶解释自己为何萎靡不振。就像艳华妈妈拒绝自己的奠仪那样,她失去了让自己良心哪怕稍稍好受点的机会。所以,她唯一能为艳华做的,就是按照她生前的交待,“别告诉别人我病了。”
娅凝不再有别的朋友。因为她原本就不需要朋友。她喝空了玻璃杯里的酒。
周围的嘈杂似远似近,令人窒闷地讴歌着日子的美好祥和。前两天拿到新的体检报告,除了视力不合格,营养不良,其他都过关。肝肾功能还算正常,并没有产生服药的副作用。
作为健康人,有什么理由难过呢?
可是那天,把体检单搁置一边后,娅凝继续捕捉到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可称其为广泛性的焦虑。命运的不测并非由体检单来呈现。还有其他。她发现自己像一个在山里迷路的人,总是回到原点,周而复始的焦虑。她下决心破除这样的思维。努力戒药,跟沉沦期挥别。
娅凝很久没有身处热闹场,几十平米的饭厅排开五六个大圆桌,跑跳嬉闹的小孩,认真谈事的大人,只顾吃菜的食客,还有从表情可推断正在说他人坏话的人,占满了大厅。她听到“呜呜——”的拍话筒的声音,新郎被拱到了前面,他缓缓拿起话筒凑到嘴边,用五音不全的嗓子起了调。这是小叶完美男友让人大跌眼镜的地方吧。人们很满意地看待他的缺陷。
台下的人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她也边笑边鼓掌。
即使句句不在调上,也用不着难为情,继续唱下去,总能唱完它。
歌声停下了不久,五官丑陋的副厂长来到娅凝所在的桌席敬酒,被几位纷纷夸他“帅”的女士挽留,莺声燕语中,他坐了下来,点上了烟,笑纳着赞赏。
娅凝鄙夷的看着这一桌睁眼说瞎话的女人。
她们刚刚还在评论小叶的妆化得太浓,转脸却阿谀起了一位丑极了的男人。
副厂长笑得露出了牙床。
极为可怕的是,一遍遍地强调“您真帅”已经不是言不由衷的逢迎,更像是发自肺腑。
娅凝霍地拿起桌上的一瓶啤酒倒满杯了一饮而尽。酒有碳酸饮料无法达到的甘冽,冲到头顶的醉意抚平了她的激愤。她的眼睛盯着瓶子里橙黄透明的液体。对耳边的询问置若罔闻。她一杯接一杯的喝,很快喝完了一瓶酒,她从酒杯上方看到那张近乎钟楼怪人的脸,赘肉像窝棚的毛坯塌了下来,抽着烟的血盆大口,那双无辜的眼也诧异的扫了她几眼,烂了一张脸的笑容显示出他已经被名不副实的赞美麻痹。
谁能猜到娅凝心里在为美丑颠倒的荒唐而悲哀,她真实起来就是这么幼稚。大家还以为她被喜宴刺激了。
“这位女士是谁啊?很能喝嘛!”副厂长问。
“我们这儿的才女!”同事回答。
看着副厂长投来的目光,娅凝呆愣地短促地微笑了一下。没有什么比这个微笑更能调侃娅凝的庸人自扰了。
酒席的尾声,音箱关闭,吱吱啦啦的噪音一停,人们的话语水落石出般的孤单。娅凝弯腰捡起地上的一枝玫瑰,刚刚从新娘的捧花里掉落下来的,捏了捏它的花瓣,居然是真的。宾客开始散了,她手里摇着玫瑰花跟新人告别。
她们的手握在一起,新娘浑身散发着馨香,不知是香水还是粉底,很好闻。
小叶咬着下嘴唇,诚挚地看着娅凝。祝福的话语都被别人使用过了,她俩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昏黄的路灯拉长娅凝倾斜着的一步三摇的影子,玫瑰从手臂旁逸斜出,生动地随她在地面游走着。
梧桐落在地上的树影看得到新芽的形状。
娅凝突发了一个冲动,这个冲动是为了抵抗今晚彻骨的空虚。她要把婚宴上所见的丑陋一幕去告诉给许久没有造访的海明,和他一起取笑庸俗的男人和女人。
她加快了醉醺醺的步伐。
海明和父母分别住在上下两层,为了看清楼层号,娅凝拉开了楼道的灯。她忘了有电子门铃,直接把手伸进防盗门敲起来。
“海明!”她一边敲一边以昂奋和迫切的语调呼唤着。
过了好一会儿,海明方来开了门。但他没有打开防盗门。
海明身上穿着棉背心,一种娅凝从未见过的扮相。
哦,天热了。
他面色慌乱地瞅着娅凝。
娅凝抓住防盗门的栏杆,就在这时,她手中的玫瑰滑落了下来。后来,她还从家返回到海明的楼底沿路寻找起这只玫瑰。
“让我进去,我有事跟你讲……”娅凝快活地摇了摇栏杆,是的,酒席上令她义愤的一幕当下已化为特殊的快乐。
海明望着她,支吾着说:“娅凝,不方便……我房间里有人。”
“什么人?”
海明沉默不语。
当娅凝瞥到房间里射出的灯光洒在地上,映着微微晃动的被子的影子,明白了什么。她感到无比尴尬。也许是不知道怎么从当前的尴尬里抽身,她的手就像焊在铁条上一样,忘了松开。
“娅凝……你醉了,回家吧……”海明的手从栏杆间伸出来,抚摸着她的头发。
惰性黏住了娅凝的脚底。终于有了这一刻。和海明一开始就预料到会有这一刻。她曾经设想过在这种境地下是对方而不是自己该困扰如何开脱。她一动不动,想转变一下吃惊的反应,却为如何给海明留下豁达的印象犯难了。僵持中,她语速飞快的讲了一遍酒席上的所见,愚蠢地以为这么冠冕堂皇的乱说一气,会让房间里的人瞧不出她和海明的关系。
然后,她转身飞奔下了楼。
不用再去海明家了,这又为生活增添了新鲜的调料。
对娅凝来说,“了断”进化成动人的字眼。和小叶、和海明。
和陶煜。
都了断了。
她也一度沉湎于和艳华生死相隔的新鲜关系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