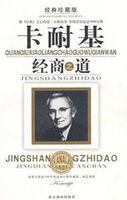看到李兰站起身形,那条人影也不在静立,转身步下蜂腰小桥,进入挑檐涂丹的连廊,每走近一步,映在年轻人眼睛中的影子便清晰一分。
与那日的衣胄鲜明不同,姜若嫣此刻一改素日劲衣窄袖长靴的打扮,竟穿着暗花云锦宫装,前襟的刺绣与腰间的流苏已成功调和了她英勃朗朗的中性气质,显得气度沉静雍容,明艳而不可方物。只有那一头又长又顺的发丝仍以略合时令的菊花簪简束,未带任何钗环,眉宇间那抹寂寥神色非常显目。
云阳公主的脚步迈过连廊回拦,走进了暖阁里,见李兰躬身行礼,不由向他露出一个柔和的笑容,道:“公子总是这般客气,我说过的,视我如之平常便可,礼数多了可就要过于生疏了呀。”
李兰微微抬眼,眸中略有神摇意动,含笑请姜若嫣在梅花朱漆小几旁的软椅上坐下,捧杯奉茶后,方徐徐道:“是在下的罪过了。我看公主这番霁月光风,可是刚从宫里回来?”
“公子客气了。”姜若嫣的视线投注在李兰素淡的容颜上,道:“确是如公子所言,我初从祖奶奶那里请安归府,听白叔说公子好不容易有余暇自左督卫而归,便过来看看。”
“太皇太后?”李兰眉睫一动,微微沉吟道:“怪不得公主难得隆而重之着上宫服,原是为太皇太后请安去了呀。公主既有如此这般纯孝之心,想来她老人家那里,应是心感甚慰呢。”
热茶蒸晕之下,他原本多思而略有苍白的面颊有了一丝朱润,看起来倒也算得上气质闲淡,清雅风度。姜若嫣凝目看了他半晌,方轻声道:“祖奶奶膝下自有云罗她们几个陪着,我平素军务繁重,很少与她老人家闲叙趣事,今日前去,也是有几分迷惘在内……提之无用。”
她说这话时语调甚是轻松,可李兰却听出了淡淡的寂寥之意,不由深深地看了她一眼,默然少时道:“公主可是在为左督卫诸多军务而烦忧吗?”
“不是。”
“那就是再为在下了?”
“没错。”姜若嫣坦然地迎视着他的眼睛,双眸亮若晨星,“我进宫是想求父皇批下谕旨,令公子调任到我那里,统领麾下亲卫,以好避免公子在神机营生出什么闪失。只是不曾想祖奶奶静极思动,派云罗那个小丫头请到了寿宁宫叙话,便有所耽搁了。”
李兰微微怔仲,不禁摇头笑道:“其实就算太皇太后未与公主你闲叙,便是见到了皇上,也不会遂愿的。”
姜若嫣定定地看了他一眼,道:“公子的言下之意是……”
李兰闭了闭眼睛,再睁开时眸中已清平如水,轻声道:“皇上既然诏命我统领神机营诸禁卫,圣心独运,自然有这样做的道理,不然公主麾下羽营众多,为何要单单是这神机营呢?若真是看在我白衣难以担客卿之尊,故而赏赐官位略显薄颜,那只管让公主随意指派不就得了?何必擅用御封呢?”
姜若嫣面不改色,但牙根已暗暗咬紧,半晌后方吐出一口气,道:“可再怎样,父皇也不能将公子安排在神机营,陆……他是父皇明谕亲贬,不会不知道的,届时父皇就不怕公子你有所牵连吗?”
“皇命不可违呀。”李兰摊开双手一笑,“公主也不要过于担心,我现在不是活的好好得么?陆都司再对我有所不满,我一应承下便是,男儿嘛,坐下来喝喝酒聊聊天,兴许这恩恩怨怨也就化解了呢?”
“公子还是这般风趣。”姜若嫣怔怔看了他一阵,低声道:“只是公子素来久居金陵,不知繁华皇都里究竟有多少见不得人的勾当,暗箭难防,他那人的性情……我不放心公子在神机营,故而才请父皇谕旨调任。”
李兰欠身重新为她添续热茶,笑意晏晏:“神机营当然不是一个好去处。可公主想过没有,就算皇上真的答应了又能怎样呢?京城里的那些流言蜚语公主总该略闻一二吧?若真是不声不响地离开神机营,届时流言传得更加神乎其神暂且不说,便是诸司禁卫那里只会认为我羞愤难当服了这个软,进而声威尽失,又如何在左督卫中立足呢?
李兰略略停顿了一下,方继续道:“这不是最要紧的,公主当知我素来不喜纷争,被人戳几句脊梁骨也就罢了,我又不疼。最要紧的是,济济朝臣那里会是什么态度?皇上那里该是何等想法呢?且御史们参我一本也无妨,最怕是皇上那里会认为,我不足以有客卿之尊,届时难保再提婚嫁之事……公主要明白,暗箭确是难防,但那些最阴险最恶毒的冷箭是冲着公主你来的,而我这个挡箭牌只有足够厚足够重,才能保你安然无恙。”
姜若嫣羽睫不由自主剧烈地颤抖了一下,胸口因为他的话反而柔柔的一暖。虽然他适才说那番话的目的,是为了劝服自己,让她以为日后神机营之争真的不会影响到什么,从而放下心来,可看到明明可以置身事外的李兰,却对自己再三庇护时,心中自然还是免不了一番感动。
多思者必心累,心重者必心苦。铁石心肠之人尚可得知这等言简意赅的道理,更遑论于她赫赫有名的云阳公主了。
暖柔的夏风自廊间自檐下攸忽而过,这个临危受命而统御三万左督卫,保护了南境万千百姓的少女,第一次觉得,其实被别人保护那么一下下,真的很好,很温暖。
默然良久后,姜若嫣秀眉微蹙,道:“公子所言确是在理,只是神机营那里……前些日子白叔曾言,公主为彻查账目而请了全京城的账房先生,可有什么眉目?陈年旧账,真的能够查得清楚吗?”
李兰仍是笑容未改,温言道:“现在的每一分时光,都是从过去延续而来的,不查清楚过去,又怎么知道现在应该做什么,不应做什么?无论是再久远的过去,种下什么因,终有什么果。既然我能从陈年旧账里找出些蛛丝马迹来,假以时日必能查清此事,只是……”
“恕我失礼,我不得不问一句。”李兰目光如炬,灼灼地射在云阳的脸上,“我再回神机营时,必会再生波澜,恐难有对其冒犯之处。再有,若确有此事,我是不会饶了陆丘得。届时公主该当如何?”
姜若嫣心头一震,眼睫剧烈颤动了一下。尽管事情已过去很多年,尽管可以不在午夜梦回时心颤落泪,但多年的修炼平复,竟未曾带来丝毫真正的痊愈。这个清雅书生简简单单的“陆丘”二字,就可以猛然勾起心中的滴血痛楚和刻骨仇恨,宛若南境寒岭那一具具枯骨,永远那么鲜明醒目,随时随地都无法漠视。
李兰将目光从姜若嫣的身上移开,似乎是不忍见到她猝然间显露出的脆弱一面。身为三万左督卫的奇才统领,自然是世间最高傲与强势的女子,可是剥开她傲人的身份与坚强的面具,她仍然是那场惨剧中所幸存下来最无助最孤单的小女孩。
活下来的万千将士可以与妻苦述离别,与友酒庆百死余生。可她呢?除了本应执手到老的檀郎给予的背叛,折磨,仇恨,还能得到什么?名扬天下的赫赫声威?哪个女子平生之愿是这个?黎明百姓敬仰的女将军?哪不是英烈男儿当有的豪情么?
终生所求,不过相夫教子罢了。
幸而她是云阳,将军的职责与坚韧的心志支撑她抗过了那次打击,皇室宗亲面前也未曾轻露悲伤。不幸她是云阳,一团混乱中人人都因为她的坚强而疏忽放心,只到某一天突然发现她已至待嫁之年,红衣披身却无家时,才徒然惊觉她心中的积愤与哀戚。
任何人的伤疤一旦揭开,必是锥心刺骨深入骨髓血淋淋的痛楚,但李兰心中明白,今日若不得到云阳公主对陆丘究竟持何态度,他日再起争端,难免有些相形见绌而事事放不开手脚。
伯仲之间的对弈,若有一方优柔寡断,最后的下场,可想而知。
“公子。”片刻静默后,姜若嫣抑制住了自己激动的心情,低声道:“自南境归朝后,我便与他再无瓜葛。他零落如尘埃也好,前程锦绣也罢,自是形如陌路,终究是一个无关紧要的过客罢了。故而公子日后想做什么,云阳不会干涉,但若有一日公子有难,云阳肯定是不会视而不见的。”
“公主良言,自当谨记。”李兰唇角轻轻抿了一下,眸色仿若清潭般幽深无底,深施一礼,轻声道:“气由心生,还望公主莫要多加感伤,今日孰乃我之过,对不住了。”
“公子言重了。”姜若嫣饮尽杯中余茶,放回桌上,站起身道:“陈年旧事罢了,提一提又何妨。公子再回神机营时,若有何难处,记得知会云阳一声,我也好为你多做准备,不教任何人伤你分毫。我……有些累了,就先回去歇息了吧。”
李兰轻轻喟叹,月白衣衫微扬,一路送佳人于庭外。小月的身影在旁边树枝间晃了晃,出现在李兰的身边,仰起小脸,那眸中的神气,分明是想让少爷前去安慰安慰。姜若嫣回眸看着满是心疼的脸,突然脚下一滞,一股疲惫之感涌上心头。
手上的左督卫军务尚未团满处理,而京城里的波澜汹涌,则更是方兴未艾,仿佛要席卷摧毁一切般,让人感觉无力抗拒甚至躲避。
云阳觉得此时的自己,竟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想要驻足,去看看天下风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