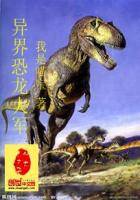地上世界有四季,春夏秋冬四季更替。而在这个属于星影照射的地底世界只有两季:冬季和秋季,冬季的雪月、雨月、风月,秋季的葡月、雾月和霜月。每年以冬季雪月为开头,下整整四个月的雪,从不间隙,雨月则是雨神戏谑欢畅的时令,风月妩媚微云和风愉悦无比,秋季则是个丰收的季节,人们的很多活动,像是庆典、祷拜都会在这时候举行。
翌日,葡月之阳,首日。
籽言起了个大早,拖着鸿鹄把到了回元药庐的药台前,然后里里外外忙活一通,望着外面排起的长龙,和她把脉枕、毛笔、纸、银针挨个摆在他面前似乎有种不好的感觉,准备好一切后籽言满心欢喜地给他递了个颜色,甚为主动地把第一位病人拉到他面前,又把人家的手直接摆到了脉枕上。
鸿鹄瞠目,果然她是要自己代替庆元给人看病,想来庆元伤了左手无法给人搭脉,她今日这样做许是为了弥补心中小小的愧疚。见鸿鹄半天无动于衷于是频频给他递眼色全然不顾,心里有在揣测是不是还在埋怨她动手伤了庆元的事,想到这籽言的表情从期待转为自怨,可是早晨也是她自作主张把病人请进药庐的,如果说这会不看诊了不知道会闹成什么样子,直到鸿鹄将手指搭在病人手脉上时她胡思乱想的脑子才安分下来。
自己一介玄武神官是何等尊位,如今居然被逼无奈在这小小药庐给人看病诊脉,这要是传回玄武神殿,不知那些星官和神官们会作何感想!
唉!
七叔听见门堂外人声吵杂不知怎么回事,因为他吩咐过下人闭庐几日,哪里会这样吵闹?等他走出去却看到鸿鹄正在和病人说着什么,籽言忙里忙外地抓药,光看着她忙活得满头大汗却已抓错了好几味药在纸包里了。七叔连忙跑过去拿下籽言手里的纸袋说:“使不得使不得啊姑娘!”他把籽言好不容易才装上的草药全倒出来说:“这是乌头,那是半夏;这是藜芦,那是芍药,这些药药性相悖可不能乱混在一起啊!”
“可、可是鸿鹄的药单上就这么写的啊……”籽言把药单递了过去。
七叔看一眼就明白了,笑着说:“姑娘,你看错行了!”
籽言顺着七叔指着再看一遍,果然是自己看错了!这里是右起竖文,而籽言习惯左起横文,还好七叔及时出现,不然这要给病人开回去,万一吃出问题不仅没给药庐帮上忙不说还会砸了人家招牌!
七叔过去把鸿鹄也拉了起来说:“你们不必为庆元的伤有什么内疚的,小孩子不懂事,受点伤磨磨性子也是好的,没那么娇气!远来皆是客,你们这样做要是传出去岂非说我们回元药庐怠慢客人了?”
可是接下来的病人也不能赶走,于是七叔自己坐到诊位上,又吩咐人把庆元喊出来,嘴里念念叨叨的,这孩子以前从没起来那么晚,今天太阳晒着腚了居然还在睡!他打算一会等庆元来让庆元帮籽言看药,由籽言负责抓,这样合作就不会出差了!约莫过了半支香的功夫,庆元才从内堂晃晃悠悠地走出来,七叔当时已经满头大汗了,籽言虽然有鸿鹄在旁边叮嘱奈何药味太多,难免兼顾不得,几番下来也是焦头烂额,
庆元脚步虚浮,两道乌青的黑眼圈正趴在眼下,人摇摇晃晃的像是踩在棉花上,没等籽言过去,七叔噌地从椅子上站起,“啪”地一声照庆元脑袋就是一巴掌!“你小子仗着带点伤就开始混账惫懒了!婆婆这才走几天你就收不住性子,你以为婆婆走了就没人管你了是吗?别想好事了!”接着又是一拳头,可是这拳很轻,七叔也是留了力气的,只是想给庆元个教训而已,“再这样不知勤勉等婆婆回来还要你抄《寻珍药记》!”
籽言咂舌,《寻珍药记》这书她也知道,是当年号称仙医的王学珍遍访山河大川悬崖辟谷所记录下来的典籍,这可是耗费了王学珍毕生心血,由于手稿极其难得,后来人们抄录相传才得以流传至今,里面一共记载了四百味草药,其中包含已经定性的三百味成药,四十味名贵珍材,和七十味不定性药料,所谓不定性就是只能确定该药材是可以入药,但是有无副作用还待考究,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带有手绘图,一般人还真无法抄录,所以当年因此书,抄录先生的价格暴涨,而《寻珍药记》的价格也是成倍上翻,想要把这东西完完全全抄下来没一定功夫可是办不到的!方才听七叔的话语估计庆元应该是不止一次抄录过了,其中枯燥与艰难籽言不禁咂舌啊!
有庆元帮忙籽言这下可以脱开手了,向旁人寻了市集的方向就出门去了,鸿鹄也没拦着,也只有她这样心大的人才会忘记药庐有结界,她根本出不去,可是约莫着到了她该垂头丧气折返回来的时候还是没有人影,他到门口一看,结界破了个大洞,籽言消失得无影无踪!一时间他又急又气,刚转身下意识又回过身去仔细观察结界口,被损坏的边缘参差不齐,整条流线下来也是凹凸不整,虽然神术技艺拙劣却并不像是籽言打破的,因为他从未教过她任何破系和发散系的神术口诀,就算借助穹珏之铃的帮助也不会这样神不知鬼不觉的,除非……除非有人故意打破结界……
就在他出神的功夫,剑鞘里的剑极其反常地响了一下,“哐啷”一声,紧接着一股腥臭气扑鼻而来。
是妖气!
鸿鹄警觉,飞梅已然蓄势待发,可是妖气又突然又消失了,像之前的三色堇一样,突兀出现又忽然消失,而且消失得无影无踪,就算他再怎么搜索也是没有一丝痕迹……这时候他才发现不知何时庆元也出来了,此时正站在院中呆立,他看似精神萎靡,阳光下的身影更是左摇右摆,一个趔趄幸得鸿鹄扶住,冷不防被庆元抓住狠狠咬了一口,血顿时就流了出来!庆元抬起头来,除了嘴角挂着的血滴,在他青紫色的脸上,两颗眼睛布满了血丝,红通通的双目仿佛要吃人一般!他脖子极其僵硬地转动两下张开口朝鸿鹄手臂咬来,他二指灌注念动口诀,在庆元的印堂上画了个卍字符,掌心推过,黑光散出,“嘶”地一声,一道黑烟从庆元天灵冒出钻入地下不知去向。
鸿鹄的房间,七叔和凝月都在。
望着躺在床上昏迷不醒的庆元七叔担心不已,方才他见鸿鹄和庆元出去好一会都不见回来于是出去看看,这刚踏出去就见庆元身体硬得像木头般笔直向后倒去,这手伤还没好,怎么又出这么个怪病。
“这早晨还好好的,怎么转眼功夫就变成这样了?……”七叔唉声叹气,凝月倒了杯茶给他,当时她尚在屋中篦头,就觉得外面有声响,追出去也看到庆元正死死咬着鸿鹄不放,不过是被控制心智的庆元所咬,虽然有妖邪之气,但是并非能伤得了鸿鹄,七叔是凡人看不到方才飞出的妖气,但鸿鹄就不一样了,她趁扶着七叔的功夫偷偷看了一眼,鸿鹄此时眉心深拧,那看似琢磨实又费解的眼神似乎也不很确定那妖物来路,怕暴露不敢过多窥探的舞凝月谨慎地收回目光。
当初水神共工扯下火麟神龙的鳞片照亮地底世界的时候就已经将所有邪恶的妖物全部送进了双极轮回之中。此妖物为万恶之祖,是一切邪恶之物的起源,同神兽失道变为妖兽和幽灵有着本质的区别,妖物属阴灵,乃先天妄生之物,有逆中和,本体失魂夺魄,所处之处祸必随之,乃大天之煞,非高悬之士不得以服。而妖兽和幽灵是后天怨恨暴戾的产物,同原始邪恶的暗灵根本没有匹敌的资格。当年那些没有进入轮回的妖物也被压在了镇妖鼎里,镇妖鼎每隔十年就会降下流古符火,符火焚烧七七四十九日任它铜皮铁骨也会灰飞烟灭,就算要破除新生也需百年,根本避不及十年一次的炎火,这地底世界已是万千年,按说镇妖鼎里的妖物早该化为灰烬了,怎么会……
想到这鸿鹄有了两个大胆的猜测,据说当年有妖物为了躲避双极让自己假死于土下深层,双极阴气不敌地心阴力无法深入从而躲过灾劫,这是其一,其二就是当年有妖物侥幸躲过流古符火,而如今又被居心叵测的人从镇妖鼎里将其放了出来!可是这二者无论哪一种情况都是需要无比的能力,要知道地心阴力和流古符火都是极阴极阳之物,能藏于此内而不被撕成碎片灰飞烟灭,这样的妖物该会是多么可怕……
鸿鹄露出了少有的凝重表情,如果任其妄为恐怕这个国家会永无宁日,可是自己连妖物的企图都不知道又该用何办法诱其现身,就算侥幸抓住,又有何办法将它送入镇妖鼎里接受惩罚?毕竟水神已逝,放眼天下,终究没有任何人有能力将地底世界所有的妖物再次封印在镇妖鼎内。
担心庆元伤势的七叔眼睛始终不离开床边。
凝月安慰着:“七叔,你就不要担心了!庆元只是被小股妖邪侵体暂时失去心智而已,鸿鹄已经用卍钉将他体内的邪气破除,过会差不多就能醒来了!”可是刚说完她就后悔了,果然七叔没多说什么反而让鸿鹄察觉丝异样问她为何会懂神术,于是极力掩饰说自己小时候曾拜在一位修仙灵人门下学习神术,但是先天无修仙灵人的根基,所以只是懂得些要诀和表象而已,连皮毛都算不上。索性鸿鹄也未多想,毕竟此刻他对不明妖物的担心远胜于舞凝月不小心露出的破绽。
这一个国家一个妖怪,角国一个幽灵还不够,亢国又冒出个不明妖物,好像自己来到这里不是将籽言带回玄武而是除魔卫道来了!除的还是别的世界的魔,卫的还是别的世界的道!干脆不要做星座神官,去当除魔道人匡扶正义好了!鸿鹄颇为烦恼,有些嘲弄自己的意味,果然这条路真不是那么好走,不知道籽言……说到籽言鸿鹄心头一惊,糟了!他步履无风人却瞬间消失不见,籽言现在孤身在外,万一碰到妖物就糟了!
结果他刚出门就和闷头往里冲的籽言撞了个满怀,一包花籽洒得满地都是!幸得鸿鹄展臂抱住才没滚下台阶,见辛苦买来的花籽洒一地那心情别提多沮丧了,她算是体会到了当初打翻六月雪的时候庆元的心情,要知道这可是她跑了七条街好不容易才买到的花种啊!
“你干嘛啊横冲直撞的!”籽言忍不住埋怨道。
“你没事吧?”
看着鸿鹄看似迫切关心的眼神籽言莫名其妙,自己一个大活人好好的能有什么事?她小心翼翼地将花籽包好,听卖花的人说这是培育出来的新品种,叫胭脂,虽然不知道能不能入药,但是光看那花苞是好看的不得了,就算不能入药培植起来留着赏玩也不错啊!籽言边跑边喊庆元。
“籽言姑娘小声些,”凝月走出门来说:“庆元现在需要休息。”
休息?肯定是补觉去了!籽言想,她刚才特地去了趟庆元的房间,可是屋里空空的,一问扫地的下人才知道鸿鹄把他抱去自己的房间了,她边跑边想这鸿鹄是不是转了性子了,他像是有洁癖的人从来最讨厌别人碰他东西,但凡有人染手,他绝对弃之不用,难得这次居然会让庆元睡他的床铺?!籽言兴冲冲地跑进去,距离床缘还有三步的时候突然停下了,与其说是停下,不如说是定住!同庆元当时一样!鸿鹄大惊失色立刻冲过去才发觉异样,籽言并没有被任何妖邪侵体的痕迹,呼吸、脉象和神情均很正常,可是奈何她对所有事物都没了反应,情急之下的鸿鹄欲用醒神之法唤醒她,可这时籽言嘴唇动了动,好像说了什么,声音很轻很幽浮,鸿鹄凑近些许,籽言死死盯着庆元身上漂浮着一层挥散不去的黑霾,喃喃道:“风伯……飞廉……”
听到这个名字鸿鹄的心咕咚一声,沉了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