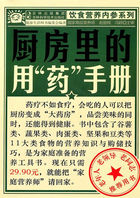“我也不知。”湛碧抹了一把额上冷汗,回想起刚才那一幕,火红的双眼,金色的光芒。心中不由泛起一阵不详预感,打鼓似地担心着。
“太医来了。”那宫女和湛碧是临门站着的,眼尖地看见一行人神色匆匆地往这边行来,便低声说与湛碧听。
“快,让太医瞧瞧主子。”湛碧挣脱了被扶着的臂膀,此时她已经勉强能站住了。
湛碧待太医进了寝殿,便很是恭敬地福身打揖,“您瞧瞧我家主子。”
“姑娘不必多礼,老臣自当全力以赴。”那个年近花甲的太医空手进了内堂,身后还跟着一个提了药箱子的医童。
内堂里,卷宛和被宫女们安置在床榻上,身上盖着柔软锦缎面的棉被,床门帘的位置,那一袭纱织的帐幔放了下来,一直垂到地上。窗外的风吹进来,直叫纱幔顺着风悠扬飘起。
“你们去关了窗户,外面的湖风极致阴寒,若是吹多了不病也得病。”那老太医看了眼窗户的位置,吹进来的风刚巧对着卷宛和床沿的位置,他捋了捋花白胡子,看不出是什么表情。冷冷地吩咐道,“立霖,将为师的药箱打开,从里面取来金线。”
“是,师父。”那个被唤的男子走近桌案,轻放了药箱,从里面找出了一团明黄极细的金丝,递给老者。
“来,将这一头系在娘娘手腕上。”老太医招来站在身边的一个宫女,将金线捋出头绪,一端放在宫女手中。
“是。”那宫女捏着细若发丝的金线,掀开了帐幔,将金线牢牢系在卷宛和右手腕上。
“师父,坐。”那个名叫立霖的男子移出圆桌下的雕花木凳,扶着刘太医入座。
“嗯。”刘太医应了一声,手肘搭在圆桌上,手指捏着金线这头,悬空着给卷宛和号脉。
“不好,不好。”刘太医一手拂须,一边摇头,还不断叹着气,吓的满屋子的人都噤若寒蝉。
“太医,您说的什么不好,我家主子怎么了?”湛碧一急,语无伦次地开口询问着。
“这位姑娘,我师父诊断时,请你不要出声。”立霖上前一步,伸手挡了湛碧询问之势。
“我也是心急。”湛碧悻悻地退后,一双眼睛还是焦急地不断在刘太医和帐幔上来回打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