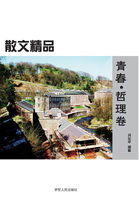还没等谢胡子把会议精神传达完,工人们便一拥而上,把谢胡子围住了,指着谢胡子鼻子骂:这哪里还是共产党领导嘛,这哪里还是社会主义嘛,分田到户?农场也分田到户?这不是修正主义嘛?人们把谢胡子推来搡去,弄得谢胡子在地上站不住脚。那阵势,就如同当年土改时苦大仇深的贫下中农斗争地主一个样了。谢胡子没有法儿,只好又跑到场里去,丧气败搭地求杨长:这次改革能不能再延缓一年,或者在其他队先搞个试点成功了,有了经验,再推开搞也成啊。
场长是个老军人,说话一向是说一不二的,看着谢胡子那副狼狈相场长便铁青了一张脸子,说:谢胡子,若是在战场上,你就是动摇分子啊不枪毙也得撤职。这改革是国营农场的出路,不改革咱农场就没有活路,你还没有穷够吗?农场怎么扭亏增盈啊,经验是现成的,这在外地国营农场早就实行了。只怕是你们将来尝到了甜头还要骂我保守,实行改革的步子太慢了呢。眼下是时不待人,你回去可以在队上先搞个试点,以点带面,条件可以优惠一点。至于生产资料缺乏就先由场里垫付。生活费用有困难,就到场里借嘛,到年底土地有了收成再还,今年还不上明年还,总之一句话,啥时候你们的日子过好了,啥时候再给我场里算账还贷。
谢胡子听了场长的话,立马跑回去,如实地把场长的话向工人们又述说了一遍,大伙这才平静下来。可轮到要制定承包计划、土地落实到户时,大伙便又都不说话了,谁也不肯领头冒这个风险。承包会议开了两天,也没有开出个结果,急得谢胡子想跳井,两天没有吃饭没有睡觉,嘴上起了一圈水泡子。没法儿,谢胡子弄了辆自行车,跑二十里路到芦花镇去找胡日鬼,胡日鬼的鬼点子多,俗话说骡子的屁多矬子的计多。当下胡日鬼听了谢胡子的话,低着头思谋了半天,把一棵烟点着吸了,吸了半截,往地上狠狠一摔,说:我操,老谢,办家庭农场这是个好事,这个头我带了。我这一辈子就爱搞个试验的,要不然也不会落个胡日鬼的外号,试验搞成了,这可能是一条路子哩。这样吧,你先答应了,给我三百亩好地,我这就关了这店门,跟你回队种地去,你看咋样?
谢胡子一听,立时跳了起来,说:胡日鬼,你这不是说胡话吧?胡日鬼说:我老胡啥时候舌头上跑过马?谢胡子一拍脑瓜顶子,说:这些日子我愁的就是那些地没人敢要,场里定的一亩地要交80元钱的管理费哩,有些人家没钱交,有些人家不敢交,这才闹腾起来的,三百亩地,你能行?胡日鬼说:那么多钱,让我立马交,我也交不起,我可以先交一半,另一半年底再交。不过这事要冒风险,有些话咱先说好了,你不答应,我就不干哩。谢胡子说:啥条件,你尽管提出来。胡日鬼说:我这是搞试点,那就只有成功;不能失败。谢胡子说:那当然,你失败了,后面的事情就不好办了。胡日鬼说:我办家庭农场,我种什么,怎么种,一切都得我说了算,你不能来胡掺和。谢胡子说:你的农场,你就是场长,当然你说了算。明日鬼说:我打下的粮食,我咋卖,卖给谁,也得我说了算。
谢胡子一听就怔住了,过去的农场都是计划种植,粮食打下来,统一交由场供销部门统一管理,甚至农业队长都没有权力销售,今日胡日鬼提出的这问题,谢胡子就吃不准了,回过头来就去请示场长,场长那几日整天和队上来上访的工人打嘴官司,上火动气,喉咙发炎,说不出话来,就用笔在一张纸上写道:
凡两费自理的家庭农场,享有独立自主的经营权,农场各级领导,均不得妄加干涉。
谢胡子拿着那张纸条子,跑回队上交给胡日鬼,胡日鬼把那张条捧在手上看了半天,笑了说:这是圣旨啊,有了它咱就放心了。
胡日鬼承包了三百亩地,胡日鬼要办家庭农场哩,这消息像风儿,很快就在农场传遍了,农场人都深感意外,于是有人就说:真是个胡日鬼啊这狗日的真是成了精了,他这一辈子都没有干过个正经活儿,属猴子的没个定性。一身的劲儿加起来没有半斤,他是个种地的人吗?瞎逞能嘛他以为这种地能像在他婆姨肚皮上耍羔羔那么容易呢,等着瞧吧,有他狗日的罪受呢。又有人说:胡日鬼这人是个精怪,他能哩,他是头顶上长球日天呢。没准儿他真能像孙猴子那样,从裤裆里拔一撮毛下来,放嘴里嚼一嚼,一口就能吐出几个小胡日鬼呢。有人嚷着说:要那么多的小胡日鬼干啥?那人说:帮胡日鬼种地嘛。一帮人就哄笑起来。
胡日鬼没理会别人怎么绕弯子骂他,胡日鬼的家庭农场还是办起来了三百亩地连起来是好大的一片呢。若是凭着胡日鬼那点瘦干巴劲儿,把他的沟子挣翻那也是忙不过来的了。但胡日鬼到底是胡日鬼,他有的是办法胡日鬼说:活人还能让屁胀死吗?人要赶大车,并不是非得人去拉车,而是人要借助牲口的力量去拉车啊,人只要把牲口驾住就行了。胡日鬼的话颇有点哲学道理,很深刻的。但胡日鬼不懂哲学,胡日鬼只知道使巧劲儿干活。
胡日鬼又跑了趟芦花镇,雇了两个庄稼汉子来帮他种地。芦花镇一向地少人多,劳动力剩余的多哩。胡日鬼在芦花镇待了一年,结识了一帮儿庄稼院里的朋友,要雇两个人来,那可是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的事儿。
胡日鬼这人很有点经济头脑,经过一番市场调查,他和省城一家啤酒厂签了一个合同,由人家给他出种子出技术,他出力,试种了三百亩的啤酒大麦。那一年风调雨顺,那三百亩的大麦长势喜人。大麦是早熟作物,在小麦刚黄芒的时候,它就该开镰收割了。胡日鬼找到场长,说他要收割麦子哩,场里能不能弄台收割机帮着收一下。那场长见了胡日鬼,拍着胡日鬼的肩膀说:你是第一个带头办家庭农场的,场里是应该大力支持的,这你放心,哪一天收割,我带收割机亲自去,同时还要在你那里开现场会哩,让全场的干部职工们都看一看,家庭农场的前景是无限广阔的,国营农场只有走经营改革这条路子,职工才能富起来,农场才能活起来。
胡日鬼听了场长的话,心里就激动得很,这让他又一次想起了那句“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的至理名言,眼睛里就热乎乎的。
那一天,场长果真就带了一台收割机来了,随同场长来的还有场部机关各科室的领导以及各生产连队的职工代表。胡日鬼的大麦地里红旗飘扬,一派喜庆气象。谢胡子也颇为得意,一边走一边对着随同前来看热闹的农三队职工说:都看看吧,好好看看吧,这就是办家庭农场的好处,当初让你们办家庭农场,你们狗日的都以为是把你们往火堆里推呢,咋样啊?后悔了吧?
在那个现场会上,首先是由场长讲了话,接下来是谢胡子讲,然后就是胡日鬼讲了。胡日鬼讲话的时候就站在场长的身边,尽管他的瘦小身子比场长和谢胡子矮了半截,但因为他们是站在那台红色康拜因收割机的驾驶台上讲的,这就让所有来参加现场会的人都得仰着脸儿来看他了,平时像三寸丁谷树皮似的胡日鬼,在那一时骤然就高大起来。胡日鬼激动得满脸通红,两手紧抓住那驾驶台上的护栏,扯着嗓子讲了一番感谢中央感谢地方感谢改革感谢开放的话。胡日鬼的话尽管讲得无边无沿颠三倒四让人摸不着头脑,但胡日鬼讲话时气势很足,神采飞扬。这就让一些原来就对胡日鬼的家庭农场心坏嫉妒的人心里就不舒服了,于是就有人指着胡日鬼在下边小声骂道:你看那个胡日鬼,不就是种了几百亩地嘛,你看把他能成个啥了,他也不在秤盘上称一称自己有几斤几两,瞎张狂。紧接着又有人说:如今这年头,富了的就是胡日鬼这种人,他这是精着沟子撵狼,胆大没牵挂,咋能不富嘛。
胡日鬼自然是没有听到这些议论的,胡日鬼对着驾驶员挥了挥手,说开始吧。紧随着一阵机器的轰鸣声,那台收割机像一艘大船一样,向着那片泛着金波银浪的麦田缓缓驶去……
这是一个夏天的早晨,初升的太阳照在院中的那棵葡萄树上,葡萄树叶上挂满了露水,早风一吹,那些露珠儿便闪闪发光。似乎那绿叶上镶嵌了许多珍珠呢。一棵大叶南瓜在篱笆墙上不停地攀援,把一朵又一朵金盅儿似的瓜花开了个满墙,使得这早晨的空气里多了一些清甜的花香。女人在院里摘菜时,随手掐下一朵金花下来,撒去花朵儿,只留下花中的一根金黄的蕊心儿,然后又把蕊心儿插到另一朵盛开着的花心里,那朵花的下面,孕育了一个小小的瓜胎。女人是给南瓜配花呢。
女人摘了一把梅豆,又铲了一把韭菜,这才开始到厨房做饭,饭做好了,就用锅铲敲着锅沿喊着说:秀儿,秀儿,叫你爹吃饭啊。女人连喊几声,见没人应,一掀门帘儿出来,看见儿子胡秀正弄了把椅子放在院子当中,人却双腿盘定坐在椅子上,目不转睛地看住了那一颗初升的太阳。此时的太阳尚不扎眼,油汪汪的,像一颗胞鹅蛋的黄儿。胡秀一边看着那太阳,一边双手不停地做出要拥抱那太阳的样子,每拥抱一次,便做出一次深长有力的呼吸。女人就怔住了,说:秀儿,你怎么和你爹一个样子,一辈子也没有个定性。胡秀撇了撇嘴,用不屑的口气说:我爹那算什么,充其量只是个鼯鼠之技,飞不能上树,涉不能渡河,洞不能掩尾。我怎么和他一样了呢?我这走的可是大师的路子呢。
儿子的话让莲香似懂非懂,儿子到底是长大了,儿子的学问也大了。
胡秀那时正在上大学,那是南方的一座很有名的大学,学的是计算机专业,那是一个好专业。胡秀原本就聪明过人,他的专业课在全年级一直是最好的,后来听说外语好了可以出国留学,他便拼命地学外语,接着又想当作家,便没日没夜地学习写诗,不长时间又迷上了《易经》。
女人便批评儿子说:你可不能学你爹啊,你爹就吃了不务正业的亏了,他那个人爱耍小聪明,学什么会什么,学会了就丢掉了,到后头是啥也没有了,人家都评职称呢,他连个技术员也没评上。女人尽管唠唠叨叨地说着,可做儿子的却不再说话,一心沉浸在他所幻想着的那个美好境界里去了。
女人见儿子不再和她说话,就回屋去了,女人才说要叫男人起床吃饭的,却见胡日鬼正泥胎木雕般地在床上坐着,两眼尽管睁得老大,却没有了一丝儿的活意。女人先就吓了一跳,拿手指在鼻子下面摸摸,嘴唇还是热的,鼻子眼里却不出气了。女人一时慌了手脚,急忙朝院子里喊着说:秀儿,秀儿,快看你爹,你爹他没气儿了。
胡秀闻说,一个蹦子从门外窜进来,趴在胡日鬼的脸上看了看,说:我爸这是走火入魔了。说着就到处找针,说要针扎了人中才能过来的,慌忙之中看到了箱柜上有一把锥子,胡秀拿过来才说要朝那人中处扎的,锥尖儿还没及皮肉,胡日鬼身子猛地往后一仰大叫一声说:我死了。说着通的一声,人就直挺挺地躺在床上了。
女人这才松了口气,知道又是胡日鬼作怪耍弄人的,就手揪了胡日鬼的耳朵,把胡日鬼从床上拉起来,骂着说:你这没正经的东西,怎越活越没出息了,没个耍头了,怎能装死弄鬼吓唬人呢。
胡日鬼把耳朵从女人手中挣脱出来重又躺在床上,说:我做梦我死了,都说人做梦死看是好事哩,怕是这次竞选队长能选上呢,你们都不要打搅我,让我再死一次。
胡秀闻说便来了兴趣,说他可以把梦中所预示的事解出来的。胡日鬼一听便坐了起来,说他梦见他死了,不知怎么稀里糊涂就死了,他死了后就装在一具棺材里被一群人抬着走呢。胡秀一听,便说:这真是一个好梦呢,梦书上说棺材乃官才也,人入棺就是入官之意啊。你入棺之后被一群人抬着走,那就是说人们在拥护你抬举你哩,这是吉兆。爸,看来这队长你是当定了。听胡秀这么一说,胡日鬼就高兴得很,多少就有点把持不住的样子了。听莲香说要吃饭了,这才跳下床去洗脸,一路走着雀儿步,嘴里哼着一支歌儿,那歌儿是刚跟儿子学会的,名字就叫《阿里巴巴是个快乐的青年》。
吃饭的时候,莲香说:你也别高兴得太早了,让你儿子一说,就轻狂得要飘起来了,人家当官的要走得稳,坐得稳,那叫官相,你看你,尖嘴猴腮,个头还没有个扁担长呢,你连个技术员都没评上,还当队长哩,我看悬着呢。胡日鬼嘴里头正嚼了口饼子,听婆姨这么一说,便急着把一口没嚼透的馍咽了下去,立时便噎得伸长了脖子,像鸡一样咕儿咕儿地叫胡秀见状急忙在胡日鬼背后用手拍了几下,待那团馍馍下去了,胡日鬼这才说:你女人家倒是好见识,你给我说说,官相是个啥样儿的。女人说这做官的嘛,个头儿一定要大。胡日鬼说:庄稼长冒了头,还不结籽哩女人又说:做官的嘴一定要大,你看眼下那些当官的吃官饭,走到哪吃到哪,这叫嘴大吃四方。胡日鬼说:吃四方还不挑食呢。给啥吃啥,你说的那是猪。女人又说:做官的耳朵都大,有一双大耳朵,上听皇帝圣旨,下听百姓民情。胡日鬼说:你说的还是猪,猪的耳朵最大,大得翻下来把自家的耳朵眼儿都堵住了,它啥也听不见,只听见母猪叫,一圈的猪,哪个发情了,一叫它就知道了,就走过去关怀一下……胡日鬼的话说得不雅女人生了气,在桌上踹了胡日鬼一脚,胡日鬼发疼,便嗷地叫了一声。
农三队有位名叫张望才的老职工死了,按照惯例是要开个追悼会的主持追悼会的当然应该是谢胡子,谢胡子是农三队的最高行政长官,他不主持谁主持?若是再换个人,那追悼会的规格就下降了,这是生者和死者都不能允许的。可让谢胡子来主持也有点问题,那些日子里谢胡子正犯病谢胡子是脑子上的毛病,一会儿清醒一会儿糊涂,清醒的时候便十分地清醒,糊涂的时候便是一塌糊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