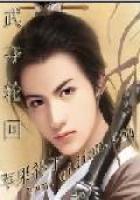乍闻脑中意识提醒,楚天孤瞬间反应,脚步轻晃,侧身闪入身旁的一块巨石之后。而就在刹那之后,一条黑色身影倏忽而至。
来人是一名身着黑色劲装的虬髯大汉。虽然生的粗犷,但脚步轻盈,一路行来并未发出太多声响,显然内家功夫也已小成。
黑衣虬髯大汉走至隧道口旁,惊奇地“嗯”了一声。方要纵身跃入隧道,便见寒芒一闪,一柄利刃便由后颈贯穿咽喉。可怜七尺之躯,未及呻吟一声便已横尸在地。
一击得逞,楚天孤急忙收敛真气,将不羁剑从尸体上抽出收回剑鞘。很显然,这名大汉正是暗中守护着风云山山脚的风云山庄的门客。也正是楚天孤轰击隧道石壁的声响将他引了过来。
想及此处,楚天孤不免对寄藏在自己身体中的那缕灵识多了几分信任。但他未曾想到,自己的心绪波澜早已被对方窥得。
“现在相信我了吗?”
楚天孤没有回答,而是扫视远方,选了一条稍加隐蔽的路径走了过去。
“现在,请先去坠神恶泽内的古藤林帮我取一件东西。”
楚天孤停住了脚步,带着疑惑问道:“去哪里?”
他并不是没有听清,只是这坠神恶泽绝非寻常所在,甚至可以说是一处死地。
坠神恶泽位于西南荒泽之地,其中瘴气弥漫,滕蔓丛生。自古至今少有人出入那里,是故上古时期的毒虫猛兽也多于此处繁衍。到如今,莫说等闲之人,就算满身修为的修士也不敢轻易踏足坠神恶泽。
“你害怕吗?”察觉到了楚天孤的内心,潜藏在楚天孤脑海中的那缕意识激问到。
“哼,笑话。连风云山庄我也敢屠杀还会怕一个小小的坠神恶沼?”楚天孤强作无畏地说到。
“那就好。”
“你要我帮你取什么东西?”
“到时候你看了自然会明白。”
楚天孤不再追问,改口道:“再去坠神恶沼之前我要先去办一件事!”
“你不能去!”
楚天孤一惊,疑问道:“你,你知道我要去干什么?”
“是的,我潜藏在你的脑海,你的所思所想我都能了解。”
自己的内心被别人系数洞悉,楚天孤不免心中发寒。
“既然这样,那你应该知道我对他的恨意。如果不是他,我也不会与南宫奉孝结怨,不会找上风云山庄,父亲更不会就这样离世。”
“你错了。”
“我哪里错了?”
“害死你父亲的不是他,而是你自己!”
蓦然,楚天孤怔怔立在了原地。轻轻的一句话却如同一道惊雷一般击落在他身上。
“若不是因为你的冲动,因为你的意气用事,你父亲根本不会死!”
“就在不久之前,你因为冲动已经害死你父亲一次,现在还要再把自己也害死吗?难道你要让你父亲白白牺牲才甘愿吗?”
一字一句如刀似剑一样割切着楚天孤的内心。没错,父亲确实是被他自己害死的。为了逃避自责,他强迫自己将恨意转嫁到了别人身上。可当这层薄纸被戳破时,汹涌而至的愧疚感更难平复。
楚天孤呆立地上没了言语。那声音遂安慰道:
“等你有能力的时候何愁不能制裁他。但你现在要做的不是被恨意蒙蔽自己。”
默然良久,楚天孤终于缓缓开口说话。
“或许我应该知道今后该如何对你称呼!”
空间瞬间静谧。
片刻之后那意识突然苦笑一声。无垠地孤独汹涌喷发,竟让楚天孤尤感凄凉!
“呵,被遗忘了数万年的称谓又何必再提起。以后,你且称呼我‘前辈’便是了!”
楚天孤不再发问,缓缓朝西南行去。
..
正午,一辆马车出了朝云镇朝南飞奔而去。
朝云镇位于风云山山脚,平日里受到风云山庄庇护,是故一向安乐平和。
烈阳如火,以天地为柴,放肆的燃烧着。六月的天气何等炽热,更不用提是晌午。马车疾驰在康庄大道上扬起阵阵灰尘。车夫手执马鞭,一身麻衣。斗大的箬笠压得很低,将那闪着锋芒的目光紧紧遮住。
这名车夫,正是楚天孤所伪装。朝云镇离古藤林尚有数千里之遥。未出风云山庄势力范围,楚天孤不敢运使真力赶路。且长期暴露于人前难免不会生出祸患。权衡之下,楚天孤不得不伪装成车夫以马车代步。
马车虽是疾奔,可楚天孤仍是觉得太慢,不时挥动手中的皮鞭。那马匹哪敢怠慢,顶着头上烈日,放开四蹄拼命奔跑。汗水从浓密的鬃毛上滴落地上,登时化作一缕青烟消失不见。
楚天孤死死地盯着前方,空旷的道路上看不到一个人影,让这个宽阔的大路显得有些死寂。但这却是楚天孤盼望着的。
此时的世界仿佛是灰色的,而楚天孤就在这灰色的世界里一直向前走着。不知走了多久,一抹淡白闯入了这灰色的世界,打破了原有的死寂。
虽然离得还是很远,但楚天孤清楚地辨认出那是一个缓步行走的路人。
马车继续前行,白影越见清晰。那身姿翩然优雅,彷如惊鸿轻舞。日光照在他的发梢,折射出五彩斑斓的光晕。却如彩虹化作霓裳笼罩在他周身。
那人左手负于身后,右手缓缓摇动一把金箔点缀的白纸折扇。折扇晃动,产生微微轻风。轻风能可吹动他的鬓发却吹不走炽热的天气。他的脸上泛出点点汗渍使得两鬓贴在了脸颊。让他平添了有几分无助。
楚天孤有些同情与他,勒住马缰,停在了白衣男子身边。
突来变故,白衣男子倒也不避不惊。停下脚步,望着楚天孤缓缓开口道:“半路拦阻,小兄弟可有贵干?”
此话一出倒让楚天孤听得一惊。自己全身伪装竟被对方一眼看穿,可语气柔和未显一丝戾气,楚天孤倒也没有太过介怀。
楚天孤将头缓缓抬起,白衣男子全貌始入眼中。白衣男子五官俊朗,面如冠玉。腰间碧玉配饰毫无掩饰地透漏出男子的华贵。
“公子要去往何方?”楚天孤开口问到。
“正欲前往陶州城探寻故友。”
“如此说来咱们正好顺路,时下天气炎热,公子徒步行走定是劳累苦闷,小弟亦要经过前方陶州城,公子若不嫌弃,则请上车同行。”
白衣男子看了看楚天孤。忽的嘴角轻扬,莞尔一笑。笑靥无限温润,如初春细雨般沁人心扉。连楚天孤那厉如锋刃般的目光都几欲消融。楚天孤有些恍惚,天下间竟有如此风度之人。
“如此便谢谢小兄弟了。”
白衣男子将手中折扇轻轻合起,微提衣衫,抬步迈入车厢。动作一贯优雅,雍容不可方物。行云流水般的风姿惹得楚天孤阵阵叹息。
修养资仪如斯,必是世家子弟。这种风度,绝非南宫奉孝那种暴然突起的武界大家之子可以比拟。
待白衣男子坐好之后,楚天孤扬起手中皮鞭重重打在马匹身上,方停歇片刻的马车便又接着飞奔起来。
见此景,车厢不由传来一声叹息。
“呓,小兄弟怜我行路艰辛邀我入车可见爱心斐然,又何必对待马儿如此残忍!”
说罢,轻挥折扇,一阵清凉之风由车厢吹起,吹至马匹周身。马匹似有所懂,欢鸣一声以示感激。
楚天孤道:“我若怜它,便不会驾驭于它。但我需要快些赶路,而他则是代步之物,事有权衡,我也只能如斯。”
那白衣男子缓缓闭起星眸,淡淡道:
“若我所猜无差,小兄弟定有法子能比乘坐马车赶路的速度快许多。我虽不知小兄弟是何缘由选择了这样的行路方式。但既然能忍,何必在乎多忍一刻呢?”
“必须忍耐的我自然要忍,可是无需忍耐的,我又何必再忍?”
“所以便将不忍迁殃至马儿身上吗?”白衣男子又轻叹一声,忧然道:“皆是天地的玩物,又何必苦苦相煎!”
此言一出,无边苍凉自楚天孤心底与脑海无端涌起。莫大的哀痛将楚天孤的心紧紧揪住。手中扬起的马鞭随之缓缓落下。
骄阳无情,烧的更炽。马车上的两人各有感怀。天地再归沉寂,唯剩骏马依然向前奔驰,不曾停歇。
光阴寸寸流失,不知不觉间已是日暮西沉。复行两三里,便见偌大城墙映入眼帘。城门站着两名卫兵,城头镌刻这“陶州城”三个大字。
时下治安良好,卫兵们倒也没做检查便让车马进入城中。
进入城中,白衣男子挑起朱帘,将头探出。左右环顾一番缓缓开口道:“小兄弟暂请停车吧。”
楚天孤闻言勒住马缰。白衣男子从车厢内缓缓走下,朝楚天孤拱手一笑道:“今日劳烦小兄弟盛情搭载,若是以后有缘相遇自会好生酬谢小兄弟。”
“公子客气了。区区小事,不足公子挂记。”
“那你我有缘再见了,请。”白衣男子说完,缓缓转身,朝着远方缓缓走去。
“此人绝不简单。”待白色背影消失在楚天孤视线之后,脑海意识再次传来。
楚天孤未去理会,驾起马车继续向前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