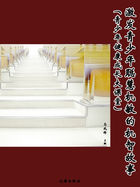普普通通,像这山间的岩石,层层堆积,有的损蚀的厉害,轻轻一捏便碎了,有的正在等待雨水,山风,烈日的侵袭,亦在慢慢老去,可现在仍是磐石一块,坚不可摧。它的身上有一圈纹路十分凸显,像是镶上去的,“轰隆”一声,一道雷光射下,雨水如络绎不绝的珠子叮呤落入人间,随雨滴四散弹跳的还有那巨石,前一刻完好无缺,下一刻便被惊雷击成碎块,那圈奇特的纹路再看不见,只有些不起眼的碎石,它们将随雨水嵌入泥土,继续组成这偌大山体的一部分。这是直插云端的险峰的一段小插曲,它并没有向任何人提起这段故事。雨越下越大。
望着屋檐瓦楞不断淌下的雨水,绿衣女子久久伫立,一动不动,如同石化一般,屋里的小女孩寻她不见,焦急地走出房间,水绿衣裳倒映在她清澈稚嫩的双眸,她展眉一笑,迈着轻快的碎步跑过去,紧紧抱着石像的腰身。石像缓缓转动一下,再动寸许,终于回归灵活自如,重重地咳嗽两声,回身抚摸着女孩笑道:“咱们回屋去,下雨了,天凉。”
那不寻常的一夜后,绿衣女子身受重伤,携着女孩逃出二十里已然不易,由于命悬一线,她并没有注意方向,前几天经人打听方知此处四面环山,进出颇为不便,是以离断水望有三天路程。眼下她走动尚且不便,三天的路程看上去遥遥无期。
“姐姐,你愁什么事情?”女孩巴巴的望着脸色苍白的绿衣女子。
“没什么,你......想家吗?”女子的目光凝在她脸上,试探地问道。
“家?家是什么?家在哪里?”女孩蹙起秀眉,颔首苦思。
“看来她经受打击后,确实忘记一些事情,不过对她而言并非一件坏事,这么小的年纪,唉......”女子想着,温言道:“家啊,家就是有许许多多像姐姐这样的人,疼你爱你,你,想不想去看看?”
“想!”女孩欢呼雀跃,围着女子蹦蹦跳跳。
“那......我们玩个游戏,游戏便是你到‘家’找我,如果找到了‘家’,就意味着找到了我,那么......就算你赢,如何?”女子惨然一笑,不过女孩看不出底下的伤感,忙答道:“好呀好呀,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可是......家在哪里呢?”
“家还有个名字,叫做断水望,姐姐会变成不同的人,给你提示呢。”
“嘿嘿,姐姐,我们开始吧。”
“乖,闭上眼睛,数着屋外的鸟鸣,十声过后便睁开眼。”
女孩依言捂住双眼,仔细听着外面的声响。四周静悄悄的,女子用尽全身力气,以剑做拐杖,缓慢地将自己疲倦的身子拖向门外。
少年在马车上沉沉睡去,彩儿坐在前方,撩开帘子看到他已熟睡,才扭头问:“师叔知晓此中缘由吗?究竟是何人如此心狠手辣?”
“断水望,山清池,常青筑,心眼本为一家,因于自家心法领悟不同,遂分为这四派,心眼派秉持‘以心视物’之道,淡却纷争,隐世修行。”
彩儿皱眉,不知师叔突然说起此事是为何故,粗布衣裳接着道:“断水望,山清池,常青筑却不遵其说,力主祖师所创之秘法并不是令其子弟隐居避世,怀着赤胆忠心作空想,而是超越耳闻目视之一切,以至己身永恒。这两者,本也无错。”彩儿道:“这些却与此间之事有何关系?”粗布衣裳道:“此三派总的宗旨一般无二,于修习之法却又生出不同见解,因此四派隔阂渐生,终于演变为今日江湖中不可小觑的四大流派。心眼一派虽隐居遁世,却也偶尔留侠名于尘间,其它三派不然,争执不休,几百年来从未停止。”彩儿若有所思,揣测道:“莫非?”粗布衣裳不睬,继续道:“争执之源乃是一部祖师传下的典籍,唤作《非言》。”彩儿道:“常青三筑以《非言》一书立足江湖,三百年风雨飘摇仍屹立不倒,反而人丁愈来兴旺,彩儿有所听闻。”粗布衣裳回道:“是了,《非言》一书确是无上宝典,成就三大派无数好手,当然,亦是整个江湖的武功好手,心学之集大成者,而你方才所言,“常青三筑”,江湖间以此流传其名,其他两派焉能心服口服?”彩儿点头道:“三派均以超越为宗旨,是以单只被冠以‘常青’之名,断水望与山清池自然不能认同。”粗布衣裳点头,接着道:“这部《非言》最早藏于常青筑,常青筑近水楼台,实力自然强于其余二派,其它两派亦可参详,但当时三方出于安全思虑,定下此书不能离开常青阁的规矩,即只能于阁内观阅。他们的祖师驾鹤西去后,余威仍波及两代人,几十年内不曾有人提《非言》的归属问题,然而前人终究逝去,青出于蓝的一代心高气傲,自然想将宝典至于己派高阁,于是乎百年争端便由此始。不过......”他心存疑虑:此三派到底师承一家,无非于脸面上分个高低,从来不会大动干戈,更休提杀人屠派!彩儿问:“会是他们自相残杀吗?”粗布衣裳颔首沉思,忽然大骂自己糊涂,紧勒缰绳掉转方向,马儿吃痛发出长长嘶鸣声,彩儿讶道:“师叔你怎么啦?”粗布衣裳问:“方才你可见到一个小姑娘,与这位少年一般年纪?”
人常道:天意使然,天意难违云云,然而天意太过不公,尽折煞鲜活生命,教一腔热血泼在粪土之上,教纯良青年落入泥潭。它强行折断想要突破天意的人的翅膀,打磨成天意喜欢的形状,更美其名曰:磨练。究竟一切在天意之中,还是天意弄人?究竟有一千次的改写便有一千零一次的天意使然乎?
“喂,醒醒”脏兮兮的青年男子一脚提醒躺在街角的少年,“这是本大爷的位置,新来的怎么如此不懂规矩?”周围的看客多起来。
看那同样脏兮兮的少年艰难地直起身子,揉揉眼道:“这......这是哪?”
青年男子有种天下人负他的憎怨神情,再踢一脚,少年应声而倒,乌黑的脸擦着地上的石子,破了一大片,起来时脸上已挂满鲜血。
有位看客大为不悦,道:“好没骨气的小子,这要是搁老子身上,三拳下去准保对方脸上开酱铺子,屁滚尿流地管老子喊爷爷!”几人点头应和,几人讥笑不语,几人朝远处招招手,又唤来几个看客。
“装什么傻?”
“你凭什么打......打人?”少年气愤至极,话都讲不顺畅。
青年再揣过来一脚,少年有所防备,伸臂格挡,奈何身子太过虚弱,仍被打翻在地。
“跟我走!”这时人群中突然出现一个缺口,一个少女十二三年纪,用力拨开前面的汉子,她同少年一样有着脏兮兮的脸庞,但从眼色中看出她下了很大的决心和勇气,似乎还有,憎恶。她跑到少年跟前,伸出布满污迹的手。少年胸中压着一团怒火,不能舒畅,加之身体虚弱,一口气喘不上来,双目变得失神呆滞。少女应是自小在此长大,不似寻常人家女子,力气蛮大,背起瘦弱的少年,顶开人群,在众人极尽肮脏下流的话语下,跑得远远的。
青年神情复杂,不去追,只骂句骚浪蹄子,恨恨地转身离去,看客们炸开了锅,纷纷出言完成他们肮脏的著作。一位汉子道:“这一对脏人儿倒也般配,指不定一会儿那女子怎么勾引他。”一清瘦男子哂笑道:“还用怎么勾引?你家那位怎么勾引你的,她就怎么勾引他。”众人哄然大笑,汉子的身边站着一位妇女,闻言脸色通红,瞥一眼清瘦男子,眼中却无恶意,反而充满无限撩拨,汉子一张脸涨得发紫,当着众人不好冲妇女发作,生怕别人知道他娘子那点风流韵事,叫他更出丑,便出言挑衅道:“你是找死!”清瘦男子笑道:“怕你不成?”又一出话剧开始上演,这次由看客亲自上演,这在此处是常态。人们说,这里是天神遗弃的地方,连鬼魂都不愿在此游荡,这个地方多为各大门派、各大城池流放的犯人所喜爱,称其:“尘世弃我,我不自弃”,赠其名曰“凡人弃”。
少女端来一碗清水,为少年理顺气息,道:“喝了吧,等晚点了我去弄些吃的。”
少年对她心存感激,但蒙受大辱不吐不快,道:“那个人在哪?我找他算账!”
少女道:“你打不过他的。”
少年不悦:“打不过便不打了吗?”
“等你养好身体再寻他吧,这样胜算大些。”
“莫名其妙,我甚至不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便受如此折辱,我咽不下这口气!”
“你,从哪里来?”
“......”
“是我冒昧了,我不该问。”
“不.....我忘记了......”少年使劲锤着自己额头。
“别想啦,快喝水吧。”
“谢谢,这里是什么地方?”少年接过碗。
少女一五一十地诉说了此地状况,少年闷头不语。
少女似乎对这个少年充满了好奇,问道:“你叫什么名字呢?”
少年道:“文远,文字的文,遥远的远,叫我文远就好。”
少女似乎想起什么,急忙追问道:“那你姓什么呢?”
文远又拍着额头沉思起来,这些问题倒是暂时让他不想方才耻辱。
少女托腮笑道:“想不起来便罢了,记得名字便是一件好事,我姓白,叫净凡,他们都唤我脏什么什么的”,少女有意避过那些龌龊字眼,“其实他们不知道,我爹娘给我取了这么好听的一个名字......”净凡说起她的名字,喋喋不休起来,文远心想:你可一点都不白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