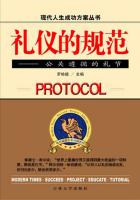“他是我的情报员。他在贝鲁特广交朋友——这对我很有利,因为我在那儿有很多大主顾。即使在过去很糟的天气里他也能随时到达或者离开,他是个远近闻名的优秀电线工人。柯里派给我监视任务时,我就找了汤米。”
“他现在伦敦吗?”
邓菲耸耸肩,突然感到局促不安,“我想他不在伦敦,他已离开市区。”
埃斯特哈齐和莱因戈尔德目不转睛地瞪着他,邓菲却无动于衷。如果代理曾告诫他什么的话,肯定是让他安静地坐着,即便不能这样也要:
否认所有的事情。
不承认任何事情。
要反辩解。
最后埃斯特哈齐打破僵局:“我们先宗主国警察一步找到了他,这一点很重要。”
邓菲点点头说:“我明白。”
莱因戈尔德的眉毛拧在一起,清清嗓子说:“我们在教授的电话上发现了窃听器。”
“我知道,”邓菲说,“杰西曾经提及此事。”
“好,警察认为这与谋杀案有联系。”
“说得对。”
“当然,这没有什么价值。”
“当然。”
又是一片寂静。莱因戈尔德用铅笔敲打着桌子。埃斯特哈齐皱着眉头把烟踩灭,接着摇摇头。
他说:“我认为你最好跟我们合作,坦率地说这对你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邓菲一头雾水。
“但这件事,”邓菲说,“我无能为力,帮不上忙。”
“但是——”
“已做的事是既成事实,”莱因戈尔德说,“关键是窃听器把教授和戴维斯先生联系起来,而戴维斯先生又和你有关联,等等。”
“等等。”
“等等。很难讲到哪儿是个头。”
“这类事情我们可以直奔主题。”埃斯特哈齐又说。
邓菲点头,接着又把头转向一侧,扬起眉毛又落下来。他开始用缓和的措辞为自己辩解:“我明白,但我不知道戴维斯在哪儿。我确实不知道。”
年长的人皱皱眉,耸耸肩换了个话题。“告诉我们教授的情况。”
邓菲咕哝着。
“他为什么会被监视?”
邓菲摇头说:“他们没告诉我。”
“但你听了他的电话对话,你应该会有些看法。”
“没有。”
“无疑——”
“我确实不知道。关于听电话谈话一事你们误会了。我仅仅是在把录音带交给柯里之前,取样检查看上面是否有录音。通过我自己听到的和他们告诉我的,我了解到那人在国王学院教书。看文件上显示的信息,我认为他很可能执教于心理系。”
埃斯特哈齐探着身子说:“把他的情况告诉我们。”
“什么情况?”
“希德洛夫教授主要研究心理学的哪个方面?”
邓菲把这些问询者逐个看了个遍。最后说:“我怎么知道他到底研究什么?”
“好——”
“我告诉你们,他的情况我都是从文件上看到的。”
“你不对你的窃听对象感到好奇吗?”
“好奇?对什么好奇?一个心理学老师?我可不这样想。我唯一感兴趣的就是,据我所知,他是被屠杀的。”
“屠杀?”莱因戈尔德问。
“是的。”
“你为什么要用那个词?”
“相对于哪个词?”
“杀死。”
“因为他不仅仅是被‘杀死’而是被分尸。他的胳膊、腿——他被阉割了。你们想听听我的看法吗?警察应该去食品杂货店挨个问那里的每一个人,看看那天晚上他们在哪儿!因为这不像是杀人而像是切割。”
询问邓菲的人又皱起了眉头,“是啊……这确实很可怕。”莱因戈尔德说。
埃斯特哈齐把脸转过去,他们又僵持着好一会儿没说话。
最后,邓菲开口问道:“这之间有什么联系呢?”
“联系?”
“监视和杀人之间有什么联系?”
“没有联系,”埃斯特哈齐回答说,“为什么要有联系呢?”
“好,那么这真是一个天大的巧合。我是说没人会在电话里谈论机密。监视的目的只是了解这个人在家里的生活起居习惯。他是否养了狗或者猫?如果他养了狗,那么他什么时间遛狗——在哪里遛?他去看牙医吗?去按摩吗?他有情妇吗?”
“邓菲先生,离题太远了。”莱因戈尔德很沮丧。但是邓菲还是不停地说而且越说越快。
“他做了些什么?在哪里做的?什么时间做的?因为——让我们面对这一事实——有人设法在铁轨旁的某个地方找到了他,他们在伦敦的中心行动了——像外科手术一样动刀——直至他成了该死的肢体分离的尸体——他们才离开——”
“邓菲先生——”
“为了基督的名,滚出教堂——”
“杰克——”
“见鬼,我是个嫌疑犯?!你们说没有联系是什么意思?”
邓菲疯狂地看着询问者。他们一句话也不说。时间一秒一秒地滴答而过。
最后,埃斯特哈齐清清嗓子很尴尬地说:“事实上你不是。”
“不是什么?”
“嫌疑犯。”
“你怎么知道?”邓菲问。
“只有等我们找到戴维斯时,才能排除你的嫌疑。你更像是一个,嗯,能够提供重大线索的关键人物。”
“的确是,”埃斯特哈齐说,“他可能需要我们的帮助。”
一片死寂。他们连眼都不眨一下。
最后,邓菲翻转手掌把头顶的灯放下来。“老兄,对不起,我不知道他在哪儿。”
到了下午7点钟,任务汇报仍在进行。莱因戈尔德的手表这时突然尖锐聒噪起来,提醒他这会儿该在别的什么地方。
他们收起笔记,盖上公文包,站起身。“我想你应该就在旅店吃些晚餐。”
“这个主意不错!”埃斯特哈齐插了一句,“享受旅店的送饭服务,可以好好休息一下嘛。”
“我们明天8点钟继续,”莱因戈尔德补充说。
“你看我们能稍微晚点开始么?”邓菲问道,“中午怎么样?”
埃斯特哈齐和莱因戈尔德一脸迷茫地互相望了望。
“我需要换洗衣服,”他解释说,“还有袜子。你知道商店上午10点钟才开始营业。”
没有回应,更别说一个微笑。
邓菲叹息道:“好吧,没问题,我在浴室把它们洗了再穿就是啦。”
于是,他在七楼买了一瓶“护丽”洗涤液,回到房间,浴盆里放满水。脱下衣服,跪在浴室地板上,骂骂咧咧地洗着套衫、袜子和内衣。
他用手把它们拧干后搭在散热器旁边的椅子上。然后坐下来,电视里正在播电影,他要了一个汉堡,裹着浴巾进入了梦乡。
任务汇报第二天接着进行,邓菲穿着还有些潮的套衫,就这样持续到了傍晚,不得不第二次暂停。星期三早上继续,还是同一个内容。
整个过程使人疲惫不堪,心生厌烦,到最后,一切都成了敷衍了事。他们想要的答案,邓菲一概不知,当然汤米·戴维斯的下落,他们是下了决心一定要弄出个眉目。星期三下午,埃斯特哈齐靠着椅子,抬着眉毛说:“我想我们进展得差不多了。”
莱因戈尔德点点头:“我同意,我得说我们该结束这次汇报了。”
几乎是同时,两人站了起来,收起钢笔和便签、火柴和烟。埃斯特哈齐从桌子上拿起表,戴在手上。
想到这场折磨终于熬到了头,邓菲松了口气。笑着将椅子推到身后,站了起来。
莱因戈尔德盖上公文包的时候毫无表情地看着邓菲,“你准备去哪?”
邓菲做了个手势,好像是在说“出去一下”。
“你的事情还没完,”莱因戈尔德说,“我们的任务结束了。”
煎熬中一个小时过去了门才被打开,一个罗圈腿的男人走了进来,手里拿着一对不搭配的公文包,朝邓菲点了点头,就把文件夹摆在桌上,脱去运动夹克,把它小心挂在椅子上。其中的一个公文包很薄,皮质光滑,另一个鼓鼓的,很结实,类似矿渣的灰色。
以一种近乎仪式般的郑重,这位来客从美国旅行者箱包里取出一对血红的东西,放在了邓菲面前。
有一本简装杂志,封面上是一张野性十足的图片,一个身着短裤和露背上衣看起来湿漉漉的金发女郎正跪着擦拭厨房的地板;就在几英尺远的地方,一个丹麦人淫荡地望着她。书的名字,邓菲注意到,叫《男人最好的朋友》。
第二件物品是个小型镀金的耶稣神像,耶稣的双目从血棘王冠中仰望着天堂。邓菲看了看这两个东西,晃了晃脑袋,哼着鼻子对这些廉价拙劣的心理测试表示不屑。
这个罗圈腿男人眼也不眨,打开塑料公文包从里面的仪器里拉出一根电线。然后转向邓菲,双手支着斜倚着桌子,向神像点点头,低语道:“我知道你做了什么,我知道你所知道的,你对我撒谎,你个混蛋,你敢对主撒谎,现在卷起你的袖子。”
接下来这一天,可以说整个星期三,就是对邓菲的整个职业生涯的一连串模糊的提问。当然这项测试对邓菲毫无意义,每一位受过职业训练的官员,虽不能说能彻底攻破测谎仪,却至少可以干扰它的结果。假如测试足够长,就像邓菲现在面临的这个,想要通过它将会是个耗精力的过程,要求被测试者长时间保持相当高度的精神集中。困难有,但并非没有可能应付过去。当需要隐藏有价值的信息时这样做完全值得。
诀窍就是利用问题和回答中间的那个空隙。这个空隙通常会被测试者刻意延长以便更好地获取被测试者的流电感应。若要通过测谎仪,你必须为真相创建一个虚拟基线。做法就是在每一个真实的回答中融入定量的压力,使得那些答案和谎言混淆起来无从辨认。
生成压力不难,你只需要一点算术,也就是在每一次作答前做些类似14乘以11这样的乘法运算。然后,该你撒谎的时候,你可以不假思索地撒谎,这样出来的结果或多或少都是一样。
测谎仪操作者就只能得出结论:要么你对每一件事都在撒谎要么你说出了全部事实。既然有些问题的答案是已知的,那么推理出的结论就是被测试者是诚实的。
“今天是星期三么?”操作员从一个电脑打印出来的复写簿上读着问题。
邓菲想了想,16乘以9是……90加54:144。“是的。”他说。提问者在问题的旁边画了对勾。
“你去过伦敦么?”
14乘以12是……喔,140加28:168。“是的。”又一个对勾。
测试就这样进行着。
“你熟悉合体字母MK-IMAGE么?”
27乘以8:216。“不知道。”邓菲说,并刻意用脑子记了下来。他的算术越来越好了(可到底什么是MK-IMAGE呢?)。
“戴维斯先生离开伦敦当天和你联系过么?”
341除8是……42——邓菲的脑子一片空白。42或者其他什么数。42和……零钱。”“是的。”邓菲说。又是一个对勾。
“他告诉你他去哪里了么?”
邓菲再次使大脑呈现空白状态。“没有。”他说。一切照旧。
又一个小对勾。
邓菲胜券在握。
邓菲晚上回到酒店,装有他用过的护照、钱包还有衣服的箱子已经在门口等他了。还有一个装有牙刷、剃须刀、一大把收据、梳妆台上的零用钱、梳子、其他杂物的塑料袋。上面用黑色的标记笔写着:私人物品。这让邓菲有一种怪怪的却又似曾相识的感觉。原来如此,他突然想起,人死的时候都这么来标记物品。
他们把你的牙刷、零用钱一起装袋然后送到你最近的亲属那里。由于极度疲惫,邓菲坐在床上,躺着没多久就睡了过去。
响个不停的电话铃声把他从沉睡中叫醒,他已经睡了十个小时。电话那端的声音通知他明天立即去中情掩护部报到,而且要随身带上所有的证件资料。
邓菲照电话里说的,如约前往。一位头发花白的黑人官员手里拿着一份清单,要求收回克里·索恩利的护照,他的爱尔兰驾照,以及所有口袋里的其他物品。清检过的每一件物品都从清单上被划除,随后就放进了一个标有焚毁字样的金属篓。
他第一次清楚认识到以后自己再也不用为中情局去英国执行任务了。
昏昏沉沉中,他乘上电梯来到了人事管理部,在一个石灰绿的休息室里翻着一本破旧的《经济学家》,坐了将近一个小时,终于有一位身穿制服体态较小面相老练的女人走了过来,告诉他现在B-209将是他暂时的办公室。
邓菲对总部再熟悉不过了,可……“这个地方在哪?”
“我不太清楚,”她说,真的被问住似的,“你得问一下保安。”
其实B-209位处北区的地下室,两个码头中间宽阔的走廊上。这条走廊也兼做仓库用来放置电脑设备、办公用品,还有(这一点邓菲马上意识到了)挂在国际事务分部下面的乱七八糟的小机构和准军事机构。
铲车组沿着走廊从一个码头隆隆驶向另一个,彼此间或是和墙壁时常发出猛烈的碰撞噪音的缘故,人们在这里说话比在总部其他地方嗓门更高些。当然处处也少不了同事之间的插科打诨。这在邓菲看来就像是一团睾丸激素笼罩在走廊上空,让人想起缅因州乡村小径中出现的鬼火。根本无法在这种地方思考,如果真有事情要想的话。不过现在是无事可想,他已被监控。
他的办公室是个浅黄色的小阁室。数不清的隔离物作为滑动门。房内配有一把米黄色的旋转椅、一个衣架,以及一个米白色的书架。屋角还有一个空的文件柜,就在旁边放有一个垃圾焚烧篮。
地上还有一部电话和一本《罗杰斯辞典》,却没有地毯,说得更直白点,没有任何桌子。
邓菲拿起电话想叫房间服务,却没有拨通。一阵恼火,他怒气冲冲地走出这个小阁室(你真的无法称它为一间屋子)直奔人事部,却在迷宫一般的走廊里迷失了方向。接下来情非得已的问路让就在这里工作的邓菲感到尴尬无比,就这般忍受着屈辱,他来到了人事部,满腔怒火,却在眼前这位身着制服瘦小阴沉的女人同情地耸肩面前蔫了下来。“要耐心,”她说,“他们在整理东西。”
邓菲抢过一部电话要求总机帮他接通他的部门主管——弗莱德·克里斯曼,现在策划署。只有弗莱德能告诉他发生了什么,邓菲通过杰西·柯里向他汇报情况长达一年之久。
“对不起,小伙子,”电话那头传来一个声音,“真不巧,弗莱德上个星期就去了东非。”
邓菲拨了另一个号,可他要找的人都不在:开会中,不在办公室,外出旅游。
勤务员说他将传达口信给这些人,语气就像旅店工作的客房服务生,然后允诺马上给他电话。“你怎么给我电话?”邓菲问。“我告诉过你,这部电话根本不管用。”
茫然郁闷中,邓菲一天的生活就这样开始了,从办公室溜达到人事部,从人事部到餐厅,从餐厅到健身房。每天如此。他在里面跳绳、举重、打打拳击。一周过去了。两周、三周,他的肌肉越来越结实。犹如一个技术官员版的体育健将,不为人知地在这座官僚机构空旷的大厅里整日闲荡。到了下午,他就来到局里的图书馆,那里可以读到来自世界各个角落最近的消息。每天都舒舒服服地坐在同一把椅子上,邓菲搜读着英国媒体有关希德洛夫教授的报道,却一无所获。第一行新闻标题过后,有关调查的报道就消失了。
这让邓菲怀疑英国政府已下令封杀了该消息。因为愤怒和焦虑,他的胃开始翻腾。最终,事情的真相会在某一天水落石出,可会是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
又会牵涉到哪些人?一切都未知。
邓菲厌倦了弗吉尼亚北部的泰森斯角旅店。他想念在切尔西的公寓和在那里度过的日子。那才叫生活。他最想念克莱姆,除了说些“我在潜逃,到时会联系你,再见”,真的,他什么也无法对她讲。这让两人的关系没有了基础。他可能再也不能返回英格兰,更别说见到克莱姆,这个想法让他胆战心惊。
正如二战后中情局的处境,因为敌人的投降,使得中情局在冷战过后消极涣散,士气全无。因为不再有合适的任务,存在也变得岌岌可危。这些年,在没有匹敌对手的情况下勉强运转,靠着设法对付曼努艾尔·诺列加和萨达姆·侯赛因之流的顽固头目,还有在逃的恐怖分子和一些在逃的哥伦比亚亡命徒。现在,国会开始蠢蠢欲动。有人放话要在局内裁员,“重新分配稀有资源”。资源中最昂贵的当属没有官方掩护的特工,或叫NOC,邓菲就是。他们逐渐从战场中被撤回,接着就被来自五角大楼人工智能防御部的神出鬼没的家伙们取代。
中情局自成立以来面临第一次的预算危机。兰利小区不再是个让人开心的地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