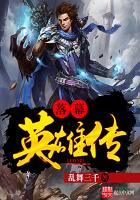走进店里的一扇小门,光线即刻黯淡下来,一如一个人幽闭的心门里的寂静。白泽兰觉得有什么东西擒住了自己的胸口,喘不上气来的难受。
走廊很长,又狭窄,只有窸窣的脚步声在回荡。大叔停在了离拐角的倒数第二个房间门口,推开门,声音低沉的说:“进去吧。”男孩在身后,怀里持着枪,脸色淡漠,没有停下或者解释的意思。白泽兰深吸一口气,跨进了房间。
房间里的灯光较走廊更加阴暗,一盏悬浮灯憔悴的浮在房间的中央,看样子好像随时会熄灭。墙上乍一看十分脏乱,仔细观察,才发现那上面满是黑色线条笔画上的涂鸦,小丑的脸,哭泣的孩子。
房间里简洁的过分,除了悬浮灯以外,就只有一张白板床,白色床单,如同医院里的病房。床上躺着一个人,那人用被子蒙着头部,看起来是个成年女人的体型,只是床上的人正在不正常的颤抖着,发出意义不明的呢喃声。
白泽兰敏感的注意到,大叔脸上万年不变的淡定,从一进房间开始,就带上了一丝丝温暖的色彩,像一股暖流填满了他钢刻般的皱纹。
他慢慢低下身子,跪在地上,用双膝在地上行走着,慢慢靠近那张床,以及床上的人,他的脸上有着最虔诚的爱人才有的温柔,他轻声地唤着,就连气息都是轻柔的:“宝宝。”
“我来了,宝宝。”
女人从被子里探出头来,被单落下,露出一张纵然韶华已逝,却依旧倾国倾城的脸庞。黑色的柔顺的长发滑落,带着一丝天然的妩媚神色,但那眼神里分明装满了单纯与不谙世事。
她看到了靠近她的男人的脸,突然痴痴的笑起来:“小白,小白,你是小白。”
笑着笑着,眼泪就从她白皙的面庞上淌下来,美人泣下,一时间似乎连天地都变了颜色:“不,你不是,我的小白已经死了。他再也回不来了。”她哭起来,又用被子蒙住头。
她哭得竭嘶底里,却把全部呜咽都埋在了雪白的被子里。
“宝宝,我在这里,我一直在这里。”男人脸上带着浓的化不开的愁郁与疼惜之色。
女人突然抬起头,眼睛里带着恨意:“你杀了我的小白,你把我的小白还回来!”她一口咬在男人的肩上,手脚扑打着,男人忍耐着,动作轻柔地抱着她。他轻轻地安抚着怀里的人儿,像对待一个婴孩。
白泽兰耐心的看了这出八点档情感大戏,心里没有一丝波澜。她看的太多了,在她短暂的生命里,这样的死去活来可以说是家常便饭,每年每月甚至每星期,总有那么几个痴情种子来找她解梦。有的人希望解开心结,有的人选择一忘皆空。在白泽兰看来,如果纠缠只剩下伤害的话,那么放手就是最好的选择,婴孩就什么烦劳都没有,何必呢,作死呢,最后的恨常常都来源于最开始不加束缚的爱。
没有人需要谁,没有人离不开谁。解梦师总是站在一个旁观者的角度,用最冷漠的目光去剖析,用最冰冷的语调去嘲讽,越狠就越成功,越无情就越能影响梦境。
解梦师只有一个执念,那个执念关于自己,不许人触碰,也永远看不开。
女人终于打累了,睡着了,又恢复了孩子一样的睡颜。大叔将女人放回床,温柔的盖好被子,抚平床脚。再轻手轻脚的从房间里退了出来。
他们又回到了狭长的走廊上,大叔走在前面,男孩走在后面,白泽兰被夹在中间,没有人告知她什么,她自觉的闭上了嘴,跟着大叔又走进了斜对面的第三间屋子里。
这个房间依旧简洁,只是没有哭闹的女人,却显得更加的阴森。墙壁上挂满了武器,一面墙上全部是各式各样的匕首,另一面则挂满了枪支。墙角堆着炸药,唯有房屋中间是空白,放置了两个塞进了毛绒填充物的老式橡胶轮胎。
“这里面都是炼金武器,可以用灵力加成,使用它们,不会引发学院防护罩的警报。”大叔自顾自的坐到了一个轮胎上。
“你跟我说这个干吗?”白泽兰警惕的问道,仍旧站在原地。
“坐吧,”大叔平淡的说,“你会需要一把的。”坐下来就告诉你原因,他言下之意如此。白泽兰只好乖乖坐下,男孩进门之后将门关好,像个保镖一样,持枪伫立在一旁。
“有人想杀你,或者说,有人想让你离开防护罩的范围之内。”
“你怎么知道?”白泽兰有些意外,男人让她见到了那个女人,却又提起别的事。白泽兰当然知道有人想让自己离开这,她就从来没有停止过被追杀的命运。
“昨天,全温港的佣兵与杀手接到了一个近几十年来的最高悬赏,就是杀死你,或者逼迫你使用阴阳术,被迫离开温港。我也在通知之列。只是他们不知道我的身份,我当这个武器店老板当了几十年,几乎没有人知道我是解梦白家的一员。”大叔这时终于表明了身份,只是语气淡淡的,就如同在谈论天气一样自然。
你身为家族成员正在劫持家主啊混蛋!这么淡定真的好吗?白泽兰抽搐了一下嘴角,竟然无语以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