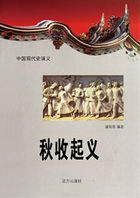而在这里,条件不允许他们以城池的方式围居一起,但又不能分散力量,于是就出现了长达数千里的土碉建筑群。
清朝时,赵尔丰率军进入西藏,就曾利用这些土碉和藏军进行战斗;而藏族人在1904年抗击英国军队时,这些土碉建筑也再次发挥了作用。
永远吉祥,驮负神音的圣地歌声
在拉萨往西往阿里地区去和往聂木拉的去的分路口处,有边防人员例行检查过往车辆。我下车后突然发现雍强的车也在那里停着,就上他的车前往萨嘎--日喀则地区最西北的一个县。
雍强来自宁夏中卫县香山脚下,酷爱学习,尤其是历史和社会学方面的知识;
4年前中学毕业后由于家境贫寒他只能辍学,随舅舅赵兴敦、赵兴忠前往西藏,给日喀则石油公司开车。这是我第一次坐他的车。在车上,他给我讲述沿途的风土人情。比如到了桑桑,他说这虽然是个小镇却是整个西藏出酥油茶最好的地方;到了昂仁,他又特意停车让我了解这个“中国的藏戏之乡”。法国藏学家石泰安在其《西藏的文明》一书中说:“西夏王朝的奠基者、木雅的掌权家族在王朝覆灭和被成吉思汗征服该地(1227)之时,曾迁移到了藏地以北和昂木仁一带。该家族还把其国和与此有关的宗教民间故事也带到那里。”藏族学者桑珠在《西夏王族迁入西藏时间献疑》一文中也指出,石泰安所说“木雅的掌权家族”即是指后藏的木雅司乌王族,拉堆县就在今日喀则地区昂仁县境内。拉堆在阿里和后藏交界处,以雅鲁藏布江为界,分成南北二部分。“这一支西夏人以终昂木仁寺为中心,在后藏形成了一个较有势力的地方割据集团,是元代皇帝诏封的乌恩藏十三万户之一。”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黄领教授所撰《藏文史书中的弥药》一文称:西夏国被蒙古灭后,王统虽绝,但是其后裔仍然存在。如多吉表布之子南喀甸巴就从元朝得到“宽头第三宝国公”、“大元国师”名号及玉印。他卫护萨嘉及昂仁诸寺有功,其孙辈还得到“司徒勤国公”及“灌顶国师”等职务。其他如查巴达泰领古薛禅汗之旨,取得宝印及司徒之职,修建了北昂仁大寺;其子多吉衮波袭父职,掌萨迦本勤之职,声名极隆。
“天地来之不易,就在此地来之;寻找处处曲径,永远吉祥如意。生死总有定论,祸福因缘而生,寻找处处曲径,永远吉祥如意……”听见这首藏歌时,我已经走近了圣地喜马拉雅山。
从日喀则到聂拉木,中间经过珠穆朗玛峰所在的定日县,有几百公里的路程,走起来相当坎坷。我这次搭乘的是许师傅的车,持续一夜地行车,到达定日是第二天中午。在一个小饭馆里吃了点饭后,许师傅倒头便睡。我开始调查这里的夏尔巴。
在喜马拉雅山下,年轻的向导边巴告诉我,居住在山那边尼泊尔境内的夏尔巴,和他们一样都是“来自东方的人”,是从西藏翻越喜马拉雅山移居过去的,在语言、文化和宗教上都和他们相似。山居生活使得登山爬高成为他们的生存技能,1953年腾辛·诺尔基陪同新西兰人希拉里初次成功攀登珠峰峰顶而使夏尔巴名扬四海。从那时起,由于人们对珠峰的向往,登山爬高成为夏尔巴的经济资源。而且尼泊尔境内的夏尔巴在登山协作方面和由此带来的经济收入要强于中国境内的,主要由于开放程度的差异。属于尼泊尔的昆布地区已经建立了萨加玛瑟国家公园,夏尔巴在那里建立了一个相当完善的徒步旅行企业。
腾辛·诺尔基站在地球上最高的地方,留下了这样一段话:“我看到了前所未有、今后也不会再看到的景象,这种感觉既美好又恐怖。当然,恐惧不是我唯一的感觉,我太热爱这座雪山了!对于我来说,峰顶上所见到的不仅是岩石和冰,所有的一切都是温暖的、富有生气的。”后来的岁月里,当儿子向他表达要登顶的愿望时,他这样回答道:“我已经替你上去过了,你不必亲自登上峰顶。”
关于腾辛的国籍一直存有争议,印度声称他是印度人,尼泊尔则声称他是尼泊尔人。真正揭开他身份之迷的是由美国登山家埃德·韦伯斯特2003年创作的《雪国》一书:腾辛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人,他生在西藏!
希拉里事后介绍说:“我们登顶成功后,英国向腾辛发出访问邀请,但他遇到了麻烦,因为他没有护照。”这个时候,印度总理尼赫鲁亲自出面,私下保证腾辛将拥有印度护照。这样,腾辛终于踏上了英国之旅。
腾辛的儿子诺尔布后来随登山队进入西藏,找到了一些早就失去联系的亲友,包括腾辛同父异母的弟弟塔什,解开了他父亲的出生地之谜。位于西藏的卡马山口有一座“纯洁之神的宫殿”,围绕着寺院的是一大片牧场,站在牧场上可以清楚地看到珠穆朗玛峰。这里就是腾辛童年玩耍的地方。
看到起伏的群山和飘拂在山巅的经幡,我更能体会到夏尔巴的悠远和神秘。
走在寂然的喜马拉雅山下,我忍受着饥饿、孤独,没有任何补给,没有人对话,孤独的行走常常被找不到方向带来的巨大懊丧淹没。到了晚上,气温急剧下降,躺在睡袋里有时会在半夜里冻醒,看着寂静的喜马拉雅山脉横在眼前,天地一片沉默,星星仿佛伸手可摘,人和天地似乎融合在一起了……
从“地狱之门”到“云朵上的米尼琪雅”
寻找夏尔巴,他们和党项人究竟有着怎样的关联?我继续向西藏大地深处挺进。
茫茫夜色中,只能看到聂拉木的大概轮廓。聂拉木,在藏语里的意思是“通往地狱之门”,是说地理气候恶劣,平均海拔4300米,年平均气温3℃~5℃。在这里徒步行走,相当与在内地负重25公斤的运动量。这时我既饿又冷,浓重的睡意使我对睡眠的需求超过了一切,住宿的地方选在了县委招待所。招待所里只有一个藏族女孩,她不太会汉语,只能简单而生硬地报出住宿费,除此之外再也说不出第二句了。
早上起来,我开始在这个县城转悠。所谓县城也就是有一条很短的大街,从头到尾几分钟就走完了。这是个袖珍县城,大街上的人很少,来旅游的外国人比当地的藏族人还要多。
我又上路了。车上有懂汉语的人问我来自哪里,到樟木做什么?旁边一个藏族打扮的年轻人,一听我是做夏尔巴采访的,当即和我搭话。这位叫普布赤列的年轻人说,他就是夏尔巴。他在济南上学,毕业后分配到县文教局工作,他利用周末时间带着妻子去一个温泉洗澡。
普布赤列解释道:“夏”是东方或来自东方的意思,“尔”是语气词,相当于汉语中的“的”,巴是“人”的意思。
“我们夏尔巴是外来的,搞不明白当初我们的祖先为什么来到藏族地区。夏尔巴和藏族人有着明显不同,和尼泊尔人也明显不同。我们希望你这样的人来做个调查,把事情搞搞清楚。”
车越行越慢,在短短的几十公里内,海拔下降了1000多米。路紧挨着山体,外侧就是万丈悬崖,1000多米的山脚下有一条美丽的河流,像一条蜿蜒的白丝带弯弯曲曲地切割着米尼雅山。满眼密集的原始森林,云雾环绕在山间。
出门这么些天了,一路尽是一片枯黄,突然间出现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反差太大了。它的遥远与神秘,更适合一个逃亡民族的生存与隐蔽。这一点加深了我对西夏党项人后裔中的一支逃亡到这里的判断,而随后几天的走访成果更是巩固了这一判断。
车上还坐着一个夏尔巴少年,和他交谈得知:村里没有学校,夏尔巴孩子上小学得到镇上住宿;等小学毕业了,要到县城里去读初中;而上高中则要到几百公里外的日喀则。后来我发现,这里不少的夏尔巴都把孩子送到近处的尼泊尔去接受教育。
樟木的下午是绝对值得珍惜的,否则就是一种罪过。这里生活很本真,充满了在淡淡的阳光下悠闲地走在街道上的恬然。到处可见用头背负物品的夏尔巴、背着擦鞋小箱子转悠寻找生意的印度人、跑来度假的尼泊尔大学生、土著居民则坐在临街的铺面喝奶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