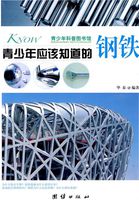天祝,突破祁连山东麓的僵局
古羌人离开析支后四处流徙,其中的一支向西走,翻过阿尼玛卿雪山和西倾山,将生存触须伸向青海的深处,在美丽富饶的玉树草原上生衍繁息。在这里,他们和汉族政权、吐谷浑政权、吐蕃政权展开生存之战。越过大夏河向北,羌族的一些支脉分布在青海东部和甘肃中部,甚至有的到了河西一带。后来都归入了西夏王国的版图。沿着白龙江迁徙的一支大体以松潘一带为分水岭,又分成两支:向南的一支进入摩梭河谷地,成为今天中国最大的羌族自治州的主体部分;向北的一支由甘肃陇南一带向天水、陕西一带进发,构成后来建立西夏国的主体民族党项族。
1996年夏,我从景泰出发,翻过绵延数百公里的寿鹿山大森林和山顶终年积雪的马牙雪山,经甘肃的皋兰、永登、兰州,前往天祝--中国最东边的一个藏区及千里河西走廊最南端的一个县城。天祝藏族自治县属武威市,是当年西夏人和吐蕃人交锋的最前沿地带。从位于兰州红古区的吐鲁沟出来,就是甘肃和青海交界的大通河--黄河上游最大的支流;进入大通河谷就能立即感觉到这里和外界的距离,会被一种巨大的幽静包围着。天祝是我国最早成立的藏族自治县,它的名称是由天堂寺和祝贡寺两大寺院各取一个字而组成的。其中,天堂寺在人迹罕至的大通河畔深处。历史上的西夏对这里没有进行过有效的牢固统治。在天堂寺里朝拜的藏人,他们每磕一个头便从身边的一个小布兜里拿出一个小石子来,嘴里念念有词。后来我才知道,他们没有数字概念,根本不知道或许也不想知道自己这样一场朝拜下来要磕多少个头--兜里的石子取光了,就证明自己当天要磕的头磕完了。那些牧人也是如此。每天牛羊出圈时,羊出一只就拿出一只小石子来,羊出完了自己的石子也拿完了,就证明羊没有丢;羊出完了石子还有剩余的话,就证明羊丢了,就得回去找羊。
2005年8月末,我再次来到这里。10年的光阴刷洗掉的是青春狂狷之气,进入天堂寺时我有了一种物是人非的感觉。10年前我来这里时,和当地知名的诗人靳万龙相遇,那时他是天祝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如今他在城建局担任副局长,他给我介绍了当地的一位藏族朋友让智澳登(汉语是“快乐阳光”的意思),汉族名字叫“李生云”,是天祝县文化馆馆长。我这次来有了意外收获。李生云告诉我,文化馆里收藏着两件西夏文物,其中一件是西夏扁壶,经过专家辨认是军队用的,证明西夏军队曾经到过这里。这个结论打破了以往研究者一直将追寻西夏的目光停留在祁连山以东的“僵局”,这对西夏疆域西界的认定也有着重要意义。
河西门户,西夏陪都--武威的身份
天祝往北,过了古浪峡,就进入了当年的西夏陪都武威市。武威位于甘肃省西部河西走廊东端,南靠祁连山,北抵腾格里沙漠,东接古浪石峡,西临茫茫草原。这里是河西走廊开发最早、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一片绿洲,这里属冷温带大陆性气候,土地肥沃,石羊河水系全境覆盖,灌溉十分便利,适应多种农作物生长,自古就有“凉州不凉米粮川”之说。因而,武威也是西夏人在黄河右岸第一个要极力征服的地区。《西夏书事》中说:“黑山峙其东北,黄河绕其西南,地方二千余里。”武威在西夏王朝统治者眼中的地位是“羌戎之都会,屯守之要区”。武威地位的形成更多是基于丰裕的物产和良好的地理气候条件,当然也与这里“武力威震河西”的军事位置有关。
李继迁把自己的出生地陕西米脂县当成了党项人百年流徙的最东点,他把目光转向富庶的鄂尔多斯高原,很快夺取了此地;深远而辽阔的蒙古大草原没有淹没李继迁的欲望,更加富庶的宁夏平原吊起了他的胃口。于是,马蹄西移,灵州战役,宋王朝在自负中失去西北的军事重镇,西夏为立国奠定了最坚实的军事基础。夜渡黄河,李继迁看到了足以为一个新帝国提供物质基础的凉州。1003年,李继迁攻下了凉州;不久,又被吐蕃部的首领潘罗支用计夺回。这一次,党项人失去的不仅是一个重要城池和向西扩张的基地,更重要的是失去了一个杰出的领导者--李继迁在凉州战役中中箭身死。
1032年,李继迁的孙子李元昊继位。李元昊采取与宋王朝缔和政策,以求自己进行军事力量上积累的时间。同时他又竭力攻打凉州,还西攻回鹘,南打吐蕃。他对河西地区“经谋不息”,他的誓言是不为祖父报仇、不夺下凉州就永不立国。最后他终于将吐蕃人从这里赶了出去。东边河套平原的“塞上江南”和西边千里河西走廊南大门的“银武威”,像两条血管源源不断地给西夏王朝输送能量,持续了190年。由此武威成为西夏王国西境最大的城市和军事据点。1036年,李元昊夺取了瓜州、沙州、肃州等整个河西之地,完成了他所立下的誓言。直至1038年,李元昊正式称帝,定国号为“大夏”。
西夏对武威的长期占据,而且将其作为陪都,使得这里在西夏国中的地位仅次于银川,因此也留下了很多重要的见证物。两百年前,著名学者张澍前往武威的大云寺游历,无意中发现了一块石碑上刻着一些古怪的文字,他一个都不认识。等绕到石碑的背后,他看到了汉字,根据上面记载的年号,他终于弄明白原来石碑正面上是失传已久的西夏文字。它的出现,揭开了西夏研究的一个新时代。
这里还出土了今人破译西夏王朝的重要依据--《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碑》。这块碑最早是在武威的护国寺内,现存武威市的西夏博物馆内。在宁夏博物馆和西夏王陵博物馆内也都有《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碑》的复制品。原碑凿刻于西夏天民安五年(1094),是西夏文碑刻的珍品。该碑文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未见于史籍记载的珍稀史料,同时对于研究西夏文字也是极为宝贵的素材。1996年秋,我第一次到了武威,认识了对当地风俗颇有研究的《武威报》记者李学辉,随后的几年里我又相继认识了诗人谢荣胜、邱兴玉,以及彭斌山、何学平等诸多朋友。正是在他们的帮助下,我在往西夏的河西深处走进时少走了许多弯路。
武威是农业和畜牧业的理想基地,加之其战略地位的重要,极大地促进了西夏王国的巩固和发展。直到近些年,武威人才刚刚开始认识到作为陪都的武威在西夏历史文化上的地位。在当地学者和文艺工作者的大力呼吁下,武威投资252万元于2001年建成了西夏博物馆,与武威文庙毗邻,主体为二层仿古式建筑,主要展示武威出土的西夏文物。
现由西夏博物馆收藏的西夏文物有3000多件,其中有西夏文与汉文对照文字最多、保存最完整的西夏碑,有反映当时建筑水平的西夏木缘塔,有造型简洁古朴、具有民族创新特色的西夏铜壶,有反映当时精湛手工艺制作水平的西夏金碗、金链,有全国现存唯一的西夏容量器具金撮,有反映当时银币流通的西夏银锭,有记载西夏经济发展状况的《西夏文书》,有记载西夏商业活动情况的《西夏卜辞》,有反映西夏佛教发展的西夏文泥活字版佛经《维摩诘所说经》及其他各类西夏文经卷,有反映当代贵族生活的西夏木版画,还有大量的西夏木器、瓷器和金属制品。这些都是研究西夏历史的重要实物资料。
2005年8月,甘肃省西夏文研究专家陈炳应在研究武威天梯山石窟的西夏文佛经时发现其中有两页可能是木活字版印刷品。一个月后,陈炳应参加在银川举办的第二届国际西夏学研讨会,他告诉我说:“武威的天梯山石窟出土了许多佛经,只有这两页上面有题款,还是西夏皇帝的尊号,所以可以明确断定年代,一篇是《圣观自在大悲心总持》,一篇是《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下卷》。”他所说的题款,是夏仁宗的尊号“奉天显道耀武宣文睿智睦懿恭皇帝重敬施”。从这个题款可以看出,这件木活字版西夏文佛经的印制时间是在1139年6月到1141年8月间。1988年夏,武威县新华乡缠山村的村民们在修复祁连山北麓古寺亥姆洞的施工中发现了一批被压在地砖下的西夏文经书。当时村民们见那上面的字奇形怪状的没有一个人能认识,都以为是神书,怕招来灾祸,于是就一本本地投向了火中。仅剩的几本被一位老人藏在石缝里,其中一本后来转到了在武威文化馆工作的孙寿龄手中。孙寿龄初步鉴定这本《维摩诘所说经》是西夏仁宗年间泥活字印本。1988年3月,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确认其为中国11世纪中期的活字印刷本,应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从武威往西走,沿着千里祁连山,这条路我已经走过多次了。当年,党项人在这里和吐蕃人、回鹘人、汉人乃至后来的蒙古人展开拉锯式的争夺。争夺最激烈的地方就是张掖,古代称为甘州。“金张掖,银武威,铜高台”的说法可以证明这里曾经的富庶;今天的甘肃省得名,就是取了甘州和肃州(今甘肃酒泉)的字头而来的。1028年,一场能够充分见证李元昊运动战天赋的战争就是爆发在这里。勇猛的党项人第一次没有采用以往凭借勇毅和对手正面冲突的方式,他们在年轻的李元昊带领下长途奔袭,突然包围了回鹘占据的甘州。经过一番激战,这里从此并入了党项人的领地。从此,党项人也彻底解决了一个新兴帝国所需的粮食及畜产基地的问题,他们在这里完成了建国的物质储备,并为继续向西、向北推进奠定了基础。中国有许多地名都蕴含着不凡的来历。当年,汉武帝派霍去病西征匈奴,占据了祁连山下这块富庶之地。汉武帝像对待其他地方一样,战争一结束就在当地实施文治,设张掖郡,取“断匈奴之臂,张中国之掖”之意,张掖之名由此而来。在漫漫历史长河中,张骞、班超、法显、玄奘等都曾在这里留下过身影。隋炀帝在西宁战役后,由此往西巡视自己的疆界,当他来到张掖时,立即被这里所吸引,曾集西域27国在此举办过“博览会”;元朝时大旅行家马可·波罗也曾在这里停留过一年之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