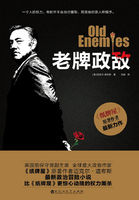侯宝斋在衙门的大牢里见到三个人犯,已经挨了一顿饱打,萎萎顿顿靠墙坐着。一个年岁稍大的是头,姓韩,另外两人叫他“韩二哥”。另一个白白净净,年纪很小,面容消瘦,长的有几分像戏台上的小生,名叫张跃廷。还有一个年纪也不大,相貌丑陋,小眼睛大嘴巴,鼻孔往上翻,但这个人身材魁梧,一看就是那种光长肉不长心的人。他姓霍,不知道叫什么名字,衙门里的人问他,不吭声;打他,挺直了胸膛让你打,大家就叫他“霍笨”了。
许伟仁、覃吉之等人问了凶犯半天,只知道他们一行四人来自川南古蔺一带,走州过县卖艺为生。今天在花桥场耍把戏,碰见了从成都府运送官银的队伍,就心生歹意,动起了歪念头。要知道,抢劫官银的囚犯,如果押到成都府,多半是一个“斩立决”。
每月三、六、九,花桥镇逢场。这天上午,场镇上人流如织,嘈杂喧嚣。四个走街串巷耍把戏的汉子到这里扯圆了场子。该场因为石桥栏杆雕饰有花草,故名“花桥”。场镇距县城十多里,是新津到成都的必经之地。
由于交通优势,在清代已经发展成为一个繁荣兴旺的城镇,店铺鳞次栉比,五行八作一应俱全,商业之盛,仅次于县城。
四个卖艺人周围有一大堆观众。他们舞完一套大刀,博得了一阵阵喝彩声。特别是韩二哥的铁砂掌功夫非常地道,劈砖就像劈豆腐一样,断砖残块到了他厚实的手掌中,捏捏就成粉末了。
花桥十三公口的堂口设在街中的“怡园”茶社内,公口的一位管事杨绍德正跷着二郎腿,把茶碗里面的茉莉花瓣轻轻吹开,井水甘爽清冽,用之冲茶别有一股幽香。杨绍德是当年那个叱咤风云的杨督生的侄儿,此人身材瘦高,性情强悍,双目寒光射人,两只手形如鹰爪。他多年练成了一手大力鹰爪功夫,在当地掌红吃黑,乡人多有敬畏。但是这个人长了一副滑稽的胡须,不但分叉,还往上翘,所以本县人就叫他“杨猫胡子”。
杨猫胡子呷了一口香茶,他看了看几个耍把戏的川南人。
“这几个家伙身手不错,不像是一般跑江湖卖打药的。”杨猫胡子很年轻,但已经混成了花桥十三公口的管事五爷。他武艺高强,在茶社里面与四面八方的人都有交际,加上又是正宗的杨氏血统,就在当地的哥弟中很有号召力了。
“来我们这里混饭吃,不先来拜码头,小心老子给你一点颜色看看。”
杨猫胡子理了理他的猫胡子,心里面窝了一些气。
快散场了,人越来越少,四个卖艺人也开始收拾家伙,看样子准备离开了。
远远地,三辆鸡公车吱吱嘎嘎沿着官道推过来,每辆鸡公车上捆扎两个大木箱,由赤膊的汉子推着走。四位镖师前后压阵,还有几个成都府的巡防军,挎着腰刀,不紧不慢地跟着鸡公车。一行人走到花桥场,准备在这里打个尖。
当鸡公车推到场镇中心,与韩二哥一行擦肩而过。杨猫胡子突然眼前一花,看见的一幕让这个久闯江湖的后生当时都傻眼了:只见韩二哥一个箭步从侧面扑了过去,虎吼一声,一掌将鸡公车上的木箱劈碎。韩二哥的铁砂掌已经浸润多年功力,足可开碑裂石。木箱里面是白花花的马蹄银,用布包成了许多个小包。
官府的人一时没有回过神来,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在这个繁华的集市当中,有人胆敢明火执仗。在花桥赶场的人也全傻了,等他们回过神来的时候,韩二哥抓起两个大布包,足足有三百两重,回手扔给了身后的张跃然,张跃然轻功不错,“嗖”的一声往房上蹿,吸引了几个镖师向他追。
在房顶上,张跃然将其中一个布包又扔给了同胞兄弟张跃廷,张跃廷拔腿就向后跑,霍笨作他的掩护,拿出卖艺用的棍棍棒棒,边打边跑。
几个巡防兵迅速拔出腰刀,围成一圈,把三辆鸡公车紧紧护住。这时候,韩二哥的铁砂掌大显神威,几个镖师捕快的腰刀劈来,韩二哥直接用手掌迎,手上的老茧就像是蒙上的一层铁皮,将腰刀震得东倒西歪。推鸡公车的那位哥子不知厉害,一棍打在韩二哥肩头上,木棍断成两截,韩二哥硬挺了下来,回手还了一掌,正中胸口,那人直飞出一丈多远,肋骨寸断,眼见不得活了。
韩二哥看到张跃然等几个人快要得手,又大吼一声,虚劈一掌,把几个捕快惊退几步,拔腿就向后跑。
“这几个人往金马河方向跑的,肯定有人在河边接应,叫码头上的兄弟们,带上家伙,我们去那里等他。”杨猫胡子冷冷地看着刚才的一切,对茶社里面的兄弟们说:“胆子不小呢,在老子的地盘上抢官银,见者有份!”
韩二哥一行人跑到金马河边,早有船等在那里了。
兄弟四个喜笑颜开,三百多两银子啊,足够让他们家乡的人渡过暂时的困难了。几个月来,川黔交界处大旱无雨,方圆数百里看不见一点绿色,田地开裂,庄稼如同枯草,一碰就成粉末了。
韩二哥等四人都是同乡,家乡的树皮树叶都被人吃光了,挖观音土的人,把山都快挖垮了。他们还亲眼看见乡亲们把几岁的儿子交换了吃,吃的狼吞虎咽,吃完了又吐,吐完了又哭。撞墙的、上吊的,什么样的死法都有。人死了,尸体又被人拿去吃、拿去卖了。每一天都听见家乡父老们在嚎哭:
“朝廷啊——青天大老爷啊——你他妈的睁开眼睛看看吧!”
韩二哥与几个兄弟在没有饿死之前,远远离开家乡,靠自己半卖艺半讨饭,在各州县流浪。这次一出手就弄到三百多两银子,是他们一生中见过的最大数额了。只要顺着金马河水道,不到一个时辰就进入岷江主流,再随便找个地方上旱路,一般来说,就可以摆脱官府的追捕了。
韩二哥看见几匹马如飞一般奔来,领头的大白马上坐着杨猫胡子。他面无表情,目露寒光,驶到韩二哥跟前,一提缰绳,大白马前蹄腾空,仰天长嘶一声。只见他抱拳说道:“花桥十三公口码头,杨绍德拜会哥子。”
韩二哥也是袍界哥弟,还礼道:“兄弟远道而来,办点小事,一切不周到之处,还望海涵。”这几个月,韩二哥家乡的人活得比牲口都不如,码头上的繁文缛节就没有考虑那么多了。
“在我们码头上办事儿,不办交涉、不拿上咐,腔不开气不出就走,这算是哪门子规矩?”杨猫胡子问道。
“依哥子的意思,又当如何?”韩二哥也有气了。
“见一面分一半,兄弟给你开道。”杨猫胡子高坐在马上,趾高气扬,说得轻描淡写。
韩二哥没有把这个年轻的毛头小子放在眼里,他气往上冲,指着杨猫胡子一行六人说:“哥子几个一起来比划比划,只要胜得了在下的一双肉掌,三百两白银全部拿去。”
“二哥,夜长梦多啊,这里是他们的地盘,给点钱算了。”张跃廷尽管年纪最小,但考虑事情比较周详,悄声劝韩二哥说道。
杨猫胡子几时受过这等轻侮,立即跳下马来,大声叫道:“老子和你单打独斗。”
一时间,金马河畔的草坪成为了比武场,两方的人分别站开,韩二哥和杨猫胡子居中。杨猫胡子的大力鹰爪功经过名师指点,自己也下过多年苦功,在本县从来没有遇到过对手,加上他们占尽天时地利,所以有恃无恐。只见他大吼一声,凭空跃起一丈多高,瘦长的身躯凌空扑来,如同大雕展翅,两只手形如鹰爪,气势夺人,直击韩二哥咽喉。
韩二哥气运丹田,扎稳马步,可见下盘功夫极好。他趁杨猫胡子将要落地时,左拳上勾,虚击对方下颌,右掌如同霹雳闪电,挟带了一股劲风,直击对方前胸,随即左拳也变作了掌,一掌紧似一掌,不断向杨猫胡子的要害部位招呼过去。
“好厉害!”杨猫胡子大叫一声,方才盛气凌人的样子全没有了,他连换了几个身法,才把韩二哥的连环铁掌化解开去。韩二哥是木匠出身,还在牙牙学语时,就抱着锯子、斧头玩。少年时代,宽大的手掌上就结了一层厚厚的茧疤,后来深山拜师,学到一身横练功夫,特别是一双铁掌,在川南一带也打出了不小的名气。由于他生性忠厚、木讷,入哥老会之后也主要干自己的木匠活,并没有真正在外面跑滩、闯江湖。这次适逢大旱,田地颗粒无收,他才外出逃荒。利用一身的功夫沿街卖艺,张跃廷和张跃然是同胞兄弟,能说会道,哥哥张跃然有一点功夫,就帮忙跑跑场子,另外一个霍笨,就打打杂,混口饭吃。
他们在成都府打探到,有一批官银将运往雅安,作为当地军队的经费。
他们恨官府,连父老乡亲们的死活都不管,打起仗来却毫不含糊,白花花的银子运了一车又一车。韩二哥面对官家的银子,一股热血涌上了心头,四兄弟萌生了抢夺官银的念头。
花桥场是成都到新津的必经之路,韩二哥等人提前一天在这里等候着。
当押送官银的镖师路过,他们一击得手。同时考虑到自己这边只有四个人,追兵即刻就到,就不敢把银子抱得太多。就算把这次抢夺的三百两银子带回家乡去,可以救得多少人的性命啊!
韩二哥与杨猫胡子拳来脚往,转眼斗了二十多个回合。论武艺,韩二哥要技高一筹,但他也不敢尽全力伤了对方,眼见花桥十三公口的哥弟又来了好几个,对自己这方的人形成合围之势。况且,这是在别人的地盘上,他只想走人,不愿结下更多的梁子;再说又是在别人的码头上作案,人家要你“拿话来说”也是正常的事。
对打中,杨猫胡子屡遇险招,但没有认输的意思,反而把拳脚使得虎虎生风。明眼人都看得出来,韩二哥占了上风,随时可以叫杨猫胡子倒在地上。只见韩二哥掌劈腿踢,连续攻了几记猛招,把杨猫胡子逼得后退了几步。然后他跳出圈子,抱拳说道:“兄弟好身手,我们打了个平手,银子,就拿来大家分了吧。”
杨猫胡子大喜,巴不得找一个台阶下,他非常感激韩二哥给他这个面子,如果真正当着众兄弟的面,把他打倒在地了,以后在码头上还怎么混啊。
“好,哥子说了算。”杨猫胡子跳出圈外,抱拳拱手,就打算叫兄弟们上前分银子。这一架打下来,他是真的服气了。
忽然之间,河滩上几匹马旋风般追来,马上骑手一路高叫:“不要放走了贼人。”
杨猫胡子远远地看见,认得是衙门里面的许伟仁、覃吉之等捕快。县衙的人他认识不少,平日里多少有一些交道。杨猫胡子的眼睛一转,立即翻脸,他把手一挥,命令兄弟们:“把这几个人围起来。”
话音未落,杨猫胡子一腿向韩二哥当心窝踹去。事变仓促,忠厚的韩二哥哪里有杨猫胡子的花花肠子多,根本就没有想得到这一节,被杨猫胡子一脚踢翻了。
“你这个不讲信义的杂种!”韩二哥身后的张跃然拔刀在手,挡在了杨猫胡子面前。张跃然的功夫就差多了,加上杨猫胡子身后的十多个弟兄全部亮出了家伙,张跃然完全没有招架之功。杨猫胡子手指似铁,左手捏住张跃然砍来的钢刀,右手闪电一般掐向对方的咽喉,用力深抓,张跃然喉间顿时出现三个深深的血窟窿,血如泉涌,双目暴凸,栽倒在了地上,眼见不得活了。
张跃廷见哥哥被杀,不顾一切扑将过去,立刻被花桥十三公口的一群人围住,拳打脚踢,毫无还手之力。
衙门里的捕快也赶到了,随后是几个护送镖银的镖师。双方的格斗形势瞬间发生了逆转,所有的人都亮出了家伙,短刀、铁尺不住向韩二哥一行招呼。张跃然倒地气绝,剩下的三个人怎么是大队人马的对手,韩二哥再神勇,也挡不住杨猫胡子、许伟仁、覃吉之以及几个镖师的合攻,十多个回合之后被擒了。
张跃廷与霍笨被打得遍体鳞伤,几乎就没有还过手。
阴暗的大牢里面,散发出一阵阵腐臭。牢里的重刑犯单独关押,用粗大的木栏隔成一个个小单间。侯宝斋与韩二哥面对面的时候,他一眼就看出这个粗壮的汉子不是坏人。
“官爷,要杀要剐,请便吧。”韩二哥知道闯下大祸了,这条命多半是保不住的。他看出侯宝斋是个头,就干脆把话明说了:“货是我一个人劫的,与两个小兄弟无关,官爷,我宁肯立刻就死,把他们两个放了。”
“你不要叫我什么官爷,我是新津三渡水码头的侯宝斋。”
韩二哥的一条腿被打折了,双手戴着枷锁,背靠砖墙坐在地上。身上的粗布衣服已经扯得稀烂,泥水和血水混在了一起,结成的疤痕变成了黑色,东一块西一块粘在衣服上,五官红肿开裂,完全变了形,整个模样非常狰狞。他听见“侯宝斋”三个字,血糊糊的双眼放出了光,但是随即又黯淡下来。
“呸!”韩二哥吐了一口血痰,“你怎么会是侯宝斋,我听说新津的侯大爷为人仗义,在四州八县素有‘小宋江’之称,怎么会在衙门里面当一条狗。”
哈哈哈……韩二哥放声长笑。
覃吉之飞起一脚,踢在韩二哥腰上,大叫道:“这就是我们‘新西公’
舵把子大爷侯宝斋,你他妈的嘴巴放干净点。”
韩二哥挣扎着站了起来,腰板依然挺得笔直,伤痕累累的身体也掩饰不了那股豪迈的雄风。他抱拳道:“四川码头上的人都听说过侯大爷的名号,今日幸会了。”
“只是这大牢之中,委屈几位兄弟了。”侯大爷还礼,完全没有把他们几位当作囚犯。
“我姓韩的知道在劫难逃,一人做事一人当,袍哥做得受的,一条贱命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只是这两个小兄弟才十几岁,抢劫官银的案子跟他们没有关系,从头到尾都是我一个人干的。”韩二哥从走进牢房的那一刻起,就不断为张跃廷、霍笨两人开脱,想尽办法把劫案的责任全部揽在自己身上。
“侯某人敬你是一条汉子,但是这次人赃俱获,我又怎么能够相信你的话。”侯宝斋有心为他们开脱,看起来很不容易。
“银子你们也追回来了,如果我死了,我兄弟的性命是不是就保得住了?”韩二哥看着侯宝斋的眼睛说,“况且我的兄弟已经被你们打死一个,就算是欠下了命债,我们也还了。”他想起血肉模糊的张跃然,一阵阵揪心的痛。
侯宝斋还在思考,他在想一个万全的法子。突然他听见“咚”的一声巨响,“不好!”侯宝斋暗叫一声。韩二哥运起最后一股力气,狠狠地把脑袋向红砂石砌成的石墙上撞去。在场的人顿时嗅到一股刺鼻的血腥气,他的脑袋撞得稀烂,连眼睛鼻子都分不清了,红的白的,黏黏稠稠流了一地。
“韩二哥啊——”隔壁牢房的张跃廷与霍笨大哭大叫。
经过侯宝斋的多方斡旋,张跃廷与霍笨最终与此案无关。侯宝斋敬韩二哥是一位义士,就将两人收留下来,让他们在三渡水码头上找碗饭吃。
几天后,县太爷的告示出来了:……被劫匪掠走之官银三百两已悉数追回,首犯古蔺人韩武狱中自尽,从犯张跃然在格斗中丧生,此役花桥人杨绍德协助官兵,并手刃从犯,功绩卓着。……
五
清晨,有霜。
县城刚刚从一片静谧中苏醒过来,东西正街开始有了小伙计开铺板门的声音,饮食店里隔夜的火炉还剩下一点余热。几个过路的叫花子蜷缩在火炉旁,斜闭着眼打呼噜,样子比掌柜的还要享受。
晨风吹开侯家大院的房门,人们陆续起床、洗漱,新的一天开始了。
侯宝斋的宅院在城西,是一处不大不小的四合院。大院坐北朝南,有两进院落,虽然不像大户人家的宅子雕梁画栋,但是开间敞大、建筑结构整齐。走进大门先看见一个地坝,可摆上十来桌酒席,地坝中间种一棵大槐树,枝繁叶茂。正面是堂屋,供关二爷的大幅神像,堂屋左右是八间厢房,东北角为厨房。侯宝斋与黄老五、何耀先等老兄弟住在二进院落内,这里面要小得多,也安静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