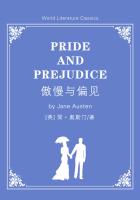古应春说:“素贵兄只这一个点子,就让汇丰赚得盆满钵满。现在整个上海的钱庄,恐怕没有几个不用这个法子做生意。”
胡光墉坐直了身体,饶有兴致地催促道:“你快说说,让我也长长见识。”
古应春喝了一口茶,不紧不慢地说:“钱庄不需实物做抵押,只需以自身开具的远期汇票,在五至二十天内,便可向汇丰银行借款。譬如,钱庄借用汇丰的利息是7厘,而以1分的利息转贷于商号,这其中便有了自己的利润。在这期间,钱庄和银行之间往来银钱周转的次数越多,利润就越丰厚。”
胡光墉点点头说:“汇丰本身存款的数额巨大,付给储户的利息应该很低,但借给钱庄的钱却可获得高额利息。借款时间短,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小风险。这一进一出之间,钱就生出钱来了。其中钱庄的信用是最为关键之处。常言说,好借好还,再借不难。”
席正甫说:“雪公是银钱业前辈,正甫的这点小伎俩,入不得您的法眼。”
胡光墉夸奖道:“‘满招损,谦受益’。我看,素贵今后的前途不可限量啊。”
“雪公过奖了。”席正甫停顿了一下,将话锋一转,见缝插针地说,“您刚才既提到信用,晚辈觉得阜康银号遍布大江南北,也是汇丰挑着灯笼都找不着的生意主顾。”
胡光墉双眉一挑:“阜康的事,你和应春便可商定。”
古应春也赞成同汇丰合作,但他没有直说,而是拐了一个弯:“现在上海的市面上,至少有近七成的钱庄在用这样的法子跟汇丰合作。说句实在话,他们都是在用汇丰的钱做生意。”
胡光墉点了点头,表示知道了,略作思忖之后,便言归正传:“素贵,今天请你来,咱不兜弯子,应春应该已经跟你说了。左大帅西征筹款的事已委托于我,本来同怡和洋行、丽如银行谈得已经差不多了,可谁曾想到,就在这节骨眼上,英国参赞马嘉理却在云南被杀了。朝廷和英国人在谈判,英国公使威妥玛告诉怡和、丽如不让他们借钱给我。这两家虽说有些背景,但不得不给威妥玛一个面子,这才劝我等一等。我倒是能等,可左大帅等不了啊!没有饷钱,士卒一步都动弹不了,仗就更没法打了。你说素贵,这让我怎么办?”
席正甫说:“我听古兄说,您正在跟德、法、俄等国的银行在商议这件事?”
“这也是没办法。”胡光墉苦笑着说,“我总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吧?”
“您既然能找到正甫,就是信得过晚辈。”席正甫略作沉吟说,“只是不知雪公这次需要用银多少?”
胡光墉目不转睛地望着席正甫,一字一顿地说:“500万。”
席正甫的心里一震:“不瞒您说,这个数远远超出了我的预想,更不是我能做得了主的。”
胡光墉笑笑说:“我知道汇丰的规矩,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放款权限。100万两以内,你一人便可做主。超过这个权限,便要再向上面请示。”
“您既知道汇丰的规矩,这最好不过。”席正甫低头盘算了一下,“晚辈现在只能说,三日之内,无论这事成与不成,都会给您个答复。”
“痛快!素贵快人快语甚合我心意。”胡光墉哈哈一笑,“既是这样,其他的银行我就先不跟他们谈了,我专等素贵三天。”
“这不妥吧。”席正甫劝道,“您跟别家该怎么谈还怎么谈,这样也好有个比对。”
胡光墉说:“事就是再急也不差这三天。再说了,也没啥好比对的。各家银行的利息都在我心里,谁高谁低我清楚得很。”
“那晚辈心里就有数了。”席正甫站起身,恭敬地说,“您先歇着吧,晚辈告辞了。”
胡光墉要亲自送席正甫出门,可席正甫坚辞不受。没有办法,他只好让古应春代自己送客。望着席正甫的背影,胡光墉不禁暗叹了一声:“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胜旧人……”
仁济医院是上海最早的西医医院。它的创办宗旨是:以西医术为华人免费诊治疾病。1873年,在上海各界人士的捐助下,医院进一步扩大规模建成了近3000平方米的二层新楼房。不久之后,徐润也以夫人的名义,捐出巨资在隔壁设立了女子医院,专门免费为妇女诊治疾病并开展用新法接生婴儿。正因为如此,徐润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了该医院的董事之一。
今天是仁济女子医院开业一周年,徐润在院长詹姆斯的邀请下来到医院参观。
“时间过得真快。如果没有一年前您和夫人的慷慨解囊,这里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詹姆斯院长驻足在大门口,指了指四周那如同花园一样的环境。
“您太客气了。”徐润谦逊地说,“在下一介商贾而已,除了能资助院长先生一些财米之外,其他的也无能为力。”
“是徐先生太客气了。”詹姆斯做了一个“请”的手势,一行人走入医院的大门。
一楼的一间诊室之中,华人医师黄春甫正在为新生婴儿接种牛痘疫苗。他动作娴熟地用锋利的手术刀片,在婴儿的手臂上轻轻划了一道血痕,然后取出一种类似药粉的东西敷在划破的地方。
那个小婴儿几乎完全没有感觉到疼痛,始终一副不以为然的样子,瞪着大眼睛望着驻足在门外的徐润一行,而婴儿母亲的眼中却露出担心的目光。
“真是乖孩子。”接种完毕,黄春甫轻轻拍了拍婴儿,并安慰他的母亲说,“您不必担心。这道小口很快就会结痂,两三日后即可出痘一二颗。自此之后,这孩子终身便可不患天花。”
“谢谢先生,谢谢先生!”孩子的父亲在一旁忙不迭地道谢。
“不必客气。”黄春甫站起身把夫妻二人送出诊室。
当他看到詹姆斯、徐润等人静候在门外的时候,便摘下口罩,用流利的英语微笑着同众人打招呼:“您好,院长先生,诸位先生们好。”
“请允许我做一下介绍……”詹姆斯非常礼貌地给徐润和黄春甫互做介绍,“这位是黄春甫医生:雒魏林医师最优秀的中国学生……黄医生,这位是徐雨之先生,咱们医院的董事。”
黄春甫摘下手套,拱手道:“徐先生,久仰大名!”
“黄医生辛苦了。”徐润也拱了拱手,颇有兴趣地问道,“您刚才是在……”
黄春甫说:“接种牛痘。这是预防和攻克天花最有效的办法。”
徐润点点头:“接种的人多不多?”
“很多人都不相信它的效果。”黄春甫苦笑着摇了摇头,“甚至还有人认为,种了牛痘以后,头上会长出牛角,甚至发出牛叫的声音。”
众人也纷纷笑了起来,徐润又问:“此西法与我国人痘接种相比,哪种更好?”
黄春甫略作思忖,断然道:“还是西法为佳。人痘接种者,还会再患天花,而用西法者,则无此疾患。”
詹姆斯在一旁说:“为了推广牛痘接种术,黄医生免费培养了大批的年轻助手,到周边的县城去为住在乡村的儿童免费提供服务。”
徐润由衷地再次向黄春甫施了一礼:“为使我国人身受其益,您能不顾个人得失,请受徐润一礼。”
黄春甫连忙还礼:“国人民智尚未开启,还需徐先生这样的商界领袖,身先士卒,广为鼓噪,此善法方能有大行其道的一天。”
徐润用力点点头:“您放心吧,一定会有那么一天的。”
约翰逊的办公室里似乎笼罩着一股诡异的氛围。
这种不同寻常的状态,让“澳顺号”的船长布朗好像有所觉察。多年来的航海经验,早已把他锻炼出一种如同野兽一样敏锐的感知力。这种能力不知让他多少次避开航行中的灾祸,得以完好如初地活到现在。
布朗一走进房间,便隐约感到一种无形的危机向自己袭来。但约翰逊仍跟往常一样,极尽友好地拿出自己收藏的古巴雪茄请他品尝。布朗吸了一口,对烟的口感颇为满意。
约翰逊说:“我刚刚看了一下这个月的财务报表,‘澳顺号’的营业收入比三个月前减少了50%,这是怎么回事?”
“您真的不知道吗?”布朗疑惑地看着约翰逊,“我想不仅只是‘澳顺’的收入在下降吧?‘久绥’、‘天龙’、‘亚平’……所有船只的收入应该都在减少才对。”
“您能告诉我这是为什么吗?布朗先生。”
布朗无奈地耸了耸肩:“您应该比我更清楚。我们所有的船都在面临着来自招商局的竞争。”
约翰逊面无表情地说:“可从报表上看,只有你的船收益最差。”
“这怎么可能?”
约翰逊没有直接回答,而是缓缓靠在椅背上,双手抱着前胸说:“布朗先生,你应该清楚,我们的业绩是不允许被任何人拖后腿的。我更不希望,上海分行因为这样糟糕的业绩而遭到克锡先生的批评。”
布朗熄了手里的烟,略带些窘迫地看着约翰逊。
“当然了,有一种情况除外。”约翰逊坐直了身体说,“就是你不希望再背靠怡和这棵大树来乘凉了。”
“噢,不,约翰逊先生,我们一直都合作得很好,不是吗?”布朗露出一副无辜的表情,摊了一下双手说,“怡和是一块金字招牌。如果‘澳顺’不是依附在它的名义下经营,我是不会这么轻松就赚到钱的。”
约翰逊叹了一口气:“你应该清楚,我之所以允许你的船以怡和洋行的名义经营,是出于两个原因:第一,‘澳顺’是一艘好船。无论航速,还是船体的材质,都堪称百里挑一。二是因为你——布朗先生。你是一位一流的船长,你所负责的船从来没发生过任何意外。可我真的想不明白,为什么一流的船长与一流的轮船结合起来的结果居然是营业额的每况愈下。”
布朗想了想说:“这个问题或许是您应该想办法解决的。您负责制定运费,我们只是按规定执行。既然我们现在的运费比三个月前降低了一半,那么来自每艘船的收入自然也就相应地减少了。”
“你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吗?”
布朗想了想说:“我建议您可以跟招商局谈谈,最好能一起把价格恢复到原来的标准。您和唐景星是老朋友。我相信,只要您愿意,这应该不难。”
约翰逊不屑地轻笑了一声:“我从来没把中国人当成朋友。”
布朗见约翰逊沉着脸没吭声,便挠挠头,自我解嘲地说:“除此之外,我真的想不出别的办法了。”
“你的‘澳顺号’保险了吗?”约翰逊莫名其妙地问了一句。
布朗的直觉再次告诉他,危机比刚才更近了。在布朗的印象中,约翰逊的记忆力超强。他明明记得,就是在这间办公室,约翰逊同自己亲手签订了“澳顺号”的保险合同。
布朗点点头,略带一丝紧张地看着约翰逊。
约翰逊说:“包括我们在内的多家洋行,都不给招商局的船只保险。他们的船一直都在毫无保障地航行。我还听说,他们被逼得走投无路,正在招集股份,准备成立保险公司来给自己的船保险。”
布朗一直目不转睛地望着约翰逊,心里不停地揣摩着对方话里的含义。
“如果这个时候,他们的船突然发生意外的话……”约翰逊停顿了一下,把目光直射向布朗,“假如招商局的某一艘船,突然在航行中遭遇意外,沉没了,而他们的船又没有保险,请问,这个损失将会有多大?”
布朗觉得约翰逊这个问题简直太幼稚了,一艘没有保险的轮船一旦遇险的话,会遭受多大的损失是显而易见的。虽然如此,他还是严肃地回答:“损失的不仅是船只本身,还要外加船上装载的货物。船上的工作人员、乘客,如果因为意外而死亡或受伤的话,他们还要承担相关的赔偿。如果把这些加在一起的话,天呐!我真的很难估计出实际的价值。”
“说得太好了,布朗先生。”约翰逊的嘴角露出了一丝冷酷的笑容,“如果你不反对的话,我们可以精心设计一场意外,让它从外表看起来简直就是一场完美无缺的意外。”
布朗顿时明白了对方的意思,他难以置信地说:“你疯了吗?这是谋杀!”
约翰逊一反常态地拍着桌子吼道:“你难道非要逼我去和中国人妥协?你别忘了,是他们先闯进了我们的地盘,是他们先破坏了游戏规则!”
“和中国人妥协怎么了?”布朗站起身,毫不示弱地说,“我提醒你,我们是在中国,是我们闯进了中国人的地盘?只要不影响我们的利益,妥协又有什么不好?”
“我不想再和你争论这个毫无意义的问题。”约翰逊一把揪住布朗胸前的衣襟,大声吼道。
布朗大声说:“我是船长,不是杀人凶手。”
“你以为我是为了自己才想这样做吗?”约翰逊松开布朗的衣襟,露出一副无辜的表情,“为了英国商人在中国的利益,我还会有其他选择吗?招商局如果一直这样纠缠下去,我只能选择解除我们之间的合约。”
布朗沉默不语。
“我一向崇尚和平,这一切都是他们逼的。”约翰逊深吸了一口气,“你放心,我全都替你安排好了,你不要有任何顾虑。你的安全会万无一失。我已经调查过了,‘澳顺号’船头的钢板是专为制造铁甲船使用的高强度材料,比普通轮船更加坚硬,如果木质轮船撞上它……”
约翰逊一边说,一边习惯性地拿起放在他办公桌那艘轮船模型上的生鸡蛋,然后取过一只玻璃杯,把鸡蛋在杯子的边缘上一磕,随着一声轻微的响声,蛋壳立刻破裂:“……就会像这个鸡蛋一样。而且,你的船已经买了保险,如果有损坏的话,我们会对它进行全部赔付。”
他把磕破的鸡蛋倒进玻璃杯,继续说:“你也无须对结果承担任何责任。我会把事后所有的问题都处理妥当,你的‘澳顺号’可以继续在怡和名下经营,我还会在现有管理费用的基础上,再给你打个九折。”
布朗依旧紧锁着双眉,一言不发地站在那。
约翰逊看了他一眼,忽然问道:“你和家人是不是很久都没有相聚了?”
布朗还是没有吭声。
约翰逊一仰头,把那杯蛋黄和蛋清混在一起的液体一口喝了下去。然后,他掏出手帕极尽绅士风度地擦了擦嘴角说:“你应该回去看看她们了。不然你那漂亮的妻子还有可爱的女儿,都会生你的气。”
约翰逊拉开抽屉,从里面掏出一本支票,拿起笔在上面飞快地写了起来。写完之后,递给布朗说:“这是1000英镑。事情完成之后,我会安排你回国跟家人团聚。你可以带上她们离开家乡的农庄,去美丽的伦敦看一看。听一场歌剧,或者只要你愿意,随便是什么……”
布朗迟疑着,没有伸手去接。
约翰逊把支票放在桌上,冷冷地说:“当然,你也可以选择‘不’。如果那样的话,就请你带着你的船,马上滚出去。”
布朗的脸上阴晴不定地变幻着,他的内心也在不停地挣扎着。约翰逊看了他一眼,起身走了几步,一把拉开房门——看来他已经准备结束这次谈话了。
“我忘了提醒你,布朗先生:即使你不做,也会有别人愿意做的。如果你和你的船离开怡和的话,每年1万英镑的收入就会烟消云散。”约翰逊似乎一瞬间又恢复了平日里的那种绅士风度,回过头温和地看着局促不安的布朗。
布朗的心又是一动,约翰逊继续说:“就算你找到了新雇主,我也会写信给他们,劝他们不要雇用你。我想,无论在这里还是英国,怡和都有能力办到。”
陡然间,布朗的脸顿时变得毫无血色,而约翰逊则头也不回地走了出去。
养心殿,东暖阁。
慈禧、慈安两位皇太后并列端坐在一把铺有明黄软缎坐垫的锦椅上,前面是同治皇帝的龙椅,椅子上空无一人。
下面侍立着恭亲王奕、兵部尚书沈桂芬、户部尚书罗淳衍,还有李鸿章、翁同龢几位王公重臣。
慈禧的目光在几人的脸上依次掠过,用一口地道的京片子,软软地说:“本来我和姐姐今天是不该在这儿的。可是皇帝的身子骨向来孱弱,现在又染上了恶疾,不能躬亲裁决奏折。就只能再由我们姐俩勉为其难,权为披阅办理。”
几个人异口同声地说:“太后圣明。”
慈安朝众人微微点了点头,语气和缓地说:“左宗棠和李鸿章上的折子,诸位都看了吧?”
众人齐声说:“禀太后,臣看过了。”
慈禧依旧不紧不慢地说:“既然都看了,那就说说吧,你们对这事儿是怎么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