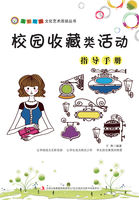我不准备举更多的例子来说明这一问题,我将对我医务实践中所经历的一个例子做详细的分析。一个已婚的年轻女士在一次车祸中摔断了小腿,这样她不得不卧床几星期。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她没有表现出痛苦,对这种不幸表现得异常的平静。这个事故导致了她的严重的心理疾病,这个疾病一直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不过最后还是通过精神分析的方式治好了。在对她进行治疗的时候,我了解了有关这次事故的背景材料以及前期事件。这个少妇在她的嫉妒心很强的丈夫的陪同下,到她已婚的妹妹的农庄小住,陪伴他们的还有她的很多兄弟姐妹以及他们的丈夫、妻子等。一天晚上,在这个亲密的圈子里,她显露了一下自己的才气,跳了一曲康康舞,亲戚们对她的这个精彩的表演拍手称赞,唯一不满意的是她的丈夫,他对她低声说道:“又在做婊子!”这句话伤透了她的心——我们不去考察这句话是否仅仅指她跳舞——她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第二天早上,她感觉自己应该驾车去放松一下,马是她自己选的,说这对马不行,特选了另一对马。她的妹妹让她的小孩和保姆一同前往,她表示强烈反对。坐在车上走的时候,她显得很不安,她叮嘱车夫小心惊了马。果然,一刻也没有停止的马真的出现了问题,她惊恐地从车上跳了下来,结果摔断了腿,而其他待在车里的人则安然无恙。我了解了这些细节后,不得不承认,这种意外是设计好的,我们也不得不佩服她的这种技能,即为自己的犯罪行为找到一个恰当的惩罚机会的技能,因为,她在以后很长时间无法再跳康康舞了。
至于我自己的自我伤害行为,所能报告的寥寥无几,但在一次很特别的情况下,我发现我也无法逃脱这种自我伤害。当我的家人抱怨说自己咬了舌头,或夹了手指此类的话,他通常无法得到他希望得到的同情;相反,人们会反问:“你怎么会这样的?”当一个年轻的患者在一次治疗过程中表现出要娶我的大女儿的愿望时(当然,并不是认真的),我夹了我的大拇指,当时感觉很疼痛。我知道,当时她由于重病而住在医院里。
我的一个儿子,脾气暴躁,生病的时候很难护理。一天,当告诉他今天上午要待在床上时,他很气愤,威胁说他要自杀——这种方式可能是他从报纸上了解到的。到了晚上,他让我看了他胸部一侧的一个肿块,这是他撞门柄时留下的。我感到很奇怪的是,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其用意何在,这个11岁的孩子的回答好像能够让我明白一些:“我早上说过我要自杀的。”这样看来,我的观点对解释我的这个孩子的情况似乎不太适用。
如果你相信有半存心的自我伤害行为存在的话,那么,你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除了有意识的、存心自杀外,还有半存心的自我毁灭(在潜意识动机支配下的自我毁灭),其表现是巧妙地利用一些对生命的伤害事件,或将它伪装成偶然的不幸的事件。这样的自我毁灭为数并不少,因为有自我毁灭倾向的人比已经做出这种行动的人要多得多,自我伤害实际上正是这种自我毁灭的动机和阻止它表现的力量之间的一种妥协,即使这种自杀已经成为事实,这种自杀的倾向实际上也以被压抑的方式在无意识中存在了很长时间。
即使是有意识地自杀的人也要选择自杀的时间、方式和机会,对于潜意识的自我毁灭而言,在完成这种活动时也要等待机会,一方面逃避监督,另一方面利用个体防卫的力量,将这种被压抑的动机力量释放出来。我的这个观点远非无稽之谈,我从很多这种偶然的不幸中了解到(从马背上摔下来,或从车上摔下来),自杀是由于潜意识的默许而表现出来的。例如,一个官员在和他的同事骑马比赛的时候从马上摔了下来,由于这次他的伤很重,几天后便死了。清醒的时候,他的行为在很多方面都是正常的,但他在事故发生前的行为则很不寻常。他很爱他的母亲,他的母亲死后,他变得一蹶不振,多次在谈到此事时,在同事或朋友的面前都泣不成声,在他的好朋友面前多次说他对生活已经厌倦了,并要辞职去非洲战场,而他以前对此则没有兴趣。以前,他是一个熟练的骑手,现在他则避免骑马,即使有此可能。最后,在赛前,他也并不退出,但表示出一种悲哀的预感,根据我们所阐述的观点,这个预感变为现实是不足为怪的。有人还这样告诉我,一个人在这样一种悲伤的状态下无法控制一匹正常的马也是很值得怀疑的。我很同意这种看法,但是由这种“神经(nerves)”状态所引发的运动机能的抑制也应该被看作一种自己所坚持的自我毁灭的动机。
布达佩斯的费伦茨为我提供了一个可以公布于众的观点,他分析了偶然的枪伤事件,他把此解释为一种潜意识的自杀的企图,我同意他对这个事件的看法:
“J.Ad,22岁,一个熟练木工,他于1908年1月18 日拜访了我,问我说,1907年3月20日,一粒子弹穿透了他左侧的太阳穴,这个子弹能否通过手术取出。除了偶然有一点轻微的头疼外,他感觉很好;而且客观的检查也表明,除了左侧有一个子弹疤痕外,并没有什么不正常的,因此,我建议不要动手术。当我了解到当时的情况时,他解释说,这是一个偶然的伤害事件,他正在玩弄他哥哥的左轮手枪,心想里面可能没有子弹,因此用左手对着自己的左侧太阳穴扣动扳机(他并非是左撇子),结果子弹射了出来。在这个能容纳6颗子弹的弹膛里竟然有3颗子弹。当我问他拿起这个手枪时是怎么想的时,他回答说,那时他正要进行服役体检。就在前一天晚上,他还拿着枪到了酒吧,因为他害怕打架。在体检的时候,由于他的血管肿大,他被认为是不合格的,他对此感到羞愧。回到家后,他便玩起了这个左轮手枪,但并没有伤害自己的意图,结果不幸却发生了。经过我的询问,我发现他对自己的生活不太满意,他爱上了一个女孩,这个女孩也很爱他,但她却离他而去。由于钱方面的原因,她移民到了美国,他要和她一起去,但是他的父母阻止了他。他的恋人是于1907年1月20日走的,两个月后就发生了这个不幸的事件。尽管有这么多可能的因素,但这个患者仍坚持枪伤自己是一个“意外”。不过我还是顽固地认为,他玩弄这个自己确信没有压子弹的左轮手枪,并伤到自己,是由内在的心理动力决定的,在这种失恋的悲伤情绪的打击下,他也在做出努力,也许自己可以在军队“将这一切忘掉”。但是,当自己的这个希望也破灭时,他去玩弄这个手枪——或者,出现了一种无意识的自杀动机。他用左手而非右手来拿这个左轮这一点明显揭示出,他仅仅是“玩”;或者,在他的意识中并没有自杀的愿望。
还有一个对这种明显的偶然性自我伤害分析的例子,对这个例子的考察,使我想起了一句格言:“自掘坟墓。”
“弗拉,中产阶级出身,已婚,有3个孩子。她患有神经过敏的疾病,但是,她并不需要什么治疗,因为她能够应付日常生活。一天,她将脸弄伤了,虽然是暂时的,但却使她很难堪。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她在一个正在整修的路上行走时,不小心踏在了一个石头上,结果脸摔到了一个房子的墙上,整个脸都搞伤了,眼也青了,她怕自己的眼会有什么问题,便去看医生。当她的情绪从这个情形中平定下来以后,我问她:‘你为什么会这样摔伤呢?她回答说,就在这之前,她曾警告过她的丈夫要小心一点,因为他关节炎已经几个月了,在街上走路的时候很困难,而且要十分谨慎。她的经验表明,当自己警告别人不要做什么的时候,这件事往往发生在自己的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