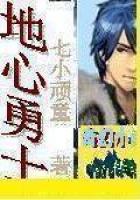沧州城,四面被高耸的城墙戍卫着。这座有着几千年历史的古城,在时光无情的倾轧下,千年前的繁华流传至今已是消磨殆尽。
或是战乱,或是天灾,林林总总的不幸在漫长的岁月里纷至沓来,一点点的消耗着这个城市的活力。到得如今,偌大的内城已经显露出荒凉之态了。
城门口,一名身着青袍男子正打算出城。还算英俊的脸上挂着的淡淡笑容,配上那身飘逸的士子长袍,散发出一股温文尔雅的气质。却因为他肩上扛着的那一垛冰糖葫芦而变得不伦不类。
这个一路上引得行人纷纷侧目的男子,正是已经来到沧州三天的吕洞宾。
此时的他正扛着一个草垛闲庭信步的向城外走去。他已经在沧州城转了三天,原本满满一草垛的冰糖葫芦,如今只剩下插得密密麻麻的竹签。
回头望了一眼沧州城,他把手里仅剩的半串冰糖葫芦一口咬光。一边毫无风度的大口咀嚼,一边含用糊不清的声音嘟囔“看来是在城外啊!”然后随手把手里的竹签插在肩上的草垛上,扛着草垛大步向城外走去。
沧州城外,一处离城有些远的地方。
一座小巧的茅草屋建在那里,屋子四周遍布野草野花,屋后还有一个小小的菜园。茅草屋右边紧挨着一个低矮的厨房,或许是不常用,烟囱雪白异常。茅草屋左边的空地上有一株碗口粗,正在落叶的山楂树。树下横着一座长方形石条,一个身着白色衣裙的女子正托着下巴坐在上面凝视远方。
这里离沧州城虽有一段距离,但毕竟靠近车道,平时仍是有不少赶路的行人经过。可从来没有一个人能发现这里的茅草屋。
因为有一层淡淡的结界薄雾般把这个小小的家园隐藏在了其中。
“应该是这里了。”吕洞宾在城外找了一段时间后,终于发现了这个与众不同的地方。这种隐匿的方法还是他和白牡丹一起研究出来的,他几乎可以肯定白牡丹就在里面。
扛着草垛,嘴里念了一段口诀,结界打开一个小口,吕洞宾跨了进去。
没走几步就看见了那座茅草屋和山楂树,以及坐在树下的白色背影。
他的脸上露出了一个与平常截然不同的笑容,不是习惯性的礼貌而是发自内心,温馨而亲切。
“牡丹。”他轻轻喊了一声,简单的两个字,不知道蕴含了多少情感在里面。
树下的白牡丹浑身一震,难以置信的转身站起来。
这是一个美丽端庄的女子,清秀的瓜子脸,一双眼睛温柔似水,给人一种淡淡的如水墨画的感觉。
回过头来看到确实是那个魂牵梦萦的人时,她的眼眶瞬间变得通红。张大了嘴,动了动嘴唇,想要说些什么,可是眼泪却不争气的在眼眶打转,最终什么声音也没有发出。只是红着眼睛一动不动的看着吕洞宾。
眼看她就要掉下泪来,吕洞宾急忙放下肩上的草垛,伸手在草垛顶上变戏法似地拔出两串冰糖葫芦,跑到女子面前,二话不说把一串塞进她张着的嘴里。
“唔……”女子猝不及防的咬了一口,感受着那熟悉的酸甜在舌间翻转,又看了看眼前正咬着一颗山楂一脸打趣的看着自己的吕洞宾。她努力的吸了吸气,那眼泪终于没有掉下来,终于一抹笑靥在脸上绽放开来。
然后两个人吃着冰糖葫芦,默契的并排向茅草屋走去。
“牡丹,你一直住在这里么?”
“嗯”
“牡丹,这些年我一直在找你。”
“我知道的。”
“牡丹,你……”
重逢的惊喜已经适应过来,自己还要面对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想着这些她回答起来也就心不在焉了。“吃饭吧,我做几样你爱吃的菜,吃完饭我慢慢跟你说。”脑中一连串的画面闪过,终于,还是下定了决心。
她低着头不敢看吕洞宾,说出这句话仿佛是用尽了她全身的力气。如果是梦就好了!许多年后,她常常这样想。如果当初并没有做那件事,一切都不会发展成这个样子吧!
“好怀念你的厨艺啊,今天有口福了。”吕洞宾一边好奇地打量着四周,一边颇有些回味的说道。
随即,两个人进了屋子。屋子里的陈设极为简单,最里面放着一张挂着白色帐幔的木床;旁边有一个放东西的柜子;屋子中央摆着一张桌子,桌子上放着一个紫砂茶壶,茶壶旁边有两个倒扣的杯子。
吕洞宾把剑解下来挂在墙上,撸起衣袖自告奋勇地说道“牡丹,我看到后面有个的菜园,摘菜的重任就交给我了。”随即他迫不及待的冲进了菜园。
其实对于修道者,完全可以辟谷不食。但他们俩以前在一起的时候,却是很热衷于做菜吃饭,两个人都很享受同坐一桌的温馨感觉。
片刻后,吕洞宾就捧着一大堆蔬菜回来了。两个人钻进厨房,好一阵乒乒乓乓。等白牡丹切好了菜,吕洞宾就蹲在灶边点起火。
雪白的烟囱便开始往外冒出炊烟。袅袅的炊烟持续了一个时辰,随后,院子里开始飘散出诱人的菜香。
桌子上摆满了菜,两个人面对面坐着。吕洞宾那边是大快朵颐,一大盘菜顷刻就都进了他的肚子。
白牡丹一脸满足的看着吕洞宾狼吞虎咽,自己却一筷子未动。我们有多久没有这样在一起吃饭了。白牡丹心中这样想到。
她抬起头看了一眼窗外,太阳已经西斜。就让这一幕永远留在记忆里吧!她有些忧伤的坚定了心中那个想法。
吃完后,两个人一起收拾碗筷,期间吕洞宾还问她为什么不吃,被她以辟谷太久,吃不下为由推脱过去。
收拾好饭桌,他们两个人一起走出门外,紧挨着坐在树下的石条上吹风。这是他们共同的一个习惯。用吕洞宾的话说,傍晚的风是最温柔惬意的,人放下一天的奔波,吹着这样的风心中轻松自在。
???“真不知道这样的日子还能持续多久……”吕洞宾的头枕着白牡丹的双腿,也许是因为晚风过于清爽,勾起了他的睡意,他就这样低喃着沉沉睡去了。
“以后不会再有了。从我知道你就是纯阳帝君转世的那一刻起,就没有了。这是最后一次了……”白牡丹轻轻地抚摸着吕洞宾的脸,悠悠一叹。一柄闪烁着五彩辉光的匕首悄无声息的出现在她手中。
她低头看着熟睡如婴儿一般毫无防备的吕洞宾,颤抖的双手握住匕首,笨拙的把刃尖对准吕洞宾的心口。刀尖在心口停留了好久,她的脸上显出痛苦和挣扎,她还是下不了决心。直到那一幕幕血红凄厉的画面在她眼前划过,她才认命一般闭上了眼睛,把那尖端刺入这个她深爱的男人的心脏。
鲜血无声的流出,“对不起……我要报仇……对不起啊!”完全没有大仇得报的喜悦,反而心中似是空了一块。她哽咽着拔出匕首,用力向自己的胸口刺去。
“我知道……我知道的,杀父之仇不共戴天呀!不过……你不能死啊……”一双有力的大手突然攥住了住那沾血的利刃,不让它再靠近白牡丹一点儿,那尖刃硬生生停在白牡丹胸前再不能前进分毫。
原本应该在熟睡中慢慢死去的吕洞宾此刻却站在她面前阻挡了她的自决。他粗鲁的夺过白牡丹手里的匕首,用两只手把那匕首一遍又一遍的折揉,不顾双手伤痕累累,直到被扭成一团,他才放心把匕首扔了出去。做完这一切,他才无力的倒在石条上。
??杀父之仇。白牡丹如遭雷亟,呆呆地看着吕洞宾疯狂的举动。刚刚做了那样的背叛,她不敢上前。直到吕洞宾倒下,她才失魂落魄地冲过去把吕洞宾扶起来。
“原来你早就知道。”她带着哭腔,伸出一只手放在吕洞宾不断流血的心口,白色的妖力源源不断的输入。
绵长的妖力除了让吕洞宾的脸色微微好转之外,并没有起到其它什么作用。一团五色的光芒始终在伤口处不断侵蚀着。
“在来沧州的路上,我一直在做一个梦。梦里有一个叫纯阳的人……他真的很厉害。不过我一点也不喜欢他……那个家伙太臭屁了,说什么要诛尽天下妖邪,哈哈……”他的脸上露出自嘲的笑。
“沧州,那个染血的夜晚呐,一夜的屠杀,把方圆三百里的妖都杀尽了,真是个疯子。”吕洞宾的脸上露出痛苦的神色,缓缓闭上了眼睛。
这也是白牡丹心中永远的噩梦,她永远无法忘记那个夜晚。天地被鲜红的颜色充斥,无休无止的凄厉惨叫从四面八方传过来,至亲至爱在眼前被断绝生机,尸体鲜血混杂,惨烈如同阿鼻地狱。
一只血肉模糊,布满创伤的手慢慢抬起,把白牡丹正在输送妖力的手握住。“没用的,不要再浪费妖力了……你也明白的……仙灭……刺中的伤口是……不能被愈合的……”
过度的失血并不能要了修者的性命,真正致命的是那一团无法抑制的五彩光芒,它正不断地侵蚀着吕洞宾的经脉。挺了这么久,他也终于开始虚弱,声音也断断续续起来。
“你为什么还要回来啊……”白牡丹的脸上全是慌乱,这个平日端庄的美丽女子,此刻就像是一个犯了错的小女孩。面对着无法挽救的错误,她抱着吕洞宾声嘶力竭地哭了起来。
吕洞宾只是笑了笑,他轻轻地拨拭着白牡丹披散的秀发,眼中露出一丝憧憬“牡丹……看到你没事我真的……咳咳……很高兴……你不要怪他们六个……咳……李瘸子一定只是逼你离开我……呵……这下我又欠他一个大人情了……呵呵……回去之后就……咳咳咳……不跟他抢老大的位置了……”
断断续续把这些话说出来,他的声音越来越小,眼神开始溃散,脸上残留着笑意。心口已经不再有血液流出,那一团五彩的光也消失不见。
兵解的这一刻还是来到了,他的身体开始慢慢消散。白牡丹死死的抱着吕洞宾,试图阻止他的消散,想要把他留在怀里。
却终究徒劳,吕洞宾的身体消散成一个个金色的光点,飞离白牡丹的怀抱。
兵解,修道者身死之后,躯体湮灭重归天地。
大部分光点慢慢消散之后,却有一小部分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停在半空。这些残存的光点,渐渐汇集在一起,在半空中汇成一道淡淡的虚影。虚影正是吕洞宾的样子,只是与原先相比,眉宇间多了几分凌厉。
“小九。”虚影对着不远处唤了一声。
“铮~”茅草屋里的古剑带着破风声呼啸而至,停在虚影面前。此时的长剑已经不能称作“古”剑了。原本黯淡的剑身已经变得金光流转,一股杀伐之意也从剑上散发出来。
虚影轻轻地抚摸着长剑,脸上露出一个缅怀的表情,“走吧,我们回去。”说完,虚影消散成一道金光,附在了剑上。
长剑向着南方飞去,那是去往无尽海的方向。
夕阳下,那个悲伤的白色身影,被血红的余晖拉的很长……很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