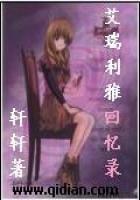?第4章
“姓名?”
长长的沉默之后换来了两个咬出来的字——“萧何。”
“年龄?”
“二十一。”这一次答得顺畅多了。
“干什么的?”
沉默,他没有再做答,坐在他对面的警察可不耐烦了,“问你什么就说什么,刚才打架的样子多英雄,怎么现在一问话全都狗熊了?”老警察又要感叹——现在的年轻人啊!
老警察有耐心,跟萧何一般大的年轻警察可就厉害多了。将厚重的案卷丢在桌上,震得萧何耳膜都在颤抖。
“你到底说是不说?有胆在酒店打架,没胆据实回答?我说你……”
他正发着威风,一个没带警帽的脑袋伸了进来,“是萧何吗?你可以走了。”
“他……”小警察的话还没说完,萧何已经站起身向外挪去。
这地方根本不是一个未来钢琴家该待的地方。不过即使知道结局如此,如果再重来一次,他还是会用拳头挥向郑全能那张可恶的狗脸。
该回去了,丢了酒店的工作,在找到新工作之前,他还是先去饭庄干一阵子吧!他需要钱,为了池砚和宝宝。
低头猫腰,他钻出警局,却躲不过头顶上雷电交加下的风雨。迎头便看到了熟悉的车牌,尾数“011”,那是父亲的车。难怪他闯了那么大的祸,竟可以轻松地走出这道门,原来有人在这里等着他。
不管怎么样,还是得上前打声招呼。他怀念坐在这车上的感觉,至少不用像个琴师那样接受客人的侮辱。
打开车门,萧严正四平八稳地坐在车里,那庄严的架势与萧何身后警察局的门脸不相上下。犹豫了片刻,他还是弯腰钻进了车里。
“爸!”
“开车。”萧严吩咐司机,把这种地方和他的儿子联系在一起,他是一刻也待不下去,“你什么也别说,咱们回家再谈。”
他竟然……他竟然在酒店里做琴师,给人演奏赚小费。这钱还赚到姓郑的儿子的头上,两个人公然在酒店里打成一团,要不是姓郑的打电话告诉他,他至今还蒙在鼓里。
这小子想干什么?上报纸头条吗?做钢琴家竟然做到了这份上,他不要脸,他的老脸还没处搁呢!
车行驶在风雨中,凉意透过车窗窜到萧何的周身,从上到下,无一丝暖意。
车开进自家的社区,远远地,就看见萧夫人撑着雨伞等在门廊处,“萧何,你回来了?你终于回来了!可把妈妈担心死了!”她摩挲着儿子的头,像在摸很小的孩子,“你怎么会跟郑全能打起来呢?他们家的孩子可是社会上的垃圾,你怎么能跟那种人搅和在一起?”
“进去再说。”萧严没给他说话的机会,只是上下打量着他,被岁月浸泡出的深邃的眼睛里放射出权威性的光芒,“你浑身都湿了,先上楼洗洗去。”
本以为会被骂得体无完肤,可回到家中,父亲不责备他,母亲不埋怨他,反倒让萧何有些无所适从,“爸,我……”
“什么也别说,洗完澡,你先给脸上的伤涂点儿药。其他的事,咱们一会儿再说。”萧严心意已决。
在外面奔波了那么久,好不容易回到了舒适的家里,萧何整个人从戒备的状态中放松了下来。他想也没想就顺从地上了楼,回到自己久别的房间里。
屋里的一切还是一如从前,妈妈从德国为他带回来的钢琴盘踞在房间的正中央,这架钢琴足可以买下十架酒店里那种破琴。他的手指划过光滑的钢琴表面,像抚摸着世间最美丽的女人的容颜。
坐在地板上,屋里进口的松木家具保有自然本色,让他彻彻底底地放松下来。即便屋外有再大的风雨,躺在这里,躺在这架黑色钢琴的下边,他就再也不用考虑什么。
没有责任,无须逃避;没有恐惧,无须勇气。他只要做回最本色的自己就好,他就是他——萧何,一个年轻的有些无助的男人。
灯光投射在黑色的三角钢琴上,它为他挡去光,将他团团包围在阴影里。太自在,太舒服了,模模糊糊中他竟然就这样睡了过去。
他睡着了,睡得忘了在风雨的另一边,有个女生正和宝宝一起等着他。他以为她会一直等下去的,却忘了,她也是人,也有失去信念的那一天。
他睡着了,睡得没听见卧房外他的父母正在堂而皇之地算计着他的未来——
“老萧,老萧,这样行吗?”
“怎么不行?我就不信,锁住了他整个人,他还能飞到那个坏女人的身边去?”
找不到萧何,竟然找不到他。
已经三天了,他没有回过寝室,也没有去上课,连最喜欢的琴房都没有去过。池砚想了所有能想的办法,动了所有能动的脑筋,她已经转遍了整个音乐学院,走遍了整个学校,可就是找不到他。
他去了哪里?是遇到了什么事被绊住了,还是……还是他刻意地躲着她?他不想要她了吗?
阴雨天还在继续,穿梭在冰冷的液体中,这一次池砚体会到了前所未有的恐惧。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也不知道将要面对的是什么,更不知道结局如何。
她的命运被寄托在一个男人身上,更可笑的是,她寄托的那个男人甚至把握不了自己命运的齿轮。
不知道找了多久,也不知道走了多久。直到她疲惫地面对一扇门,才知道自己又回到了和金山同住的寝室。这时候,除了这里,似乎她也无处可去了。
“金山,我……”
“你可回来了!”金山一把将她拉到房里,关上门,她确定隔墙无耳,这才带着满脸惊恐的表情追问起来,“你知不知道事情不好了?”
是萧何吗?难道他发生了什么不幸的事?“轰”的一声,她的眼前漆黑一片,“是萧何?”
“是你!”她哪里还有心思担心别人,管好自己就不错了,“你知不知道外面现在都怎么议论你?”
“议论……我?我?”池砚猜不出发生了什么事,“我有什么好让人议论的……”她的手按在了小腹上,难道是……“不知道谁将你怀孕的事传了出去,现在整个学校都在疯传你的事。他们说你做了人家的**,还说你……还说你给人……”难听的话金山说不下去,她知道池砚不愿意听,也接受不了。可事情就这样发生了。
是走了太多的路吗?她好累,她真的好累,累得再也站不起来。池砚的身体不自觉地向下瘫去,直挺挺地坐在地上,她的背脊无法放松,“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金山,你告诉我,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
金山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她,她甚至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只是眼睁睁地看着池砚从幸福的山顶滑到了痛苦的谷底,“池砚,你要加油,不要被那帮恶意中伤你的人打垮。他们就是要看你的笑话,越是这样,越不能让他们得逞,你要坚强哦!”
坚强?坚强?连萧何都离她而去了,她一个人怎么坚强?
“金山,让我一个人好好想想,我想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我想知道下面的路我还要不要……”要不要走下去?
没道理的,没道理全校的人都知道她怀孕了。她相信金山不会出卖她,剩下来惟一知道这件事的人就只有萧何了,他又一直失踪,难道是……他?
池砚颤抖的手捏成一团,她的手中捏出的不是滚烫的汗水,竟是冰冷的雨水。冷冷的,让她心痛。
萧何,你在哪里?
你知不知道我被逼到了绝境?你知不知道我好害怕?你知不知道我需要你?
在她最需要他的时刻,他不在她的身边,他像一只折了翅膀的鸟,被关在了笼子里。
“放我出去!快点儿放我出去!”
萧何快要发疯了,他的手满是青紫的痕迹,肿得像颗馒头,可他却丝毫不觉得痛。心里想的只是父母的卑劣,还有不知道急成了什么样的池砚。她一定在等他,说不定已经急疯了。
“爸!妈!放我出去,我必须回校!我必须回寝室!我必须回去!”
“别再挣扎了!”萧夫人即使有再多的心疼,为了儿子的未来也只能狠心这一次,“说什么我也不会放你出去,你就乖乖地在房间里待着吧!等过段时间,所有的一切都过去了,你也冷静了下来,那时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妈妈绝不会再关着你。”
等到那时候就来不及了,萧何继续捶着门,恨不得让这可恶的门与他的拳头一起粉碎,“妈,你放我出去,池砚在等着我,如果我再不回去,她会担心的。”他更怕她误会,他的失踪会让她误以为自己被抛弃吗?他估算不出,相处时间的短暂决定了他们对彼此间的了解不够深,连信任也变得浅薄。
他不提池砚还好,这一提萧夫人原本有些动摇的心情一下变得更加坚决,“不准去!就是不想让你见那个坏女人,所以我和你爸才狠心将你关起来。我们这么做都是为你好,你现在或许会怪我,但等你成熟以后,等你也做了爸爸,你就会理解我们今天的做法。你再挣扎也只会伤害你自己,有那点儿时间还是练练琴吧!”
母亲的脚步声越走越远,在萧何空荡荡的心中留下回音。门外寂静一片,他是彻底地没了指望。顺着门,他滑倒在墙边。无力的双手垂在冰冷的地上,却激不起他半点儿反应。
在一起的时候不觉得,两个人分开了,他才发现自己想她想得发狂。原来,平日里最简单的相处,最沉重的背负竟然可以让两个人慢慢地依赖对方,直至相爱、相守。这一刻,他只想对她说——
“我,萧何……没你不行。”
每天默默相对,时间久了也会觉得腻。三日不见,他却发现最美好的事不是在维也纳谈恋爱,而是坐在她的对面,对她说一句最质朴——质朴到有些多余的——我爱你。
人就是这样,他也只是千万人之中最普通、最平凡的人。他也有着人共有的缺点和脆弱,也有着人才有的“爱”。“池砚,我想去你的身边,即使是爬……即使是爬,我也会爬到你的身边。”
“为了平息学校里的谣传,请你去校医务室请医生出示一**康报告。希望你能配合我们学生处的工作,这对你的名誉也是有帮助的嘛!”
面对学生会会长狐疑的目光和官腔,池砚还能怎样?离开学校已经是她必然的结局。
她离开学校的那一天,乌云压得很低,可是没有下雨,所有的雨水都渗到了心里,不会再流出来了。
回家吧!当外面的世界已经无法容忍她的存在时,回家是她最后的一步路。
深呼吸,池砚做了最坏的打算,无论爸妈说什么样的难听话,无论自尊心是否还有存在的必要,她都会挺起胸度过这一关。
她必须活下去,生命不能夭折在这一刻。
不是她骨头硬,更不是她够坚强,只是她连自杀的勇气都没有。
在踏入家门的一瞬间,池砚真的以为任何困难她都足以面对,却不想有些话从外人口中说出来只是让她难堪,而真正从亲生父母的口中听到同样的话,竟让她难堪得连去死的勇气都有了。
“要么你带着孩子永远地离开这个家,要么你就打掉这个孩子,回学校上课!”
爸已经丢出了他的决定,妈也用她无声的眼泪站在了爸的身边。所有的决定都推给了池砚,以为可以有很多的选择,其实她能走的道路就只有一条——
她要杀了孩子,她要亲手杀了她自己的孩子,她要亲手杀了她和萧何的孩子。
她不想,可是她别无选择。
离家最近的医院就在转角处,没费太大的力气,池砚站在了医院门口。闭上眼,她什么也没想,冲进医院,她尽可能保持平静,坐在对面的妇产科医生是个中年男子,厚厚的镜片后面藏着一双微斜的眼。
“年龄。”
看病还要问年龄的吗?没错,看病的确需要报上年龄,池砚轻启唇角,“十……十九。”
“姓名。”
又是一阵迟疑,池砚吞吞吐吐间露出了两个字:“墨砚。”她不敢报出真实姓名,只以网名相告。
只是,她再也做不回当初的“墨砚”了,那个她无比信任的“降冥王”将她抛给了现实的豺狼。命运多舛,孩子啊孩子,你注定难逃此劫。
将她所说的一切记下来,男医生扶了扶眼镜,斜着眼瞄着她的周身,“哪里不舒服?”
我需要做流产手术——要她怎么说得出口?总觉得那层镜片的后面藏着鄙夷的神色,她需要累积勇气。
“到底哪里不舒服,你快说啊!”男医生不耐烦地催促着,“来妇产科就是为了看病,没什么不好意思的,你到底哪里不舒服直接告诉我,我也好作出诊断。”既然她不说,男医生索性直截了当地提问:“是不是月经不正常?你上次月经是什么时候?上次跟男朋友……”
“呼!”
随着沉重的喘气声,椅子歪在了一边,池砚几乎是夺门而逃。她受不了男医生风轻云淡的口吻,受不了他像提吃饭喝水一样提起她最不愿意想起的事。
逃出了医院,却逃不出她注定的命运。
手放在小腹上,她像在抚摸躺在她怀中的婴儿,“对不起,宝宝。妈妈——让我这样称呼一次自己,就这一次——妈妈不能让你活在这个世上,虽然妈妈很想留下你,可是凭着妈妈一个人的力量无法养活你。如果……如果你爸爸陪在妈妈身旁,也许妈妈有勇气看着你出生。”
事实却是爸爸抛弃了我们,一个人逃走了。是他逼着妈妈杀了你,凶手是他!
“别恨我!宝宝,别恨妈妈,妈妈也不愿意……不愿意……”
不敢去大医院面对医生有色的眼光,池砚的脚步停在了一家小诊所的门口。不管它有没有行医执照,不管它是否有做流产手术的条件,池砚只想尽快解决肚子里的麻烦。她怕再耽搁下去,她会没有杀了孩子的勇气。
穿着白衣的护士上下左右打量着她,虽无鄙夷却带着几分好奇。没等池砚开口,对方先张罗开了:“跟男朋友相处没作好防护吧?”
“我……我……”
瞧她结结巴巴的模样,经验老到的护士一下子就看穿了,“这没什么,来我们这儿做这手术的人多了。没什么大不了的,你也别担心了。”
一只手插在口袋里,她用力地拉开抽屉,物体的碰撞声让池砚倒吸口气。护士从抽屉里面掏出一叠纸,那纸的背面还印了些字,池砚只看见两行字——“男人的根本,女人的**”,剩下的就再也看不清了。
“多大了?”
“十九。”
护士好笑地咧开嘴,露出一排“黄连素牙”,“谁问你多大了,我问胎儿多大了。”
“三……三个多月。”现在已不适宜流产,她知道。
“没事,药流不行,咱们就人流。你自己看着办吧!”
她说得倒是轻巧,听在池砚的心里更没底了。像是为了安抚她的情绪,护士故作亲热地用手肘捣捣她,“听见没有?里面正在做人流呢!那女生才十五岁,比你还小,这一年里都第三回来这儿了。这次胎儿太大了,都五个月了才来。我们医生特有职业道德,估计药流效果不好,干脆人流。你听听!正做着呢!”
听她那口气不像在杀一个胎儿,倒像在炒一盘菜。同样的境遇让池砚的脚步不自觉地向后面所谓的手术室挪去,走到门边,她透过门缝向里望去。
与其说是手术室倒更像是简单的卧室,除了一张床和简单的手术推车上放着的手术器具,以及头顶上那盏显然不够透亮的灯,就再没其他的物件。
床上的女生满头汗水,皱着眉显示出痛苦的神情。这一幕落在池砚的眼中,她不自觉地闭上了眼。
再睁开是因为恐惧,她想看清楚自己究竟被推到了怎样的境地。
被称作医生的人站在女生张开的双腿中间,池砚正想转换角度看个真切,却看见女生的胸部剧烈地起伏,随即整个空间被刺耳的尖叫声湮没。
“啊——”
池砚的心跟着起伏起来,那种痛从她的小腹开始蔓延,直蔓延到她的心上,手术刀活生生地扎在她的心口,每一刀都让痛楚加剧。
“没事没事!”
医生适时地出声安慰,手从她的双腿中间抽出,沾满血的手将一块纱布丢在一边,也将池砚身体里最后一点儿力气给丢了出去。
“呕!”
捂着嘴巴,池砚带着作呕的冲动,扭头冲出小门诊,再不理会热心护士的呼唤。
不记得跑了多久,只觉得双腿再也没有力气摆动,她趴在路边的站牌边一阵接着一阵呕吐,像是要将身体里所有的秽物全都吐出来,或许……也能把宝宝吐出来。
池砚向自己认输,她没有勇气杀了这个孩子。即使她再怎么努力,也没有勇气在清醒的状态下看着一只手伸进自己的体内将孩子蹂躏成一团模糊的血肉,再从身体里拿出来。
那是她和萧何的孩子啊!她怎么可以这么残忍?这么残忍地对待他们的孩子?对待她自己?
可是,不横下心杀了这孩子,她又能怎样?
不失去这孩子,她就会失去很多东西。她不能再回学校做一名单纯、快乐的大学生,她不能继续学习美术专业,她的前途会就此被毁,甚至,她会被父母逐出家门,失去最后一点亲情。
左右两难,她无从抉择。
轰鸣的上天为她敲响警钟,雷电在这一刻向她袭来。她想躲,想躲避她最害怕的雷电,却发现灯火通明的世界竟无她池砚可以躲藏的地方。
如果那件事没有发生,如果那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她没有因为害怕雷电而躲进他的怀里,就不会有这许多的麻烦。
萧何不会消失得无影无踪,他们还可以像从前一样坐在钢琴凳上,她可以安静地靠在他的身边看着他的十指在黑白相间的镜子中穿行,弹出一曲曲成晔所作的经典爱情。她甚至可以安详地睡在他的胸前,继续做着那些有关未来的美梦——
毕业后他会去维也纳进修钢琴专业,她将跟他一起去。在那里,她用画笔画下最美好的幸福,画下他们相爱的片段。他们会在维也纳铺满鲜花的大教堂里结婚,不久他们有了第一个孩子,一个会弹钢琴的女儿,她帮女儿取名池池,那是他们爱的延续,也是生命的延续……
*本文版权所有,未经“花季文化”授权,谢绝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