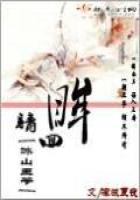虽已近晌午,玉瑾湖上一片烟雨蒙蒙,倒也全无了往日的闷热。雨丝落在翠如凝碧的湖面之上,漾起层层涟漪,一圈一圈,交错勾连,与漫天的迷蒙之色共融,频添几分暧昧。男子一袭天青色织锦长袍,执笔于案前,入目之景是无边无垠的碧色层层,其间点缀着白莲朵朵,迎风而立,雨中起舞,如娉婷绰约的少女一般楚楚动人。他轻勾嘴角,落笔处却是秀丽婉约,如巍峨青峰,远山凝黛的细眉,澄澈清亮的眸子,如深涧幽潭,皎皎月华,小巧秀挺的鼻,唇如樱瓣,含辞未吐,气若幽兰,寥寥数笔,女孩柔美清雅的轮廓已跃然纸上。
清风拂过,水晶珠幔清脆的碰撞声使整个凝烟亭于寂静中添了几分空灵。男子一手握笔,一手轻拂袖摆,神情专注,天地万物落于眼中也只剩那一抹纤长的影子。印有银边暗纹的宣纸上,女孩仿佛足踏莲叶,飘然而来,衣袂翻飞,裙带飘扬,青丝在微风细雨中轻灵舞动。
“云兄,”收起最后一笔,他扭头望向一旁倚在栏杆上闭目养神的玄衣男子,“不若,你来为这幅画题字吧。”男子闻言,依旧双目微闭,不为所动,只两道剑眉微蹙,显然是有些不耐。他不以为然地搁下笔,一丝狡黠的笑意在唇边绽开,故作惊讶地道,“小琛,你怎么来了?”
话音刚落,玄衣男子猛然睁眼,眸底闪过一丝欣喜,身形一跃,已然从美人靠上翻了出去,一掀珠帘,却发现九曲回廊之上空空荡荡哪有半个人影。转过身一脸愤然地喝道,“源初你无不无聊!”
话虽如此,还是缓缓踱到案前,垂首凝视着碧色万顷之中那一抹素白的身影。暗叹道,这小子多半是患了相思病,从小到大哪一次作画不是画的宿安,无论面前是多么动人的风景,他也能硬生生把人家画上去,最要命的是,还能将人物和风景完美融合,丝毫没有违和感。想至此处,不禁抬头略带嘲弄地瞥了他一眼,“她知道你的心思么?”源初摇了摇头,琥珀色的眸子里闪过一丝黯然,一袭天青色的衣裳把他的背影渲染的和薄雾轻烟一般落寞,长身玉立,隔着一层晶莹剔透的水晶珠幔临栏远眺,“她喜欢的是林夏。”
情之一字,最是难解。他轻叹一声,再垂首时,眼里已是一片沉寂,挥毫泼墨,笔走龙蛇,几行清隽洒脱恍若行云流水的狂草如傲雪寒梅枝头初绽,飘逸中透着凛冽,一如那人刀削斧斫般英俊刚毅的侧脸:
秀越横塘十里香,水花晚色静年芳。胭脂雪瘦熏沉水,翡翠盘高走夜光。
山黛远,月波长。暮云秋雨照潇湘。醉魂应逐凌波梦,分付西风此夜凉。
“好字,好字!”源初拊掌称赞,这首蔡松年的《鹧鸪天》用在此处倒也应景,抬眸的瞬间迎上雨后初晴那一丝浅淡的日光扬唇微笑,“为了表达我的谢意,这样吧,醉云居,我请客。”
东安门大街上,红衣雪影飞快掠过,御风踏云,急如闪电,片刻便没了踪影,只余达达马蹄在深巷里久久回荡。月白色窄袖束腰骑装将源初清瘦的身形衬得英气逼人,即便是策马扬鞭之时,身上依旧透着朗月清风般的优雅闲适。
远远地便看见一排整齐的槐树,一片片翠绿的叶子仿佛纤尘不染,在阳光下熠熠生辉。云峘望向那枝叶间隐约露出的一截灰白色院墙,略松了缰绳,徐徐策马而行。“难得啊,今儿倒是挺清静。”源初亦抬眸望去,发现门口仅仅停放着一辆马车,便忍不住感慨道。
“我看这架势倒像是被人给包场了。”云峘剑眉轻挑,眼前这马车深紫色织锦帘幔上绣着暗金色牡丹花纹,车身宽敞气派,其精致华美程度比起那府的马车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待进了院子才发现自己的猜想果然是对的,宽敞的院子里不见一个客人的踪影,倒是整整齐齐站了两排侍卫。正欲迈进大堂一探究竟,便有一位掌柜模样的中年男子迎了上来,躬身行礼,面带歉意道,“不好意思,两位爷,今儿这醉云居被人包场了,还望爷行个方便,改日再来吧。”云峘听罢,转过身望向一脸惊诧的源初,凑到他耳边沉声道,“我让你去全聚德你非要来这儿,这下可好,还没吃上你说的蜜汁脆鸽,就先饿死了。”
“罢了,我也不为难你,你只要告诉我今儿包场的是谁就可以了。”源初心道,爷好歹也是这儿的常客,何时竟受过这等冷遇。强忍下心中的不悦,寻思着反正他们人也不多,随意让出一间空房应该不是什么难事儿,实在不行,他瞥了眼三楼临窗的那几张空桌子,只要有个地儿吃东西,想必云峘也不会介意的。
那掌柜见他二人穿戴不凡,保不准又是富贵人家的公子,遂战战兢兢地答道,“今儿包场的是多罗贝勒府的人。”话音刚落,他便拉起云峘的手,头也不回地往门外拽,一面露出讨好的笑,道,“我突然想起来了,那蜜汁脆鸽也不见得有多美味,云兄你是扬州人,临江楼的淮扬菜做得不错,走,我请你去吃葵花斩肉。”两人拉拉扯扯地退到了门口,云峘双手环臂,倚着门框,似笑非笑地望着他,“看来今儿这蜜汁脆鸽我们还真是吃定了。”源初顺着他的目光回头望去,只见二楼朱漆雕花木栏旁立着一位亭亭少女,浅紫色的斜襟绸褂上暗银色兰花盘旋而上,湖蓝色褶裙下一双三寸金莲若隐若现。湛蓝的眸子里满是欣喜,几缕修剪整齐的乌黑发丝紧贴在白皙光洁的额头上,更添几分娇俏可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