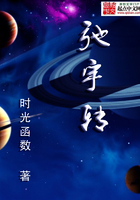在快到和安村的路上,一片乌云压顶,氛围让人只觉得让人有些毛骨悚然。一路上冯丰都在说村里发生的怪事,说来也奇怪,总觉得冯丰说的跟什么有点像,可是这一时半会,我也没有想起来。进了和安村,村里安静的死人,不知道的以为是座废弃的村子,冯丰说自从出事后,出门的人越来越少,人心惶惶。我们一致认为还是一起去找村长得了,村子里的事他应该会有自己的见解。经过村东的时候,一颗黄果树引起我们的注意,这应该就是冯丰说的那个黄果树。树上有几具干尸,恶臭连连,没有人去处理,苍蝇围着乱转,看着都直叫人想吐了。树干的枝桠上绑了许多的白条和麻绳,应该一直是不停的死人,树叶已经全都枯死了,可是枝干却生的好好的,这么臭,养分是从哪里来的?
看来,这里的事还真是不简单了。到了村长家里,村长是一个瘦如枯柴的八旬老人,村长看到我们一行人,眼神闪了闪,然后盯着舒爷说:“请各位一定要帮帮我们村,我们村原本风调雨顺,如今却破败成这个样子,外面传言是寡妇的事闹的,可是我觉得应该没有那么邪门,肯定是有小人作祟,还请各位帮我们抓出真凶还大家一个太平。要多少钱,我们都能够出的起。”舒爷愣了片刻,然后连声答应着。
就在这时谭皓突然扯了扯我,给了我一个眼神示意,我便附耳过去,听见他用低沉富有磁性的嗓音说:“这个村子已经破败不堪,为什么村长非要找我们这种事务所,还不得报警,我觉得肯定还有什么不为人知的事,还有一个疑点就是,既然这么破败,怎么会有的是钱来高价请我们事务所呢?那警察局可是免费的破案啊。”听他这么一说的确是够可疑的,有的是钱?难道是......我还想要询问村长些什么,可是村长好像都避而不答,转而说些无关紧要的答案,对于这些我心中的疑虑越来越多。
舒爷提议先去查看那颗村东头的黄果树,的确那棵树是有些奇怪的。在靠近黄果树的二十米内都闻得到那阵阵恶臭,特别令人反胃,冯丰说这些死去的人都是在凌晨三点,自己自尽而亡,没人敢替他们收尸,生怕沾上什么不干净的东西,村里的谣言特别多。但是多数都是跟那个寡妇有关的,树上染了许多的血,冯丰解释说那不是人的血,是之前村上请来的道士泼的黑狗血,只管用了一两个月。后来再泼也没什么用处了,这时谭皓叫我过去,我走到谭皓身边。谭皓说:“荌叶你看,这些凸出来的小土堆是什么?看样子还很多啊。”的确,树下有很多奇奇怪怪的小土堆,很是让人生疑。这时冯丰跑过来,神情闪烁的说:“你们大家连夜驱车,也累了,我先带你们去整理休息吧,这些土堆没什么好看,是树根长得太奇怪把土给撞出来了。走吧,走吧。”
冯丰神情闪烁,身子有些发抖,叫上我们后走得很快,头也不回,俨然没有之前的半点殷勤。我们也只好默不作声,只是看冯丰这样定是在隐瞒这什么。舒爷小声说:“这冯丰定有问题,怕是在隐瞒什么,必须撬出来,不然不好破案。”
我看了看舒爷,又看看冯丰焦急的背影:“怕是这冯丰知道些什么,看他的样子是有点害怕,有人威胁也说不定,先暂时安顿下来,时间还长,你手段不是挺多的嘛,还怕撬不出来啊?今晚我们就再来查看一番。”
舒爷默默应着,我眼睛一瞥看见了正在若有所思的谭皓,这谭皓看来不是一般人吧,有他这次破案可能要简单的多。舒爷和谭皓的身份和背景,我已经派妖孽去查了,就妖孽那个手段,不查个底朝天才怪了。这两人如果背景干净看来是可以用的,只是舒爷为什么要隐瞒他曾经做过倒斗生意呢?他那些旧伤,大多数还是倒斗得来的,我一定要让他俩实话实说。。我们住的地方是乡村中最常见的大通铺,墙角生了霉,屋子看起来还有些漏雨,潮湿的地面和着一些死去的蛇虫鼠蚁,味道很大,很不好闻。听冯丰说这是他们村里现今最好的房子了,一听这话更加证实了我的猜想,这都已经是最好的了,那么这个村长为什么会说有的是钱呢?
等一阵整顿后,我找了把椅子坐下,然后对着正在收拾书包的谭皓,和正在擦鞋的舒爷说:“谭皓,舒爷,你们俩过来,我想问你们一些事,找个凳子坐下吧。”可能是我过于严肃,他们并没有多问什么,就已经做好洗耳恭听了。
我调整了下语气,开始了我的询问:“既然大家是一个团体,那么就应该互相了解一下,在查案之前,我希望你们能够告诉我,你们的背景,和从事的工作,这也是为以后的办案提供保障。”
舒爷一听有些不乐意说:“你什么意思?审犯人啊?我们是来工作,你都说了大家是一个团体,你这样审我们,有意思么?”
谭皓到比较冷静:“你想知道些什么?”我曾一度以为他没有什么秘密,也许就像他之前说的那样,可是他那微皱的剑眉,让我打消了之前的想法。他们都是聪明的人,我知道一开始他们不会透露许多,但是现在我必须知道,因为我发现了一些东西,如果没有经验的话,他们绝对不能跟我去。
我微眯着眼睛道:“我说了我想知道的,现在时间还早,我还有的是时间慢慢听。”
谭皓说了:“我对你们确实有所隐瞒,我的确是警校毕业的,可是后来我是听从组织安排当了卧底,在一次卧底行动中,因为我的线人暴露了,没有及时联络到我,所以我一直是按照计划行事。最终卧底行动失败,我父亲为了救我,被恐怖分子枪杀。而组织也因为我的失败受到重创,我被开除警籍。但是我手里一直有一份他们的犯罪证据,这些证据足以让他们死好几百次。于是他们追杀我,我好不容易把证据交给组织,组织却因为之前的事认为我有可能还留有备份,于是对我进行了通缉。我现在的身份,是警校的好友帮我弄得,我改了名换了姓,一直在逃。”说完后谭皓叹了口气,后来他告诉我如果他父亲不来救他,就不会死,死的就会是他,就不会发生这么多事,他也就不会犯那么多错,可是这一切都是后话了。
我挑了挑眉,然后一针见血的说:“所以,你现在就是个被通缉的逃犯?”他的脸色一下变得很难看我又说,“你肯说出来已经很好了,现在你用的是新的身份,但是干我们这行的免不了和警察接触,你还是小心点好。”
我又继而看着舒爷,舒爷低头想了想说:“我的事和之前说的都是一样的,除了我家人的死没坦白之外。”他看起来很镇定,果然是干过特种兵的人,说谎都是脸不红心不跳的。我缓缓的开口道:“那么舒爷,你手上的老茧是怎么来的?你的右手无名指和食指的最根部的指节线严重错位,一看就是常年玩枪的痕迹,而你左手和右手都有明显的老茧,据你所说你只干了几年特种兵,就算拿枪,几年时间也不会有这么多的茧。而你这种茧很特殊,应该是常年倒斗才能留下的吧。舒爷还需要我说说你身上那些奇怪的旧伤吗?”
舒爷很震惊,然后眼睑收缩,困难的说道:“罢了,告诉你也无妨,没想到年纪轻轻竟有这样的观察力,真是人才辈出。早些年我是当过特种兵的,但是后来有贱人污蔑我,并且夺了我的功劳还让我挨了处分。年少冲动,就去为自己讨回公道,结果贼人得逞,我却被踢了出来。我很不甘心,回到家乡,人人都看不起我,我更不甘心。一个偶然的机会,我邻村的好友找到我,我便走上了倒斗这条道,好几年凭我这身武艺倒了不少的斗,家里也越来越景气,村里人也都叫我舒爷。可是这毕竟是从死人手上赚钱,全是不义之财啊。前年我倒了个大斗,应该是战国哪个王爷的,机关很多,那个墓去过的人不计其数,却也没多大收获。我拼了命得了盏琉璃灯,据说这不是普通的琉璃灯,琉璃易碎,可是这盏灯在地下上千年了,却依然完好,显然价值连城。后来也不知是谁,传了出去,有些贪婪之人妄想争夺琉璃灯,我家人叫我交出去以保全家平安,可我任性不给。带着琉璃灯出去躲了一阵子,等我回来的时候发现全都变了。我家里一个人也没有了,我当了那盏灯,用那些钱全世界到处找,找了快两年了,也没找到,我觉得也许他们已经不在了。”
我觉得舒爷的话可信度很高,他之前之所以不说可能也是因为,伤心事不想提罢了。我闭了闭眼,看了看他们,我知道从现在开始,他们已经完全信任我了。这样的气氛的确不好,谭皓问我的身份的时候,我只是说:“你听过员工问老板身份的吗?”于是我跳开这个话题说,“好了,填饱肚子,我们就去看看那颗黄果树。”
吃饱喝足后,我们准备出发了,现在天已经黑了,虽然才九点过一刻,但是整个村子基本没人敢晚上出门的。我们带着铁楸特别悠闲地走到了黄果树,经过一番查看后,也就是那些凸起来的小土堆有些奇怪了。我一声令下,我们就开始了挖掘,挖了也没几分钟,几个密封的玻璃瓶就映入我们的眼帘。这些玻璃瓶里面都有一团黑黑的东西,像晒干了的葡萄一样没有一点水分,我们一共挖出了31个玻璃瓶,玻璃瓶里毫无意外都有那团黑黑的物质,唯一不同的是有大有小。因为严重缩水,所以看不出来是什么玩意,我拍了几张特写后,就和他们一起将这些瓶子又埋了。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悠闲地走掉了。
回去后,我立刻打开电脑,把图片发给了妖孽,我们大概等了几分钟后,妖孽说:“通过一系列的技术分析,可以确定,这些瓶子里装的都是婴儿。”听到这个消息我愣住了,全是打掉的孩子的尸体,我们一共挖到了31个。是谁这么丧心病狂?这跟杀人有什么分别?突然舒爷说:“我想起来了,之前冯丰说了的寡妇,这寡妇风流,会不会......”
谭皓连忙打断:“不可能。完全不可能,一个正常女人在这种地方用老办法打过胎的,怀第二个都困难,怎么会怀了31个?冯丰之前说死了32个人,我们找到31个瓶子,这之中肯定有什么联系。”
我们一番讨论之后,最终决定,先休息,各自理理线索。现在村长最可疑,这么大的事身为村长他不可能不知道,却要故意隐瞒我们,一定有鬼。但如果从另一个层面想,也许这也有可能是他们选择不报警的原因。总之明天还得去会会村长和那个传言中的寡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