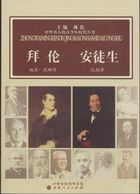江南把两份档案在桌面摆放开,其中一份上贴着一张黑白照片,是一个阳光年轻的男孩,下面有他的名字:霍子岩。“霍子岩也算是生在一个大户人家,在洋学堂念完书后做了一名新闻记者,也是在这个时候和在仙乐斯跳舞的云枝认识的,一二八的时候霍子岩加入了当时的十九路军作战,之后就失去了消息,阵亡人员名单上也找不到他的名字。”陈清雨大概的介绍了这份档案上的重要内容,而且这份档案对于找到现在的霍子岩并没有什么帮助。
江南把目光移向另一份档案,在这份档案中夹着一张素描人像,可以看得出来这幅素描的主人和照片的主人是同一个人,但是素描上的男子显得成熟了许多,特别是深邃的目光,让人过目难忘。“这份档案是我无意之中发现的,偷偷从办公室里拿出来的。”陈清雨颇有些自豪的炫耀自己的收获。江南放下素描,去看档案的内容,这个素描的主人居然不是霍子岩,而是一个叫严师先的人。
严师先,1934年加入共产党,曾用代号“锦毛鼠”长期活动于陕甘宁地区,为陕甘宁地下党重要成员,带有上海口音,然查无此人。
江南眉头紧锁,从这份档案看来,蓝衣社对严师先的了解并不多,或者说他掩藏的太好,如果不是陈清雨偶然发现,没人会知道这个严师先就是霍子岩。“又是共产党!”江南不由自主的想起那日救起的“韩先生”来,他记得追捕他的人口中喊得是“共、匪”“又是?”陈清雨听出了江南的话外之音,追问道。江南于是把那日发生的事情大致告诉了她。陈清雨听罢急急问他:“你救了那个共产党?”江南点头,他已经能够想到陈清雨接下来要说什么了。
“你最好还是少与他们有交集,虽然我不赞同委员长用极端的方式***,但是两党毕竟信仰不同,又积怨已深,接触太多只怕引火烧身。这个霍子岩,你还是不要再接着调查了。”陈清雨正色劝诫江南,在其他问题上她可以随着江南的性子来,但是涉及到党争,她不得不格外提醒江南。“我知道。”江南无奈的看着陈清雨,“你现在的话真是和陶野说的如出一辙。”陈清雨撇撇嘴,“谁像他一样,满脑子就是政治。”江南微微一笑,眼角却瞥着“严师先”的档案,他自然也不愿意与共产党有太多交集,但是事情偏偏就是在相反的轨道上愈行愈远。
江南出了门,谢家却又来了一位特别的客人,她就是肖家的大女儿,肖靖慈。此次前来,,她就是为了替小妹讨一个说法的。
家中只有两房太太和谢启文在,今天他休息,并没有去公司上班。接到仆人的通知,他就从自己房间里出来了,此时陈翠珠和周慧颖已经在客厅坐下了。客厅还有一位穿白色洋群的女子,留着齐耳的卷发,仅仅是这一个背影,看上去就有着一种干练精明的魅力。谢启文见过这个女子几面,他知道这就是肖家的大小姐肖靖慈,也是肖倍国生意上的左膀右臂。肖靖慈听到有脚步的声音,不觉得去看,她虽然及不上妹妹肖靖琪的俏丽可爱,但却有一副清秀的面庞,加上在商场上多年的摸爬滚打,自然多了一份清水出芙蓉的惊艳,身边也总是围了一群各色各样的追求者,大概是因为见过的男人太多了,而其中的大部分又是不怀好意,她对男人的态度实在很冷淡。
“启文啊。”陈翠珠看到谢启文像是看到了救星,大概是因为肖靖慈的态度太强硬了,连一向强势的谢夫人也招架不住,“你看,这肖小姐非要让老二给她妹妹道歉,我说我管不了老二,她还不依,非要我派人找去,他天天不见个人影,我可到哪里找去。”陈翠珠觉得肖靖慈实在可笑,说话的时候也带了调笑的意味,这让本来就生气的肖靖慈更加怒火中烧:“谢太太,谢启铭无论好歹也是谢家的儿子,也得叫您一声大妈,怎么您连管教他的资格都没有吗?”肖靖慈这话算是戳到陈翠珠的痛楚,她气的浑身抖的厉害,指着肖靖慈就要教训:“你这小蹄子,我好歹也是个长辈,你竟然敢这么跟我说话!”周慧颖见她真的发了脾气,连忙劝着:“大姐,你看你和一个孩子赌什么气。”边劝着还不忘给谢启文使眼色,让他拉着点肖靖慈。
谢启文见二人颇有剑拔弩张之意,匆匆插到两人中间,向肖靖慈解释道:“肖小姐,我母亲确实不知道二弟在哪儿,若你现在一定要讨个说法,我这个做哥哥的替他给令妹陪个不是。”肖靖慈看到谢启文文质彬彬,并不像陈翠珠那样无理取闹,心中的火气熄了下去:“你道歉有什么用,小琪现在伤心的很,不是谢启铭亲自去,怎么管用?”虽然语气中还带着些许责怪之意,但是已经平和了许多。“好,我去找他,一找到他就立刻让他去给肖二小姐道歉,怎么样?”谢启文正色答应,陈翠珠却不依了,不满的说:“你去找?你知道他在哪里?去哪里找!”谢启文听到这话有些愠怒,每次一提到谢启铭的事情,陈翠珠就总是没有好脸色,这个不是亲生的儿子就是她的眼中钉肉中刺,不除不快,而且还撺掇着谢启文一起冷落二弟,但谢启文只是简单的希望家里平平静静的,对母亲的做法不置可否,这次听到母亲竟然在外人面前也不留脸面的袒露谢家内部不睦,脸色开始变得阴沉起来。“好了,大姐,启文既然这么说了,多半是知道启铭在哪儿,就让他去吧,也好给肖小姐一个交代呀。”周慧颖看出来谢启文面色不佳,害怕这对母子也吵了起来,敢忙劝着,谢启文赌气站在原地不动,周慧颖朝他摆手:“还不快去找你二弟去。”这才说动谢启文。肖靖慈随着谢启文一起出去了,她不放心谢启铭会不会去道歉。
看着两个年轻人一前一后出了门,陈翠珠伏倒在沙发上大声嚎啕起来:“你看看这个孩子,从来就不跟我是一条心,什么事都跟我拧着来!还有启洋,和他大哥一个模样,都不亲近我这个当妈的,反倒和那下贱女人生的孩子亲!”周慧颖不得不在一旁劝解着,她是整个谢家最让人省心的,既不争宠吃醋,也没有儿子需要去操心,平日里谁也不肯得罪,即便是对一个打扫的下人,也是一副笑脸,很受下人的爱戴。
江南盯着云枝的眼睛,他希望能够从中看出点什么,可是云枝只有奇怪,奇怪他为什么这么盯着她看。江南终于认输,他垂下眼帘,不忍心也不愿意告诉她霍子岩的消息,因为他并不能确定这种消息对一个等待两年的女人来说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你知道了什么?”云枝突然记起江南曾说过要帮她打听霍子岩的消息,那么他现在欲言又止是有了消息吗?听着云枝颤抖的声音,江南觉得无论是霍子岩还是严师先,对女人都太绝情,换做是他,无论生死,至少不会让自己心爱的女人孤苦无望的等待。
“是吗?”云枝抓紧他的双手,渴求的望着他的眼睛,而他此刻只想闪避。如此炽热的目光,晶亮的剔透的眸子,如若霍子岩能够看到,该是多么的愧疚。
“你为什么不说话?是……坏消息吗?”云枝娥眉紧皱,试探着问,江南能够感受到她双手轻微的颤抖,她在控制自己的情绪,控制的很好。
“不是,他还活着。”江南在说出来的那一刻还在思考,究竟哪一个答案对于她来说才是最好的,是霍子岩不在了,彻底的结束漫长无期的等待,还是一个活着却不知归期的霍子岩慢慢折磨她的琉璃心。
“真的?”云枝激动的确认,双眸中的光亮如同两颗闪烁的明星。江南点头,不管今后会怎样,至少现在的云枝是高兴的,高兴的像个获得糖果的孩子。
“你告诉我他在哪里?我要去找他!”云枝急切询问霍子岩的位置,两年的等待,光明就在眼前,让她如何能够忍受的住继续苦等的煎熬呢。
“我不知道他究竟在哪儿,也不能再继续调查下去,你也不要再去查。”江南面无表情的说,他知道这是残忍的话,可是他不得不这么说。
“为什么?”云枝有些失望,更多的却是不解。
“因为他现在是一个危险的人,我与他最好是两条平行线永远没有交集,而你的关心会给他带来危险。”江南的话不咸不淡,却让人清楚的感觉到他对霍子岩的疏离,毕竟霍子岩于他来说是一个陌生人,又是分处于不同阵营的对手,他没有好感也是正常。
云枝经过“韩先生”的事,也大约明白了江南的立场,此刻听到他的话,立刻敏感的意识到霍子岩现在不同寻常的身份,眼前的男人说的不错,他是一个危险的人,既会给别人带来危险,也会给自己带来危险。
看着云枝眸中的星光暗淡下去,江南也于心不忍,他试着安慰道:“霍子岩既然还活着,就一定会回来的,你只要在这里继续等着他,终有一天会等到他的。”说完这话,江南都觉得好笑,终有一天是哪一天?一天两天还是一年两年?
云枝自己也明白这又是无止境的等待,她有些厌倦了,她不是不讲理的女人,男人应当有自己的事业和追求,但为什么事业追求就要和女人冲突呢,她从不觉得自己是一个伟大的女人,她希望自己的爱人能够一心一意的对她,她希望在自己和理想之间霍子岩能够选择前者,但是很显然他选择了后者,是因为他不再爱她了吗?不,云枝自信霍子岩不会忘了她,只是他更爱自己的事业,这个事业让多少男儿前赴后继,流血牺牲。
“在男人心里,女人是不是可有可无的摆设?”云枝看着江南,就像江南一开始看着她那样。江南觉得心痛,他只能说不是。但在心里他默默的想:只是有些男人把女人放在第一位,有些男人把其他某些东西放在第一位而已,每个女人都渴望能够遇到第一种男人,但现实中这样的男人少之又少。江南自问是否会是第一种男人,他无奈的发现现实根本不允许他做这样的男人,在上海,他是为了家仇,回南京,他是为了国恨。他想起云枝曾说过他给她的感觉与霍子岩很像,是因为他们都是第二种男人吗?
云枝赶走了他,她不希望除霍子岩之外的男人看到她脆弱的样子,江南也不例外,她只希望他们看到她的高贵和冷静。江南走后她抱起霍子岩的照片,轻轻抚摸着,又狠狠的摔在地上,相框摔裂了,她就抽出照片,点燃火柴,想要把霍子岩这个人从自己的记忆中付之一炬,可是照片烧到一半她又手忙脚乱的扑灭火焰,心疼的把残缺的一半贴在自己胸前啜泣起来。她爱他,可是她无法忍受无休无止的等待,很多女人都会面对一个难以抉择的问题:是嫁给一个自己爱的男人,还是一个爱自己的男人。而云枝选择了前者,这种爱不仅仅是爱情,她要那个男人永远把自己放在第一位,没有任何事情能够超越,但现在她发现霍子岩并不是这样的人,他可以为了理想抛下她两年,甚至今后的日子也不会见她,既没有一封书信,也没有一个口信,难道他不知道等待的焦灼?他一定知道,只是这无法超越他的理想。
碎裂的相框被浇上鲜艳的红酒,华贵的衣裙也被红酒染上颜色,剔透的钻石耳坠浸泡在酒杯中,云枝躺在铺满羽毛的地板上,散乱的发髻随着她的哭笑颤动,她捡起一缕绒毛,吹到半空中,又落回身上,她大笑紧接着又大哭,手中摇晃的酒杯因为耳坠的存在而叮叮作响,她蜷缩起身子,恢复在母体中最原始的状态,以期能够感受到点点暖意,可整个世界都是冰冷的,她该从哪里汲取温暖?